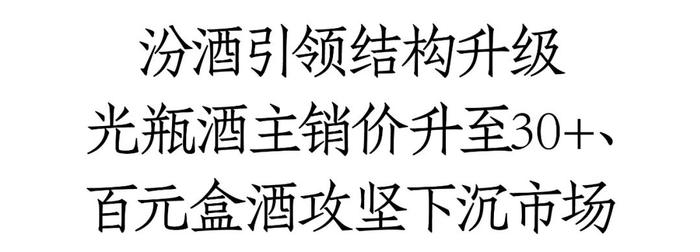2歲,我得了糖尿病,家人給了我力量,如今我過成這樣
我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一個小村裏,今年22歲,是家族裏唯一患1型糖尿病的患兒。糖尿病與我相伴近20年,給我和我的家人都留下了很多特別的記憶和感受。
我對於剛生病的時候沒有什麼記憶,聽家人說,開始時我只是感冒,但是精神越來越差,不玩不鬧,不喫飯,還喝好多的水。我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家人意識到我可能不只是感冒那麼簡單,然後就去了縣醫院,檢查之後醫生說可能是糖尿病。在那個時候,小縣城醫院的醫生給不了父母更多的解釋,只是說去外邊的大醫院看看吧。
我想,那個時候的父母,心情應該是難以形容的恐懼和難過吧。
在北京兒童醫院我被確診爲1型糖尿病,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人生就與“糖”說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注射胰島素。
住院時的情形我沒什麼記憶,到現在我腦子裏偶爾出現的那些畫面,我都分不清是現實發生的還是在夢裏。
我記得當時的醫院不準家人陪伴,所以除了每天固定的幾個小時探視時間,我都是一個人在醫院裏。兩歲多的我,一個人在陌生的醫院,聽着別人說不同口音的話,還要面對時常來“折磨”人的醫生護士,我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哭。
我想,那時候的心情應該可以用“生無可戀,撕心裂肺”來形容吧。聽老爸說,我是在病情相對穩定的時候強制性出院的,因爲經濟限制,也因爲他們接受不了兩歲的我獨自在醫院裏哭到嗓音嘶啞仍在大哭的狀態。
從此,父母就開始了陪我抗糖的生活。
我家在一個小山村裏,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我的生病給這個剛成立幾年的小家帶來了更大的打擊。
在我記憶裏,我的老爸一年裏至少有八個月是在外邊工作,父母都盡力地爲我提供更好的生活和護理環境,但是還是有很多地方達不到科學的標準。
例如飲食,從小我就沒有過特別的飲食照顧,每頓飯都跟着家人喫,但是不喫絕對禁忌的東西。
父母覺得我正處於生長階段,需要的營養比較多,又達不到喫補品的條件,所以在老媽的監控下,粥我可以喝一點,土豆粉我也可以喫一點,除了糖,幾乎所有我感興趣的東西都可以喫,但是不會任由我喫,只能是嘗一下,所以直到現在我看到美食都喜歡說“嘗一下”。
到了冬天,沒有新鮮的蔬菜,老媽就會換着花樣做粗糧飯,含糖量相對較低還營養比較豐富。
老媽還每天定量供給我水果,例如半個蘋果,一個橘子,因爲可以喫到甜味的,所以這是我每天最開心的時候。在老媽鬆懈又嚴格的飲食管理下,我成功地避免了併發症的發生。
2000年,我四歲,我的老弟出生了。做了姐姐的喜悅真是無以言表,看着那小小的一團,“姐姐”這一名詞在我心裏有了無比高大的形象,我身體裏自然而然地爆發出了強大的保護欲。
我們比較愉快的“初見”給我們奠定了堅實的感情基礎。在這18年裏,我們的每一天都相處地比較愉快。我承擔着做姐姐的責任,也享受着來自弟弟的照顧與關心。
在父母的影響下,老弟也對我很多不能做的事產生了包容和容忍的心理,而我的好多習慣也對他造成了很深的影響。
就像我定量的喫水果,小時候的他有樣學樣,我喫多少他喫多少,後來就形成了這樣的習慣,他雖然對食物沒有限制,但是也從來不會一次性隨性地喫太多的水果。
平時老媽給我們買喫的,就像餅乾,我的要買無糖的,他的是普通的,給我們的時候就說清楚,都喫自己的,不許混着喫,所以我倆從來不會像別人那樣因爲誰偷喫了誰的東西而爭吵。
像這樣的事情還有好多好多,總的來說,因爲我一個人,我們一家人都有了好多別人家沒有的規則和習慣。
我的父母都沒什麼文化,老媽沒工作,老爸多數時間在外打工,但是我覺得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最偉大的人。
從我生病到我現在22歲,我幾乎沒有見過我父母在我面前流露過太悲觀的態度。甚至我覺得我的老爸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我所有的不開心或者困擾,都可以讓他輕易地化解,而我和弟弟小小的成就就可以讓他得以滿足,讓他開心很久。
但是在我很小的時候聽奶奶說,在我第一次住院的時候,我一個人在醫院裏邊哭,父母在醫院外邊哭,而在我記憶裏幾乎沒有父母流淚的畫面。
長大以後我才明白,他們不是不會難過,不懂痛苦,而是從來不會將這種情緒帶給我們而已。能夠做到這一點,是需要多麼強大的控制力呀,這也是我對父母產生敬畏感的主要原因。而他們在我面前的樂觀、開朗,爲我小小的世界升起了太陽,灑滿了陽光。
老爸平和樂觀的態度,老媽堅強容忍的個性,爲我們創造了溫馨幸福的家庭環境,讓我忽略了生病的不幸,忘記了疾病的痛苦,也讓我長成現在這般樂觀積極的模樣。
我想,他們這種勇敢、樂觀的精神將會影響我的一生,讓我在今後的人生中有勇氣去面對所有的不幸和挫折。這種家庭的影響,就像是給我殘缺的人生安上了一雙隱形的翅膀,讓我有勇氣飛向更遠的地方。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