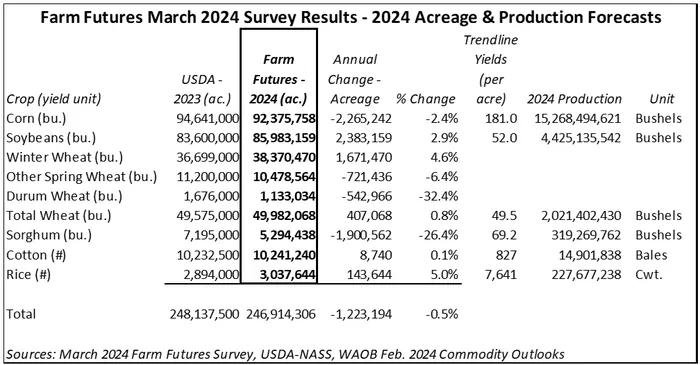農民啊,我親愛的農民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出生在農村,也一直接觸農村裏的農民,雖然村裏也偶爾有一、二個工人回來休探親假,但是真正開始接觸農民身份以外的人,是從村裏的民辦小學畢業後,到鎮上讀初中開始。
進城後,我發現農民就是少知、貧苦、落後的代名詞,我也覺得自己的農民出身有一種難言的憋屈,平時不會輕易暴露這個“祕密”。
後來,從國營企業出來,進入匯仁集團培訓部工作,匯仁是個響噹噹的民營藥業集團,產值進入全國中藥企業前五名,我做夢一般隨集團的迅猛發展壯大,來到上海金茂大廈辦公。當年的金茂大廈是中國第一高樓。
駐金茂大廈辦公的基本上是世界500強和國內頂級大企業,裏面金髮碧眼的人很多,黃種人也是名校的畢業生,看他們的談吐和作派,我在裏面辦公有點竊喜,又有點自卑。
在這裏出點動靜真難。有一天,機會終於來了。營銷部全國七大銷售區的文員和培訓本部的文員來找我商討工作,她們是清一色的上海本地美女,哇,跟她們在一起有一種沉重的出身壓力。商討完工作,她們一口一個何老師地叫着,上海美女的婉約動人,又不忍心讓她們就此離開身邊。
怎麼辦?談點什麼呢?總不能談上海蘇州河的流淌,也不能談上海外灘的風情,更不能談上海城隍廟的市井……突然,我腦子一轉,跟她們談農村!我說:上海哪裏有紅土地?她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沒有。我說:你們喜歡紅土地嗎?她們又異口同聲地說:喜歡。我說:我是江西農村人,江西就是紅色土地。有人搶着說:集團是從江西發展起來的,你從總部調來,肯定是江西人,江西是紅土地,我們從小就從課本上知道,很神奇的,令人嚮往,何老師一定要跟我們談談紅土地。
一下子,我就成了焦點中心,心裏好美哎!我開始爲她們描繪紅土地,我把江西三清山的丹霞與井崗山的紅土壤相結合,再移植到豐城羅山的鄉村田園,有聲有色,聲情並茂,口若懸河。這場講述下來,讓我自己都在心裏爲自己鼓掌。
我又開始爲她們描繪農村田園生活:紅色丘陵的小道上,農人牽着暮歸的老牛,水田裏的禾苗迎着微風招展,錯落有致的農家小舍上飄起裊裊炊煙,一個圍着藍色圍裙的小婦人,把飯菜放在籬笆小院的矮桌上,在夕陽裏幸福地等着丈夫歸來。上海美女們開始譁然。
我又接着說:有一天,家裏來了客人,小婦人從院牆上摘下幾支絲瓜,順手採了一朵粉色的小花戴在頭上,從屋後抓了一隻雞,邁着歡快的腳步來到門前漁塘,舀上來幾尾紅鯉魚,然後在土竈上做起中午的客餐。上海美女們陶醉地說:太詩情畫意。
我說:紅土地上的生活怎麼樣?她們說:美呀!我接着說:山美、水美、土美,如果你們去了就是美上加美。
有人問:我們怎麼去農村生活呀?我說:簡單,嫁過去呀!美女們開心了,紛紛說:何老師,幫幫忙,好波囉。我說:沒問題。心裏想着娶不着老婆的啞巴堂弟,還有小學沒有畢業的疤臉表哥。這時,一位美女一邊推我的肩膀,一邊說:何老師答應了,何老師答應了。美女的這一推,把我推醒了,我馬上明白,把她們介紹過去,我是在作惡呀,我還是人嗎!
過了幾天,有一位美女的鄉下親戚來了,這位親戚是個中老年男人。她自己忙着處理文件,委託我帶他去工作自助餐廳用餐。來到餐廳,這位老伯被琳琅滿目的菜品驚到了。他說:你們每天喫這個呀?我說:是呀,老闆出錢,這是我們平時喫的工作餐,對面是外國人用餐的餐廳,我們喫不慣,今天先喫中餐,想喫什麼就喫什麼,想喫多少就喫多少。
半個小時後,我對老伯說:我們喫好了,走吧。老伯說:我生病了。我過去扶着他站起來慢慢走,說:我知道你生病。老伯說:你怎麼知道呢?我接着說:我還知道你是什麼病。老伯說:我是什麼病?我說:撐得。老伯又懷疑地看着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悄悄地對他說:我是農民出身。老伯說:你不像呀。我說:現在我也學會了小聲說話,抿着嘴喫飯。
一場用餐下來,我們成了忘年交。老伯說:過幾天我就得回去了。我說:好不容易一趟大上海,多玩幾天。老伯說:不行呀,老家村口修大門樓,要開始捐款呀。我說:你隨大流捐點吧!親戚說:難囉,捐少了難堪,捐多了沒錢。我接着說:你準備多捐還是少捐呢?老伯說:家家戶戶平時和和氣氣,就捐一樣多,如果有個別人家的錢很多,就會多捐一點,一下子,拉開與別家的距離,讓其他人家只能“望錢興嘆”;也有一些人家,平時,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也會故意多捐些,壓一壓人家的勢頭;難就難在窮一點的人家,雖說捐款是自願,如果你真不捐,樹要皮,人要臉,全村人的口水會把你淹死,捐款比行政攤派的威力還要強。農村的農戶中,有強權的“美國”,也有戰鬥民族“俄羅斯”,也有“越南”、“菲律賓”等這樣的國家,也有獨立自立,去幫助非洲國家的“中國”。
我自從進了企業,離開了農村,上有老闆,下有員工,我發現自己變得不聰明瞭。見了這位老伯,我想明白了,農戶爲了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得使用做人的“十八般”武藝,不分白天和黑夜,每家農戶就像是一個主權國家,忙着在國際舞臺上表演着精彩紛呈的節目,他們有時聯合,有時牽制,有時炫武,有時炫強,有時養晦。你把農民當好了,真的能當聯合國的祕書長。
有一位偉人在農村當了七年知青,他感慨地說:我人生第一步所學到的都是在農村。不要小看農村,這是有大學問的地方。
作者:左右不對
來源:簡書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