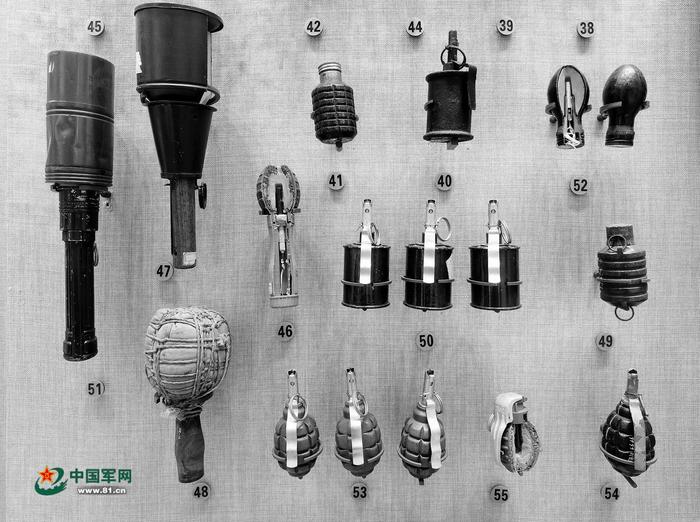垄耘:古城榆林性格
一个人有性格,一座城也有性格。
榆林古城也有性格吗?似乎人们谁也没有这样思考过。
但答案是肯定的——它就矗立在那里,几拓几展,复圮复兴,亦已走过六百多年岁月。六百年,它的性格应该是很成熟了。
一
遗传,是性格成因无法绕过的事实。
它是和有明一代共同成长起来的,它的出生略显迟了些,但一经雏壳,生长的脚步疾速,紧接着,而寨,而卫,而镇,一鼓作气,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嗷嗷小儿迅速成长为一个茁壮青年。
这一切,都因了军事。
军事是促使它骨骼形成的主要元素。它的诞生,原本很平常,就是一个庄,通俗些说,就是一个村子。它和其它的村子没有什么区别,村名也很随便,大漠荒野里,榆树很多,也不是有意栽种,秋落籽、春发芽,逐渐成为一片榆树林子,简而名之,就叫榆林。
所幸的是,从乳名到官名,至此再无更改。
和其它村子有了区别的是——寨,军事的萌芽开始发蘖,也只是萌芽。中国最早的寨子,充其量就是一个土围子,很多寨子不一定属于国有,大多数是村子的联合或家族联合对外的防御掩体。防御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土匪、强盗等。
榆林寨就是这样发轫的。
但由于它后期的国家属性,不久,就成为绥德卫的一个千户屯所。这一步很关键,军事性质和国家属性兼而具之,防护武器也就不仅仅是土棍、木棒等原始器件,而是真正拥有了刀剑戟矛一类的军事武器,而且驻扎了正规的军队。
明朝初期,榆林和真正的战争还隔着很远一段距离,那时的军事前沿是东胜卫——不是现在的东胜,是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附近。正统以降,明王朝遭遇“土木堡之变”,从此元气大伤,开始走下坡路,蒙古势力伺机而动,越套而掠,明朝则是步步退让,向南——退移,再向南——再退移,步步进逼榆林。
榆林就是这样上位于边塞古城的。
成化七年(1471),置榆林卫。然,“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往往得利去。”于是,成化九年(1473),巡抚余子俊将延绥镇治迁徙榆林。
榆林遂跨入“九边重镇”之列。
那是榆林的所幸,也是榆林的不幸。所幸的是,城高雉堞,拥兵数万,镇署卫署齐聚一地,军汉布衣麇集一城。不幸的是,从此战争的序幕就此拉开,旌旗掠掠,狼烟袅袅,马蹄声声,军号阵阵。
阻挡这些铁蹄的外围是长城,长城的修筑也是无奈的选择,是在无数次主动“搜套”不成功下被动转入抵抗的对策。长城太长,仅榆林境内就千七百里,稍有疏忽,或某个薄弱环节里,那些马队就会钻孔而驰到城跟底下。
城跟底下的战争就不是一般的战争了,城内与城外就系于一道城墙。
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农民起义部将李过、刘芳亮率十万大军进逼榆林城下。守城将士誓不投降,激战7昼夜,起义军看明攻无望,暗里偷偷在南城墙挖地洞轰塌城池,双方遂展开巷战,12天全城陷落。城中官民战死者甚多,守城将领受俘后因拒降而被杀。
康熙十三年(1674),定边副将朱龙与怀远西川(今子洲县)盐民周世民、神木副将孙崇雄响应吴三桂反清,带兵围攻榆林城。总兵许占魁、兵备道副使高光祉、城堡同知谭吉璁等文官武将,率领军民,奋力抵抗,叛军围攻三个月而未克。康熙帝闻奏大喜,追赐旌奖八个大字“两守孤城,千秋忠勇”。
1947年7月、10月,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两次攻打榆林,皆因城固墙坚而未能攻下。那已不是冷兵器时代,枪鸣炮轰,但几百年的高筑深垒,让它钢铸铁浇一样,岿然而不动。
因军事而生,因军事而长,军事是它祖宗的基因,基因一旦植入,那不是后天所能改变的。我们潜回时间深处,抚摸历史肌理,古城总是和战争连在一起。军事、抵抗,是它的关键词,也是它的历史基因。穿越六百多年的历史,揭开城头上的每一块墙砖,我们都会看到弹孔、刀痕,那上面遗留着古城的记忆,那上面记录着古城的成长史。可以说,是战争诞育了古城,是战争煅铸了古城,也是战争成就了古城。没有战争,就没有古城的前世,也没有古城的今生。古城的性格就是在战争中逐渐凸显的,也是在战争中逐渐明朗化的。
古城人就像一块粗胚的铁石,时时被放在炉火里锻打,可怜这块铁石,越淬越硬,越锻越刚,也像一个腿绑沙袋锻炼长跑的人,沙袋逐渐加重,腿功逐渐渐长。坚强常常是和淬炼孪生成长的,由于淬炼,才能坚强,由于坚强,也就格局开阔,厚重旷远。
还有皮实,战火几经,每一次都不是一般的伤害,但每一次过后,它都能重新站起来,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在民众面前。它不气馁、不松劲,抖擞精神,将自己的形象再作整装,迎接新的未来。
它硬朗,它从没有服输过,偶尔失利,在它看来,都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关键在于“站直了,别趴下”,过不了多久,又是一条好汉。
二
环境塑造人,环境也塑造城。
榆林之地的山,已不是真正军事意义上的山了,不尖峭,不陡立,也没有巨石岸屏、峻崖断壁。但在这十里百里见不到一块石头的荒漠瀚海上,驼山已经很是巍峨了,它的土质坚硬,比一般黄土高原的土质更多含了胶质,粘腻、坚固,不容易流失,不可能滑坡。对面就是黑山,北面还有红山。这三座山的颜色很独特,驼山黄、黑山黑、红山红,都很惹眼。山都不是很高,只不过丘陵而已,但对于习惯平坦草原的蒙古马队,已经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了。而且三山而环,就像一个大的瓮城,三面埋伏,马队纵有千只蹄爪,也跑不过弓弩枪箭的速度。
其次是水,城门之西,就是榆溪河。榆溪河流至古城脚下,因为地势平坦,因为沙床作底,就任意兜开臂膀,左舒右展,漫漫翰翰,最宽处足有百米之广。河不见深,但床里皆沙,马行上去,蹄脚深陷,如入雪层,拔脚艰难,行走困惑,天然一堵屏障。向南,紧邻城墙,是榆阳河,河在谷里,就像一条天然护城河自然而生,河里一切活动,都在城头哨兵的眼里,一旦开弓,百发百中。再西北,是芹河,西东流向,正好堵在北来的马蹄之下,和榆溪河构成犄角之势,有兵伏在黑山之上,刚在射程之内。
还有那沙,千里百里,浩浩漫漫,有风千尺浪,无风沙自惊。毛乌素沙漠的沙源太广了,它每年以亿万吨级的沙子向四围扩展领地,榆林是它的主要倾倒对象,它和风沆瀣一气,以沙尘暴的方式肆无忌虐地向榆林进攻。“同治二年(1863年)北城部分城垣被流沙埋没,时值关中等地回民造反,道宪常瀚令弃北城,在广榆门东西缩筑北城墙,长438丈。”这也就是很多后人置疑的为何好端端将一面城墙缩回而呈刀币型的历史原因。
©郑贝贝
还有雨雪。这里的降雨量明显偏少,雨少不说,分布也极不均匀,多数时候都是艳阳高照,天天早上都是“东方红”,一旦乌云腾卷,就是瓢泼大雨,如注大雨动不动就在几十毫升乃至百十毫升以上。旱则旱矣,涝则涝矣,天旱雨涝没收成,是这里的长情。冬天的雪也是奇怪,常下在年关附近,一下就是半尺一尺,牛羊出不了圈,街上雪堆成山。
©白军
民国《榆林县志》载:弘治十六年(1503)五月,榆林大风雨,毁子城垣,移垣洞于其南五十步。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大旱。四月,天黄三日,蝗虫蔽天,人取食之。崇祯四年(1631),榆林连年旱。十一月,大雪,至明年正月不止,深丈余,人畜死过半……这就是榆林当时的现实,检视镇志、府志、县志,灾害实在太多,隔三差五,就会遭遇。这里是老天疏漏之地,老天的眼光总是偏向于江南,偏向于关中,看到这里时总是斜昵。
城墙以里的古城,是它的内部环境。古城建在半山坡上,半数以上居民住在山上,上山的路很逼仄,人数众多,巷道之间的距离很有限,窄狭的巷子,只容二人并排行走,遇有下雨下雪,巷里雨水浪卷、雪里冰冻,更是行走艰难。那时无电无气、烧火靠煤,多数靠柴,背炭肩柴行于巷道更是维艰。巷道后期铺砖,前期只是土籽,泥泞滑腻自是平常之事。
外部险恶、内里艰涩,就是古城的环境。
©张兴华
生于塞上,长于塞上,它见惯了这种其他地方没有见惯的习惯,它只有将自己的强大修炼得足够坚强,以对抗外部环境的强势推进。显然,这不是它的自愿,是在内部和天地的多重挤压下的无奈自我塑造。是环境,让榆林古城一天天越走越大,越走越坚强,越走越走出自己的性格。清谭吉璁《延绥镇志》云:“榆林地险,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又果悍敢战,不贯胄,寇呼为骆驼城,人马见而畏之。四方征调,所向有功,更多将才,有节气,视它镇为最。”
环境与古城,时刻是一对矛盾,坚硬与柔软,强悍与沉默。相互塑造,相互制掣。可以说,没有这些可恶的内外环境,也就没有古城的坚实、厚重,也可以说,没有古城人的坚实、耐劳,也就没有古城的大气、巍峨。是环境成就定型了古城,是古城牵制反塑了环境。
三
城是人建造的,某种意义上,城的性格也就是人的性格。
甫初,最早的榆林人就是榆林庄人,这些人是最原始的土著。他们可能是一个宗族,也可能杂姓而居,他们和平相处、悠然而栖,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榆林寨。
©吴福爱
打破这种格局稳定的是卫的建立。军人开始大批量地入驻卫堡,这些军人的籍贯,一般来说,可能来自于周边地区,那时的交通还仅局限在车马,大部分是徒步,太远地方的跋涉是短时间无法达及的,也就所幸,语言、风俗等交流还是大体相近或相似的。
显然,这只是发展途程中的暂时现象。
©贺子明
等到延绥镇治从绥德迁往榆林,这一里程碑的城市建设和它区划范围的扩展以及中心城市的标杆性建立,榆林古城的人员构成经历了一次最大的洗牌和刷新。以明郑汝璧《延绥镇志·兵志》载:“今见在官军二千二百一员名,马骡一百三十一匹头。”明初实行“世兵制”,军人是世袭,一代传一代,军人所到处,连家属也一起携带。
这些人成了榆林人的主要构成。据道光《榆林府志》记:“明洪武初,延绥编选军士,有归附,有收集,有选充,有编拨,共四等。此外有赖字军,盖天顺初,出各卫远年无勾之军,发榆林卫编伍,为老军。成化初有士兵,弘治中名义勇军。又成化中有杂抽军,有四班壮丁,有屯军,一名备冬军。正德中有选丁。嘉靖中有免粮抽军。又明每岁有分番戍边,名班军,至万历年始废。嘉靖中,岁征各镇兵入卫,以榆林四营更番戍守,为入卫军,时呼为小马军。”这就是榆林军士的构成,其中“各卫远年无勾之军”,即是犯死罪因故免死改刑而充军役,却又未被编入充军服役之逃兵。这些人的籍贯实在不好考籍,九州之地无所不包。
©王亮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世兵制”的疲软和塌陷,也随着蒙古势力的不断侵扰,还被迫实行了“征兵制”“募兵制”,这些所募之兵,来源地域也是广及全国各地。
他们后来居上,成了榆林的主要居民。
这些榆林人身上流淌的是军人的血液,他们的世袭制带来的后果就是血液的不断纯正和更加鲜红。他们忘不了战争,忘不了战争带给他们驰骋疆场的英武和疆场归来的兴奋。他们争强好胜,即使与人相处在和平环境里,他们依然保留着“两兵相接勇者胜”的好胜心理,常常让一些简单的事变得复杂,让一些本该用嘴解决的事变得拳脚相加。当然,他们也仗义,也豪爽,不斤斤计较,不锱铢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更多地在于获取全局的胜利。
这些多地域多人种的组合,使古城人的性格里自然融汇了西北人的硬朗,西南人的宽宏,中原人的坦荡,江南人的聪慧,东北人的豪爽,华北人的方正。当然,也不可回避地携带了南方人的促狭和北方人的莽撞。所以,古城人到底是哪里人?就很难说清楚,他们是相互的同化。这种同化究竟是秦人的体魄占据了多数,还是晋人的语言获取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还是京城的建筑格局让多数人羡慕而仿效,抑或是南方的小调让人们的听觉发生了位移,都是有可能或会发生的事实。他们的血液是O型的、混合的,融汇了汉族人的多血质,也杂合了少数民族的B型血、单血质。他们的体型是粗犷的、伟岸的,他们的体质也是白皙的、柔美的。他们性格的主基调是豪放的,他们性格的辅支撑是温良的。
四
开放与保守,是人为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它先天也后天地形塑着性格。
这道墙,筑得比西安城墙还高了半米,底宽五丈,顶阔三丈,高三丈六尺,池深一丈五尺。城墙上建砖垛口1700多个,有逻城72个,并置火炮。站在城墙之外,仰首向上,只能看到一跺一跺的雉堞,城里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在那个冷兵器时代,那就是天堑,除非鸟儿,人力是无论如何难以达及的另岸世界。
这就是铁桶般的榆林古城。
城墙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对外,阻挡了敌人,对内,封闭了自己。
城墙越高,封闭性越强。
榆林古城就是这样逐渐地将自己包裹起来的。
古城里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们的安全意识逐渐增强、古城墙变得越来越厚重结实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半径也变得越来越局促。当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逐渐地局限于城里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与外部世界的隔离,与周围生活的隔膜。
市民,就是这时候在这座城市里产生的。一座没有市民的城市,严格意义上,还不叫城市,它就是一个大集市,一个村庄的放大版。榆林几百年城市的敷衍,使它具备了一个城市所有的应备条件和必备条件,那就是孵化了真正的市民。
市民是不靠种地为业的,他们的职业就是经商、做工。封闭起来的榆林古城里的市民开始经营他们的城市,他们建起了很多商铺,像天成恒、福泰隆、晋源恒……建起了很多作坊,像万益银炉、三合公皮坊、长发泉油坊……他们的服务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城里居民的消费,一类是城墙之北蒙人的需求。康熙朝之后,蒙汉关系变缓,互市开放,民间交流日益活跃。蒙地所缺正好是古城所产,古城所需正好是蒙地所产,这种贸易往来是平等的也是互相渴望的。一时间,边客催生,古城里外出内蒙做生意者日渐增多,这也是全陕北以及全西北意义上的“走西口”现象。
这种长距离的贸易,反倒让古城忽略了对近边地区贸易的生疏以及回避。相对意义上,蒙人的憨厚和做生意的粗放更切合古城人的胃口,近边地区人的细致、锱铢斤两反倒让古城觉得抠门和不好打交。长此以往,这种对于周边地区的嫌吝让古城逐渐和近边产生了隔膜,以致有女不嫁城外郎,有男不娶城外女。
原初,城里城外的风俗礼仪差别是不大的,其后,古城里两拨人的加入,改变了这种格局。一类是京城贬谪官员,这一类人虽然政治上遭贬,但生活质量上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随身携带了家眷、佣人,包括厨师。他们害怕偏僻之地饮食粗放不合他们的胃口,在生活上受困,就亲自带来了京城的一应服务人众;另一类是江南北上做官的官员,像余子俊、谭吉璁、刘厚基等,他们和京城贬谪官员的心理是一致的,他们同样带来了自己的一班服务人员,包括唱江南小曲的戏班(后来逐渐演变为榆林小曲)。这些人都是古城的大户和名流,他们的礼仪规矩直接影响着古城的习俗,一般市民仿而效之,就逐渐变成了恒定的风俗习惯。
从此,古城就逐渐变成“文化孤岛”,和外界的风俗礼仪全然二致。
高门大户们仿照京城建筑格局盖起了四合院,也仿照江南风格设计了天井、花园等南方风味的建筑,唱起了小桥流水的榆林小曲,喊起了老北京的“爷”们称呼。
市民的成分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具市民味了。市民们不出古城就可以生活得很圆满,他们在粮市里买粮,在菜市里买菜,在书院里上学,在作坊里做工。一切变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一个标准的城市格局在大漠上崛起。
这么说吧,是古城人最初建造了古城及城墙,最终,古城及城墙又将古城人框定并固化在古城人的思维以及风俗习惯上。从农民到军人,再到市民,是古城人进化演变的三部曲,也是古城人从朴质到刚勇再到圆润的性格发展史。成于斯焉,固于斯焉,这种双向逆背的定律,是无数人自觉走进而一旦意识到又无法挣脱的精神枷锁。
五
时代决定性格,时代也改变性格。
古城榆林诞育勃盛于有明一代——因为军事重镇,也鼎喧繁荣于有清一朝——因为商业边贸。
作为一座古城,前期明朝和后期清朝的性格是迥然有异的。
曹颖僧《延绥揽胜》曰:“榆林自有明由绥德迁镇筑城以来,以地临塞上,屯兵习战,故人娴骑射,重武轻文,勇略将材,炫耀史册。迄崇祯甲申……民喜酒肉征追,妇女则艳妆奢饰,相习成风,视为固然……民国以来,中级社会者,类多经营商业,练习蒙语,入套跑边做生意,不数年,牛羊驼马牧养成群,皮毛绒酪满载而归,利赢数倍,蔚为富商大户。下焉者,操作百工匠艺,独擅专业,此外,肩挑摊贩、水湿屠厨各行及走卒仆厮、当差供给之人,均能糊口养家。因是榆市之人,金融活动。”这就是古城前期与后期的相异之别。
这一切,都是时代的造就。
清朝走来,古城的军事地位式微。按理说,城墙里的人还是原来的那些人,但是时代需要他们转身,他们就不得不转身,褪去的不只是军装,还是肌体和心理。身份的改变也就改变着他们的内心。
古城的装束也在改变,原来城墙上站的大兵减少了,到后来,是有了需要才摆摆姿势,装装样子。城墙上的城砖有些已经脱落了,也是视而不见,掉一两块是应该的事。
古城里的街面比原来讲究了,铺上了光洁的石板,走上去叮当作响,铺面都挂起了匾额,额上的字也很讲究,都是请书法家或老先生书写的。书院里的读书声一天比一天高亢动听,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坐在那些冷板凳上,青衫白袖,端坐如仪,还甘愿挨着戒尺。有那些出众的考中了进士,满街上披红挂绿的招摇,门上还新挂了“进士第”的匾额,多少走过者都是仰头观瞻的。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少了,练拳脚功夫的偶尔才懒洋洋地去一次,教练们也不过于追究。他们感慨地说,修文偃武,时代不同了啊!
端的是,古城里的水也比原初越来越旺了。龙口里的水除了供给全城人的饮水外,还开凿了沿街的水道,就像南方城市的街水一样,蜿蜒穿过城巷,汩汩而流。大漠硬城,一条渠水应是多么珍贵,人们的心情也随之而变,变得平静、安宁。水能养人,尤养女人,桃花水、榆林女,甚是城市一景,那种注重打扮和奢侈,也本就是城市女人应有的风采。连同男子,也另行儒雅风流,谈吐不俗,落落古风。
确实,时代需要榆林古城。因了军事,古城不得不崛地而起,他们的性格就朝着尚武而行,前期古城的性格里自然是刚硬、坚实。时光之辇,需要古城柔软的时候,古城就自然转身了,向着商业看齐,向着经济起飞,古城真的就成功跨越了,从明代一步跨越而入清朝。长袍马褂替代了甲胄魁衣,温文尔雅替代了雄纠气昂,讨价还价替代了阵前喊话,说买说卖替代了战胜战败。
时代是一把利剑,将古城从方正削劈为圆润,从强刚熔化为柔济。人随城转,城随人走。人亦城也,城亦人也。前朝后朝判若两城,前期后期判若两人。
回望六百年的古城,走到现在,古城人增了又减,减了还增,走了一茬又一茬,来了一批又一批,但它的性格却一直秉持未变或变:尚武,豪性,硬朗,刚正,皮实,大气,放浪;当然,也或时移世易:传统,知性,自在,封闭,阴柔,圆润。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