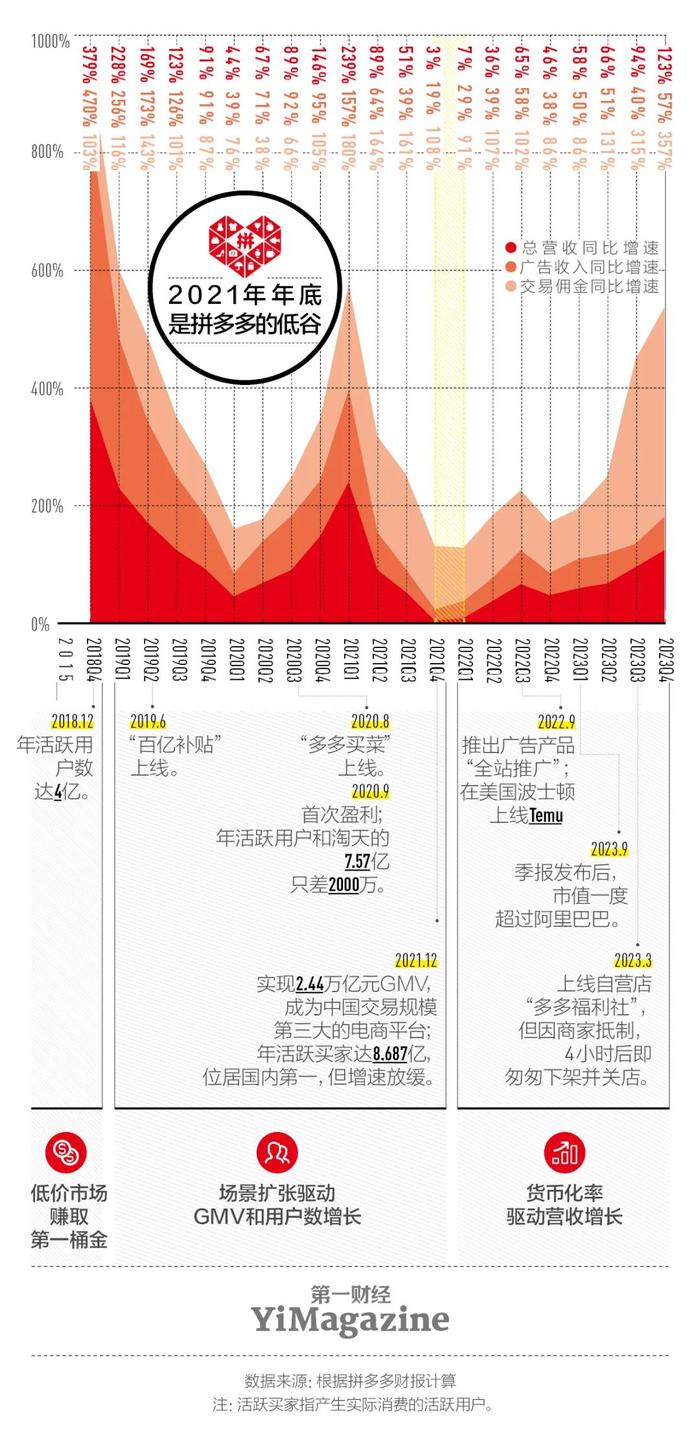阿里組織架構調整的目的之一:把“錢袋子”再往大做
摘要:單憑張憶芬口中的打通下鏈路賣流量,阿里媽媽就收入不少。通過這個指標,張憶芬希望阿里媽媽能從過去關注即時收入,到關注對消費者的長期影響,開發能評價7億消費者真正價值的指標。

原標題:阿里組織架構調整的目的之一:把每天50億流量的“錢袋子”再往大了做
阿里大樹底下能否長出“參天大樹”?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劉哲銘
2019年12月19日上午,阿里巴巴宣佈進行三年來第19次組織架構大調整。
淘寶天貓與阿里媽媽再度緊密結合:蔣凡在現有淘寶天貓總裁的職責基礎上,將代表集團分管阿里媽媽事業羣,總裁張憶芬(花名趙敏)向其彙報。
與天貓、淘寶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業部不同,很少有人能清楚地描述阿里媽媽的主要業務。這家成立於2007年的公司,聽起來與阿里巴巴成雙成對,實際上是阿里巴巴的商業數字營銷中臺,依託於阿里巴巴其他事業部提供的媒體資源、數據資源,服務商家營銷。
更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不廣爲人知,但阿里媽媽卻是阿里巴巴最重要的收入貢獻者;儘管未曾對外公佈過具體數據,但因其對阿里巴巴整個集團財報的巨大貢獻,常被外界稱爲阿里的“錢袋子”。
在誰來把持“錢袋子”的決策上,阿里巴巴十分果斷,四年來阿里媽媽先後歷經四次換帥。
2015年,俞永福晉升爲阿里媽媽總裁,而後由朱順炎接任,2017年11月,阿里巴巴CMO董本洪又接替朱順炎的崗位。2018年11月16日,一個陌生的名字出現在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花名逍遙子)發出的全員公開信裏。張憶芬(花名趙敏),這個長期以來與阿里媽媽毫無關聯的人物,成爲了阿里媽媽的“關鍵女士”,接替董本洪(花名張無忌)出任阿里媽媽總裁。
如此頻繁調整的意圖,不得而知,但逍遙子的確希望阿里媽媽能進行“升級”。“在三年裏帶領(阿里)媽媽做一個策略上面的升級,這實際上也是老逍(逍遙子)的期待。”近期,張憶芬接受《中國企業家》專訪時強調。
在這位新上任的總裁眼裏,即便每天有超過50億的推廣流量,但阿里媽媽的商業化仍然“做小了”,她顯然看到了一個更大的蛋糕:“不是隻有淘寶的資源,7億的消費者在我們這裏,每天生活的各個場景都可以做一個商業化應用。”
阿里巴巴集團公佈的2020財年第二季度業績報告顯示,中國零售市場移動月活躍用戶達7.85億,較2019年6月勁增3000萬;年度活躍消費者增長1900萬至6.93億。大概市面上任何一家公司都未能給到張憶芬如此足的底氣。
其實,這也是張憶芬的一次迴歸。
曾被稱爲“搜索一姐”的張憶芬,於2007年出任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兼中國雅虎副總裁,負責雅虎搜索業務,隨後負責阿里巴巴集團P4P廣告及淘寶網的互聯網廣告營銷業務。不過,2009年4月,張憶芬表示因“個人原因”離職。
離開阿里巴巴後,張憶芬依然活躍在互聯網廣告營銷領域。2018年,在與老逍見過一面後,張憶芬便收到了聘書,化身“趙敏”,重回阿里巴巴。

來源:被訪者
流量飢渴
對於很多廣告主來說,阿里媽媽做得可不小。單憑張憶芬口中的打通下鏈路賣流量,阿里媽媽就收入不少。
某品牌電商工作人員向《中國企業家》表示,每年與阿里媽媽的合作都在千萬級。據財新傳媒報道,阿里媽媽爲阿里巴巴集團創造了超過總數六成的收入。
不過,在談及具體收入時,前阿里媽媽總經理薛思源(花名漫天)表示,這些都是貢獻給集團,具體比例不清楚,但阿里媽媽的確已經服務了數百萬客戶。
2019年11月11日當天,雙十一天貓交出了2684億元的成績單。這場狂歡背後的營銷收入外界難以知曉,但在阿里巴巴內部,阿里媽媽的員工和阿里雲一樣,都是這場盛典中最忙碌的人。
一位紙品電商從業者透露,11月7日鑽石展位(淘寶網圖片類廣告位競價投放平臺)的十次展現爲12元,11月8日變成了一次點擊16元,一夜之間漲幅超過33%。
“僧多粥少。”福派牙刷的電商負責人慕孟飛表示,“阿里媽媽的直通車、鑽石展位等推廣工具基本上都是競價機制。”每個商家都期待獲得最多的流量資源,但資源位卻有限,所以需要通過競價機制來調節流量分配。
自2007年創立之後,阿里媽媽逐步完善其業務,但淘寶直通車、鑽石展位一直都是其拳頭產品。
“淘寶直通車,通俗些講是買詞,通過競價獲得關鍵詞的流量,同時可以對目標客戶進行溢價。”做了五年電商的柯子如此解釋這款阿里媽媽的產品,而鑽石展位也依循類似邏輯,是“賣展位”。
一名電商從業者用“流量飢渴”來形容這種現狀——三禾50萬的展位如果沒能帶來200萬的銷售額,那麼它的這次營銷就會虧本。
但張憶芬並不認同,價格上漲的原因歸結於阿里媽媽的“競價機制”。
“因爲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定價,每一個商家的經營效率不一樣,可以出的價格也不一樣。我不能叫說你出少一點,讓別人得票。這是由市場決定的,每個環境裏都有市場,我們並不是那隻上帝之手。”在張憶芬看來,價格是由市場進行調控,“競價”只是反饋變化的錶盤。同時,這樣的競價機制設計是市場分配最聰明的設計。
其實,不止阿里巴巴,谷歌、百度、騰訊、頭條等全球互聯網巨頭大都採用這樣的競價的流量分配機制。值得一提的是,整個中國網絡廣告市場規模水漲船高,從不足百億增長至2016年的2900多億,翻了近30倍。
不做“殺一刀”
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錢袋子”這個稱呼。
每當提起這樣的稱呼,有人會忌諱,因爲這樣的形容總會帶來關於資本驅動的印象。但張憶芬則坦然:“我們是‘錢袋子’,這個是沒有錯的。而且我還希望能越來越大。但‘錢袋子’是要長長久久地幫助廣告主,讓他們賺到錢,不是‘殺一刀’。”
“阿里媽媽完全是市場經濟。”張憶芬進一步解釋。作爲阿里巴巴有機體的組成部分,系統一隅的角色在給予阿里媽媽生命力的同時,也讓其有了自我限制。
從柯子近期的投放經歷來看,“殺一刀”的情形倒是不存在,不過也有一來二去基本白乾的經驗。在柯子展示的直通車報表中,表現好的投入產出比能達到5.81(即投入1元產生5.81元營收),但有的投入產出比僅爲1.07。
張憶芬認爲流量之所以重要,是因爲過去商家必須通過流量這個載體才能到達消費者,才能達成交易,所以大家的重心都在流量上。在轉化率一定的情況下,越多的流量就意味着越多的購買,這恰好也是阿里媽媽過去最大的優勢。
2008年,馬雲做出了一項對於阿里媽媽而言極爲重要的決定:“塞回淘寶的子宮”,將阿里媽媽與淘寶合併。
漫天回憶:“當時,阿里巴巴的商業邏輯設計是把廣告等同一個商品,廣告主在網上能看到發佈價格信息,然後進行採買。但後來我們發現這條路根本不靠譜。”阿里媽媽遇到了兩手空空的困境,既沒有任何抓手能夠抓住線下的廣告主,也沒有任何的廣告資源。
阿里媽媽併入淘寶後,商家變成了潛在的廣告主,淘寶變成了媒體,命懸一線的阿里媽媽重新存活了下來。但這樣“一招鮮,喫遍天”的盈利方式,也爲之後的發展路徑埋下“隱憂”。
“這樣講好了,我們過去事實上做的是一個營銷下鏈路,賣直通車、賣信息流,做個交易,而不是全鏈路的marketing(營銷)。”張憶芬直截了當。而現在,阿里媽媽要將眼光從電商抬高,從過去的流量運營轉化到以人爲核心的消費者運營,開拓全面運營和管理消費者的新路徑。
當市場紛紛陷入流量怪圈時,張憶芬認爲市場也應該進行反思:“當‘流量’成爲整個行業關注的重點時,我們需要思考了:我們可以達到影響消費者的目的,流量是不是唯一的手段?我現在越來越覺得不是,我們要開發的並不是這樣子的狀況。”
但對於阿里媽媽來說,真的能下決心捨棄手中的“流量”王牌嗎?

來源:被訪者
沒有免費的午餐
“流量爲中心實際上是在考驗我們用戶重定向的能力。現在,我們可以做IP,做超級派樣。利用數據技術,幫廣告主把樣向消費者派出去,這樣的解決方案中間不會牽涉任何資源位、任何廣告位。而且,已經形成了一個閉環。”在張憶芬繪製的未來藍圖裏,阿里媽媽要開發的是以數據和技術爲核心的產品。
轉變流量運營的觀點在整個阿里巴巴內部早就有跡可循。董本洪曾提出要運營超級用戶,更早些時候,時任阿里COO的張勇也曾提出,阿里會從一個運營流量的公司過渡到一個運營數據的公司。
市場方面,通過流量提升收入仍然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如果阿里媽媽推出新的數據產品,可能會有用;但如果產品還在早期,不太成熟,我們應該會比較保守。”對於像慕孟飛所在的小商家來說,新推廣方式的試錯成本太高。
而喫螃蟹的人已經開始品嚐到新的紅利,聯合利華是其中一個。作爲大快消巨頭,聯合利華生意的大頭仍在線下,因此,如何把線下生意數字化,是它想要突破的重點。據聯合利華(中國)數據與數字化副總裁方軍介紹,他們原本已經準備花大力氣去探索,剛好以阿里媽媽爲代表的商業操作系統提供了相應的能力,雙方一拍即合。
線上線下的消費者運營變成一盤棋。一方面,包含小店鋪在內的代理商網絡被數字化了,分發到某偏遠城市夫妻小店的一袋洗衣粉,也是數字化、可運營的;另一方面,泛快消的物流難題也大大解決,以往,洗衣粉、洗髮水等產品往往體積大,物流成本昂貴,而通過本地化履約,比如與天貓超市、餓了麼等合作,或者是未來通過區域經銷商,消費者購買的洗衣粉、洗衣液等可以直接從最近的門店發貨。這不僅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時,消費者訂單也由聯合利華統一來進行管理,線上也帶動了線下的活力。
許多線下原本不可運營的場景,現在成了品牌增長的新抓手。更爲顯著的是,全域的數字化帶來了極大的獲客動力。
2019年12月18日,在阿里巴巴第二屆ONE商業大會上,良品鋪子總裁楊銀芬說,其在門店3公里內的會員實際佔比只有18%,它通過新增輕店和前置倉的方式服務這部分消費者,從而擴大了店鋪服務範圍並提升了履約速度;通過引入跨端運營策略,聯動線上線下團隊,復購次數提升20%;在2019年雙十一,它通過藉助支付寶和天貓的跨端能力,在阿里域的獲客能力提升40%。
2019年9月,阿里媽媽M營銷峯會上,發佈了一個關注人的新指標“阿里媽媽購買意向指數”,以此來衡量每次品牌整合營銷投放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通過這個指標,張憶芬希望阿里媽媽能從過去關注即時收入,到關注對消費者的長期影響,開發能評價7億消費者真正價值的指標。
不過,在阿里媽媽變化的過程裏,商家們也透露出了擔心。
“數據也是要花錢的,不花錢的只是一部分表面的報告。真正關於市場、競品的分析也是要付費的。”一位商家向《中國企業家》分析。雖然指標可能有效,但慕孟飛清楚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有商家表示,如果能不再以流量的方式來獲取利潤,可以投入更少,掙更多,何樂不爲?
錢進了誰的口袋?
十年間,阿里巴巴從電商業務逐步發展成包含阿里雲、螞蟻金服、菜鳥等多項業務的“超級巨人”,營收與利潤不可同日而語。據阿里所發佈的最新財報顯示,其2020財年第二財季營收爲人民幣1190.2億元(約合166.51億美元),同比增長40%。
業務聯合還能給阿里媽媽帶來更多可能。
阿里媽媽首屆M營銷峯會上,阿里媽媽在展臺中位於中心位置,外圍環繞着天貓、分衆、餓了麼、優酷、阿里大文娛等衆多集團事業部。這無疑最清楚地傳達出了官方定位,阿里媽媽是中臺,它肩負着依託集團的核心商業數據和超級媒體矩陣做營銷的使命。
不過,最終的收入有多少流入了阿里媽媽的口袋,有多少歸於其他BU?這似乎並不是決定內部合作的關鍵性問題。
“內部財務有分配比例,就是說流量在誰的土地上,客戶從誰那邊來,誰就拿大頭,中間做技術的再拿一塊。”張憶芬表示,“都是在阿里的口袋,它放在左口袋、右口袋、大口袋、小口袋,都可以決定。”
說到這裏,張憶芬想了想對阿里媽媽的比喻:“與其說是‘錢袋子’,不如說是‘過路財神’。”
張憶芬曾出任全球效果營銷科技公司Criteo亞太區的掌門人。“它(Criteo)可以理解爲是一個沒有淘寶跟沒有天貓的媽媽(阿里媽媽),但基本上就服務了整個亞洲的電商客戶。”張憶芬形容。
阿里巴巴的收益增長,是否意味着商家多掏錢?二十歲的阿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在接受《中國企業家》專訪時,逍遙子曾表明:阿里巴巴積極創造生態,既能夠幫助中小企業發展,也鼓勵支持新的獨角獸、小巨人發展,從而讓大樹底下不僅能長草,也讓更多小草長成參天大樹。
阿里媽媽給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在峯會上張憶芬指出的種種問題——爲什麼自己的頭像照片比客戶大?爲什麼演講順序按照職位層級來設置,而不是業務邏輯?可以看出,客戶第一在阿里內部的烙印,阿里媽媽希望的是和客戶一起探索新營銷落地。
“雖然每年阿里媽媽的價格都在漲,但作爲一個營銷平臺,它要每年找品牌收錢。但是品牌也有自己的對策,對吧?也不可能啥都參加。”一位不願具名的電商從業者這樣形容着阿里媽媽和商家間的生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花的多,當然也要幫商家賺得更多。
對於阿里媽媽來說,不破不立,新業務探索和內部調整正在悄然進行。
(文中柯子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