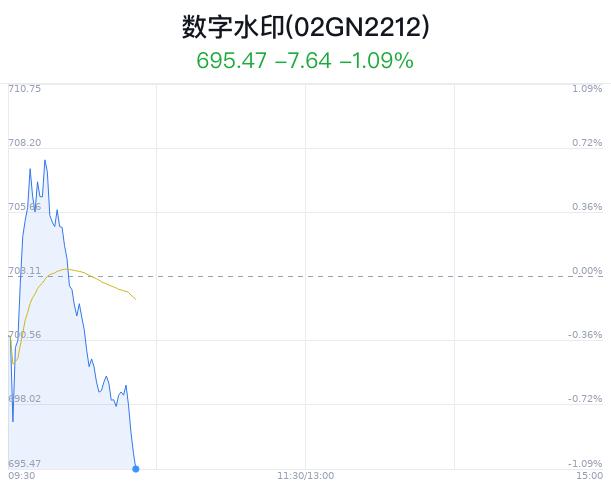我們的悲歡不相通,我們的趣味也不再相通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 看理想君。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你是否注意到?大衆娛樂正在悄然割裂。
全民型綜藝,越來越難誕生。
許多收益不錯的綜藝節目,可能只是在某個圈子內紅火;而不同圈層裏流行的暗語,卻比昔日的非主流火星文更難理解。
一部豆瓣9.6分的網劇,你可能根本沒聽說;而在長輩圈裏火爆的電視劇《娘道》,你也可能一集也看不下去。
在注意力已經成爲一種稀缺商業資源的當下,我們開始懷疑,人與人之間的審美越來越不相通。對興趣範疇之外的內容,也越來越沒有耐心。
即便各類豐富的資訊軟件、社交軟件已經提供了大量不同類型的資訊和內容,人們所獲取的資訊也同樣趨向割裂,因爲軟件精心設計的算法,讓不同興趣標籤下的人,幾乎無法相遇。
互聯網時代下,精心設計的內容分發算法似乎賦予了我們巨大的“自由選擇權”:從找到感興趣的領域,到屏蔽異己的聲音,都變得輕而易舉。
可是,這樣的選擇權,卻也很可能讓我們成爲漂流在信息孤島上的人。
一、使用抖音時,抖音也正在定義你
前幾天,看理想(作爲一家與時俱進又與衆不同的文化傳媒公司)做了一次徵集:抖音把你定義成了一個怎樣的用戶,給你推薦了哪些內容。幾乎是毫無懸念的,大家紛紛表示,自己並不是抖音用戶。
但從不氣餒的我們,還是努力挖掘了幾位抖音日活用戶進行了採訪。
有意思的是,採訪結果發現,即便大家都在使用抖音這款產品,但是所接收到的內容卻大相徑庭。
有人表示“抖音是最好的吸貓工具”,有人認爲“抖音是土味文化的最佳集合”,有人看到的抖音是“沙雕搞笑神器”,有人看到的則是“生活竅門集錦”,也有人把它視作“化妝視頻工具”……
甚至有人認爲,抖音是一種「後現代波普藝術」式的存在。
抖音陸超,一個極度後現代的存在
如此來看,因內容高度同質化而屢屢被詬病的抖音,實質上仍然是一個巨大黑洞。
因爲,在用戶無意識瀏覽的行爲之下,每個人都只能觸及到這款應用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內容。
這背後,其實潛在的就是一種千人千面的內容推薦系統。
當然,個性化推薦,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的操作。然而,抖音的內容分發模式,與過去並不相同。
衆所周知,Facebook、Twitter和微博也同樣存在推薦機制。但是,它們的推薦機制更多基於粉絲與粉絲之間的人際圈,即通過“我關注的人的興趣就是我的興趣”不斷擴大關注網絡。
而抖音的內容分發模式是“去中心化”:算法根據用戶行爲,愈加精準地推薦用戶會感興趣的內容。
抖音內容分發模式
具體來說,每個剛關注抖音的人,會被投放到一個資源池中,隨着用戶行爲(點贊、關注等)偏好的產生,繼而被算法繼續投放進一個更大的資源池。
所以,所有你看到的內容,基本都是由你過去發生的行爲所決定的。
這套去中心化的內容分發模式,能夠讓內容推薦越來越精準。但同時,內容的廣度卻難以保證,從而導致你看到的內容面越來越窄——你永遠只能看到自己已有興趣圈層中的內容,並且越陷越深。
這套邏輯之下,內容平臺並沒有讓大家的趣味更廣泛,反而更加窄化、圈層化。
二、次元壁,是如何形成的?
用戶需要什麼,頭條就分發什麼。這是頭條系資訊平臺的核心原則。
它的創始人曾在一次採訪中說:
今日頭條不是個媒體公司而是一家科技公司。因爲“我們不創造內容,我們不發表觀點”,並認爲頭條不需要主編,不教育用戶,不應該介入價值觀的紛爭,要剋制,保持對內容的不干涉。
可問題是,利用用戶的無意識行爲揣測用戶需求,真的合理嗎?
上個世紀中葉,不少傳播學學者指出,人們使用大衆媒體(如報紙、電視),除了獲取必要資訊,更多是爲了娛樂消遣。“遊戲傳播論”的提出者斯蒂芬森,也把大衆傳播視爲遊戲性的傳播:
人們讀報紙、聽廣播、看電視就像兒童玩過家家一樣,主要在於消遣娛樂,以便把自身從成人化的工作環境中解放出來。
《斯蒂芬森的遊戲傳播理論研究》
儘管人們本能地通過資訊娛樂自己,但也必須認識到,人們獲取資訊,應當得到的不只是娛樂。
可是,在“誰抓住了注意力,誰就抓住了商業資源”的邏輯之下,不斷革新的個性化推薦,就牢牢緊握資訊的娛樂屬性,從而獲取更多的注意力經濟。
而這種讓人“舒適”的內容分發模式,爲我們提供了便捷,卻也會把我們拉進所謂的“信息繭房”——人們越來越容易沉溺於自己的世界裏,不再寬容異己。
早在報紙、電視機時代,這種現象還沒有這麼明顯。電視臺,只有幾個,一檔電視劇有萬人空巷的能力。讀報紙,儘管最感興趣的可能是娛樂版,但出於本能,還是會把整份報紙瀏覽一番。那個時代,全民偶像是真的偶像,而不是錦鯉。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審美代溝,也沒有那麼大。
而如今,對信息的選擇權,史無前例地放在了我們的手上。
從屏蔽不感興趣的娛樂,到消除異己的聲音,都只需要輕輕滑動手指。
另一方面,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打破了時空限制。即便是社恐,也很容易在網上找到與自己愛好相似、觀念一致的人。社交媒體,又爲羣體互動提供了形態各異的載體。
可是,當我們舒適地使用社交媒體,瀏覽資訊軟件時,卻不可避免地進入一個“回聲室”:在“我的互聯網”上,我看到的觀點,皆是自己觀點的回聲,並認爲整個世界就是這樣(可參考梁文道談“知識的詛咒”)。
這無疑將導致:一方面,信息來源愈發閉塞;另一方面,則是鄙視鏈的出現。
精準的興趣匹配之下,人們更習慣於抱團取暖。各類社交媒體,逐漸形成自己的語言特性和氣質。人們會普遍認爲:虎撲=直男,豆瓣=廢青,抖音愛好者又自然看不上快手……
假如有一天,我們想跳出自己的圈子,瞭解其他羣體也沒那麼容易:我們必須強迫自己理解並認同他們的說話方式、價值觀和審美。而這又很容易造成不適感,致使我們退卻並轉而回到原來的圈層內。
此外,羣體之間又會在無意識中出現“極化效應”。
興趣部落會自發形成一定的審美共識,這套共識在羣體的作用下不斷偏激化,使黑白界限分明。比如,粉絲團之間的不定期罵戰;豆瓣上的惡意打分;彈幕上的毒舌嘴炮。
還有那些隨處可見的鄙視鏈:聽後搖的可能看不起聽民謠的;藝術片愛好者鄙視綜藝商業片……
可問題是,站在鄙視鏈兩端的人,可能並不完全瞭解對方的領域。
三、個性化推薦,還是審美層固化?
表面上,去中心化的算法帶來的是審美層面的固化,即人們會對興趣範疇之外的作品、話題表現得冷漠且無知。
但深層次而言,這種現象也正使資訊的嚴肅性被消解,公共話語空間被侵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把報紙視爲民主起源的重要推動力。因爲,報紙的傳播,讓大傢俱備了一定的共同經驗:這片土地上,正發生了什麼事;和我一樣閱讀這份報紙的人,都過着什麼樣的生活。
這種共同經驗,讓人們凝聚爲一個共同體,並提供了公共話語空間。
然而,個性化的信息推薦機制,卻在減少這種共同經驗——人們難以聽到不同的聲音,更開始逐漸對重要的公共議題失敏。
正如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一書中提到的:
民主社會的健康發展應當具備兩個條件。第一,人們對信息的接觸是不期而遇的。也就是說,人們能夠有機會閱讀一些計劃之外的內容,而不是隻看到他們想看的。
第二,大部分公民應當擁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經驗,對有普遍價值的公共話題有所瞭解。
《網絡共和國》
如今,當我們被算法左右,成爲一個被動的信息接受者時,我們很可能錯過許多重要的議題,導致某些重要問題無法得到重視。
當公共話語空間也被“極化效應”侵蝕時,面對公共議題,人們也越來越難以包容多元的聲音與價值觀。
值得慶幸的是,人們已經逐漸意識到,依靠算法實現“用戶主導內容”是一種僞命題:
2017年,人民網三懟今日頭條的算法。認爲今日頭條的去中心化算法模式,是在讓算法決定內容,並讓用戶陷入“信息繭房”。
個性、精準的推薦,在電商導購上能爲人提供極大的便利。然而,用在內容分發上,卻可能是促使內容同質化的重要因素。
在大衆化媒體的娛樂屬性下,人們本能偏愛那些能賦予感官刺激的內容。但是,利用無意識行爲揣測用戶需求,對用戶來說,是不公平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跳出大衆媒介的“迴音室”,需要的不只是寬容異己的心,更是思辨能力,以及保有對世界的好奇心。
或許,我們可以認爲,媒介就像一扇窗,當我們打開一扇窗子時,總是會留意窗外的景色,卻忽略了窗戶本身。殊不知,正是這扇窗子左右了我們看問題的視角和廣度。
因此,適時審視這扇窗子的形狀,顯得尤爲重要。
參考資料:
今日頭條與Facebook,兩個「技術中立者」的低頭(端傳媒)
智能算法分發:如何幫助抖音衝出短視頻混戰?(泰一數據)
極化效應:互聯網爲什麼讓我們越來越閉塞(董晨宇)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 看理想君。
*文章爲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網立場本文由 看理想© 授權 虎嗅網 發表,並經虎嗅網編輯。轉載此文請於文首標明作者姓名,保持文章完整性(包括虎嗅注及其餘作者身份信息),並請附上出處(虎嗅網)及本頁鏈接。原文鏈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72415.html 未按照規範轉載者,虎嗅保留追究相應責任的權利
未來面前,你我還都是孩子,還不去下載 虎嗅App 猛嗅創新!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