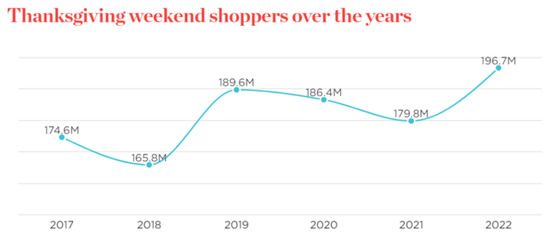這個感恩節,我們說點與“火雞”無關的……
原標題:這個感恩節,我們說點與“火雞”無關的……
Yee君說——
想到感恩節,我們第一個會想到火雞,這種動物爲什麼叫“火雞”呢 ?火雞被鳥類學家稱爲Meleagris gallopavo,這種動物本來就是新大陸上的物種,與土耳其這個國家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除了莫斯科鴨子,它是美洲唯一的本土家禽。“土耳其”(turky也代表火雞)背後的故事我們並不清楚,但這可能與一種錯誤的觀念有關,即這些鳥來自東方異域,以奧斯曼土耳其爲代表的一些國家。
有證據表明,在火雞這個品種與歐洲人接觸之前,美國人已經在美國西南部馴養過火雞了。17世紀,英國殖民者將馴養的火雞帶到了馬薩諸塞州和弗吉尼亞州,這些火雞也是一個世紀前由西班牙人帶到歐洲的墨西哥火雞的祖先。在歷史上,火雞差點在美國總統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想法下成爲美國的國鳥,正是這樣一種神奇的動物,每年它們其中的4600萬個同胞都會消失在感恩節的餐桌上。
當我們用炭火烘烤一隻17磅重的火雞,然後打開一罐蔓越莓醬汁的時候,這些意味着什麼呢?
這是一項歷時五年的民族誌研究中提出的問題。
該研究開始於1991年,它的研究對象是美國人的重要節日---感恩節。爲了幫助人們理解感恩節的含義,美國的兩位學者開始了這項研究,他們收集了關於這個一年一度的晚宴聚會(感恩節晚宴)的數據,他們對100名“參與者,同時也是觀察者”(主體是在校大學生)進行了一系列的深度訪談、調查反饋、照片幾率和現場採訪。他們發現,小的災難性話題(颶風或者車禍等)和那些陳年舊事是傳統感恩節聚會中的必備話題。兩位作者寫道:“感恩節的慶祝活動是非常複雜的,食物和人的數量在符號學上展現出了很高的密集性,以至於很多事情並不會按照宴會主人的計劃進行。”
大家都知道,如果烤箱還沒有到達設定溫度或大家忘記冷置香檳的時候,宴會的主人就是那個需要用隨機應變來應對一切的人。研究人員發現,尤其在感恩節那天,人們需要的其實反而是忘記一些料理瑣事:比如放在烤箱裏的麪包卷,或者如何做好一盤法國炸洋蔥。
他們解釋說:“忘記很多瑣事是宴會豐盛帶來的一種可以理解的結果。”“在這個年度聚會上大家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喫,有些不重要的事情就被忘記了,分析這個現象會讓大家對富足的重要性進行充分的討論,這個研究解釋了什麼纔是感恩節上真正重要的東西”。
從我記事開始,我對家中的感恩節的氛圍就只有一種記憶:憤怒。在我繼父家裏,爐子似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當我的母親帶着我們和心形的小蛋糕搬進這個家時,我的繼父的冰箱裏只有一個乾癟的蘋果和櫥櫃中的一罐花生醬。我們搬來來後不久,天然氣公司就打來電話詢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你們家中的天然氣使用量最近異常的高,是否需要我們來檢查下是否有天然氣泄漏的情況呢?我媽媽像一直正在歌唱的黃鸝一樣對工作人員說:“哦,沒有的事情呀,我一天就要泡17杯茶呢。”她讓被遺忘的爐子重新找到了它的的價值,然後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那年的感恩節。
在感恩節那天的早些時候,我幫忙把家裏的桌子拼在一起,以便爲30個人騰出用餐的位置,在我看來,來我們家參加感恩節晚宴的一半人是彬彬有禮的流氓,另一半則是無害無用的年輕人。我的同父異母兄弟邀請了一羣穿着破洞衣服的純素食音樂家,他們帶來了一個大火雞, 西坦肉汁和一個平底鍋,跟着他們一起來的還有一個豐滿的女人,在喫完餡餅後,她吹噓自己可以用乳溝給自己塗口紅。人們在桌上似乎就墜入了愛河,我記得有一年在家裏,喫完飯後我們把桌子放好後,繼父就開始在石頭壁爐前開始主持婚禮儀式,類似這樣搞笑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在那幾年裏,我沉迷於各種聚會,卻忽視了自己的工作。我的母親在感恩節晚宴上會站在桌子的最前面,像許多女孩子一樣托起一杯沃爾福德紅酒。這個姿勢是如此的溫柔、輕蔑而又沾沾自喜,就像眼前所有的一切——金胸鳥、冰涼門廊上的酒桶、喧鬧的人羣,看似熱鬧卻是一片虛無。
有她的晚宴就是一場精彩的演出,直到幾年之後,我才意識到這一天是上天贈送給她的禮物。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感恩節是一種跨文化的聚餐。多虧了美洲土著種植玉米的技術,讓一頓簡單的晚餐(以及冷死人的冬天)變成了一場盛宴,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因爲一場歡樂的盛宴而團聚在一起。他們在那天放開的大喫大喝是因爲當人們聚在一起開始有目的的喫東西的時候,就會促成一些重要的事情的發生。
安德魯·f·史密斯在《美食評論》上寫道:“沒有人會比清教徒對這些現代信仰更爲感到驚訝。”不過有人可能會說,萬帕諾亞格民族的祖先也會對這個故事的由來感到驚訝。該地區三分之二的土著居民在1617年的一場瘟疫中喪生,而這場瘟疫是由歐洲商船上的船員帶來的。自1970年以來,在馬薩諸塞州的普利茅斯,感恩節那天人們會舉行相關的抗議和哀悼活動。
今天大多數美國人慶祝這一節日的方式並沒有反映出飲食對於這一天的重要性。正如安德魯·f·史密斯在書中寫道的:無論1621那年發生了什麼,清教徒對這個數字都不會有太多的記憶。他們並沒有在後來過多的想起1621年的秋天,也沒有在之後去紀念它。”
他們可以忘記這些歷史,但他們不能否認的是他們確實渡過了豐衣足食的1621年。他們能在冬天大喫大喝是因爲他們有一個豐收的秋天。這也是歷史上人類一直經歷的事情,當氣候宜人,莊稼長勢很好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在上天的照顧下再苟活一年。人類在世界各地舉行了數千年的慶祝豐收的傳統盛宴,如猶太節日蘇科特節和希臘的哈羅阿節(爲了紀念女神德墨忒爾)。當然還有中國的中秋節,美國原住民的玉米節,以及非洲收穫節,在這之後就是寬扎節。他們在某個特定的節日上大喫大喝,是因爲當人們聚在一起喫飯時,除了填飽肚子之外還有其他更深層次的意義。
“與‘盛宴’最爲相關的動詞應該是‘給予’”,奧康納在小說中寫道。“盛宴不應該只是一種聚會的行爲,而應該是以一種禮物的方式贈送給對方的東西。”我對這句話可以說是深有感觸了:當我的母親和繼父步入婚姻的第二個十年時,家中的感恩節氣氛已經變得相當成熟。而我也已經長大了,所以當我低頭看着那張鋪着白色亞麻布的長桌,看着母親烤完麪包之後又舉起酒杯的時候,那幾盤火雞和好喫的調料突然顯得無關緊要了。
她所創造的,或者說她所給予的已經不只是一頓飯那麼簡單了,對我來說更多的像一個容器,一個可以容納我們人類需求的容器。它可以容下的東西有很多:我們渴望抱起一個嬰兒,想象着這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向長輩詢問着職業上的各種建議,然後過幾天忘得一乾二淨;我們在必要的時候變得急躁和憤怒。
在我母親去世後的第一個感恩節早上,天上開始下起了小雪,雪花落在樹枝上,但並沒有融化。我從雜貨店開車回家,我的箱子裏裝滿了好幾袋的火腿、小紅莓、10磅土豆和兩隻火雞。當雪開始落在田野上,當大雪落滿八月的玉米和僅剩的乾草,不知道爲什麼,這些讓我想到了母親在草地上忙碌的樣子,而她的軀殼卻已經在松木盒子裏瑟瑟發抖了。
這一年對我來說,感恩節已經變成了一場葬禮聚會。對墳墓的構建揭示了埃及人將死者埋葬在一起的奢華晚餐的意義:烤鵪鶉;各種紅燒的肉類;一籃子的無花果、葡萄、棗子和堅果。
沿着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玻璃走廊走下去,你就會看到一隻保存了3500年的烤鴨。在古羅馬,葬禮上的盛宴意味着餐桌上的食物變成了“人間與陰間世界的交流”,而活着的人們則在屍體旁進餐。這種進食是一種讓靈魂安息的方式,讓這些靈魂在前面未知的道路上繼續安心的前行,換句話說這頓飯將生者和死者的王國連接在一起。對於悼念者來說,在這樣的時刻一起喫飯避免了讓他們在悲傷中過多的感受到死亡的恐懼。“在這樣一個時代,在死亡的神祕黑暗之前,數字和親屬關係是最舒適的伴侶,”簡·列維在《美食》雜誌上寫道。
感恩節那天,我彷彿成了母親的化身,我在她的櫥櫃裏翻來翻去,尋找那隻用來盛火雞的藍色搪瓷器皿。我在碗櫥裏發現了她的擀麪杖,而家裏的糖也已經用完了。前一年,我還在她身邊做飯,也方便我學習如何烹飪——她教我如何用錫箔紙蓋住火雞胸肉,並均勻攪拌肉汁。我應該在那時做些筆記的,有些關鍵的東西我都忘了。
“你看,這些沒什麼難得。”她在爐子旁對我說道,她從烤箱手套裏抽出手來,環顧四周的客人,他們喫着奶酪,喝着酒。當然,我依舊還是在爐子前哭了一陣子,這是感恩節的傳統。當我們在桌旁坐下時,我的繼父做了個優雅的手勢,然後他習慣性的提到了那些已經無法跟我們共進晚餐的人。我又一次低頭看了看那擁擠的桌子,覺得自己完成了一個漂亮的魔術戲法。每個盤子都裝滿了美味的食物,每個客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口的喫着晚餐。那一年我們度過的時光,以及我們在每個假日的聚會上磕磕絆絆度過的時光,都被一種像假肢一樣的東西所困擾,這些就是我們所有記得的東西。
END
作者:Sarah McColl/Matthew Wills
原文標題:
Thanksgiving Is a Feast of Things Forgotten/Let’s Talk Turkey
譯者:Sara Yang
編輯:楊柿子
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在譯言整合發佈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