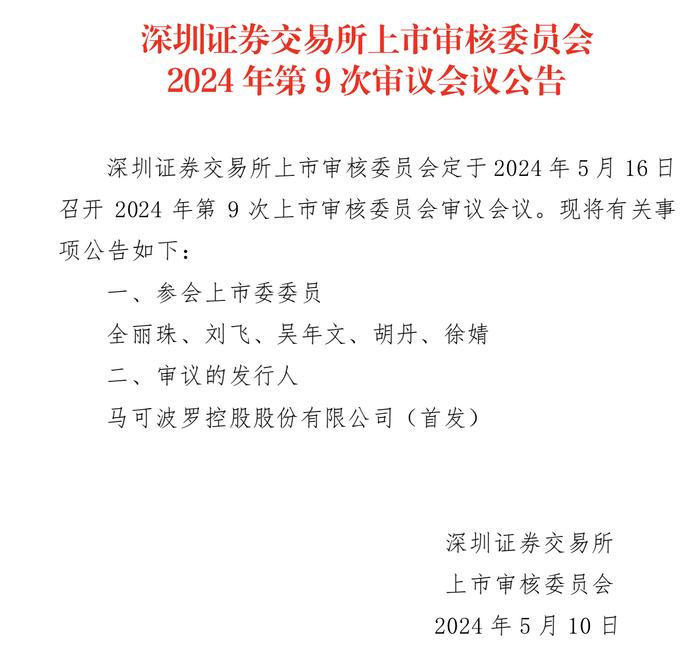只为争个面子,苏联人任性起来,居然要举全国之力仅盖一座楼
1988年11月15日,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发射成功。这款航天飞机的设计理念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不但可以多次回收利用(额定飞行寿命是100次),如果在降落时遇到情况,还能抬升并进行二次降落。即便这款飞行器是否属于航天飞机之列,一直饱受美国方面质疑,但显而易见的是,“暴风雪”是苏联专家们智慧的结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配合这款飞行器的研发,苏联还研发了安-225“梦幻”运输机。“梦幻”全球仅有一架,这也足以让其成为世界上尺寸最大的飞机。
整个“暴风雪”项目疯狂地烧掉了苏联超过200亿美元的经费,大大加速了苏联的毁灭,但我们仍不得不承认,苏联人在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天赋实在是令人艳羡。不过,我们早就熟知这一点了,这篇文章便不再多做赘述;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在苏联时代的建筑中,看看当年苏联人在建筑上疯狂到了何种地步。
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都会诞生出不同风格的建筑,就拿咱们来说,在上一波城市化浪潮中,数不清的多层建筑拔地而起,如今,这些灰色墙壁、红色房顶(或是平顶)的低矮建筑俨然成了不少城市的“贫民窟”,许多城市还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大搞棚户改造。历史上,苏联也有类似的建筑,这些建筑带有极强的时代特征,搁在城市里让人看了如骨鲠在喉,十分难受。不同的是,这些建筑非但不跟老旧沾边,反而十分宏伟,往往被视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分散在许多国家的各个角落,大多却并不怎么受待见,这是咋回事?
在许多波兰人眼里,华沙科学文化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异端”,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国家的耻辱,恨不得将这座建筑炸毁。然而,华沙科学文化宫的大楼却是这座城市的一大地标建筑,狠狠地烙印在了这座城市的生命中。但从外观来看,这座建筑可谓是辉煌宏伟,一点也不难看。但这类体量庞大、尖顶高耸入云的建筑有个统一的名字——斯大林式建筑。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类风格的建筑开始在苏联国内建设。除了我们上述的华沙科学文化中心外,如全苏维埃博览中心、“莫斯科七姐妹”和莫斯科国立大学等都是这种风格建筑的代表作。这类建筑讲究布局对称,外表富丽堂皇,高耸入云,风格单一但却十分震撼,旨在“赞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秩序,显示共产主义革命激情与荣耀”,具有极强的政治指向性和意识形态特征。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斯大林式建筑并不难看,但在苏联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这类建筑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泛滥,将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与帝国风格等元素杂糅在一起的建筑风格照搬照抄,极大地破坏了许多城市整体的建筑风格,加上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这类建筑如今已变得有点像“过街老鼠”,根本不受市民们待见。
就拿莫斯科国立大学中那座最显眼的36层建筑来说,据说这座庞然大物中建有长达20英里的长廊(约等于32千米,当然有夸张的成分),历史上,当这座建筑落成后,不少人诟病它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搞教育的场所,更像是一座高档酒店。这样一座建筑放在大学里,简直就是极大的浪费。结合特殊的历史背景,斯大林式建筑也往往被视为大搞个人崇拜、为面子不顾一切以及苏联粗放式发展模式的象征。然而相比这类建筑最终极、最疯狂的建造计划来说,我们上述列举的这些例子根本不值一提。
1931年,斯大林下令炸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东正教堂——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这座教堂先后历经44年才彻底完工,于1887年启用,高约108米,即便是放在20世纪30年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建筑。苏联人炸掉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目的是为了在遗址上建立另外一座更加庞大的建筑——苏维埃宫殿。按照设想,这座建筑无论如何,在高度上都要压过美国的帝国大厦,宫殿四周的广场面积要超过红场,这座建筑一定要展现出“苏维埃世界共和国”、“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中心”等宏伟构想。为此,苏联打开门户,向全世界征集了超过400份建筑设计方案,1930年,苏联高层最终作出决定,要把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这座“不太苏维埃”,不够共产主义的建筑炸掉,用总高约415米的苏维埃宫殿取代。
这段历史相当有趣:最初,苏联高层只是希望新建筑的高度要超过克里姆林宫,但最终将计划定为世界第一建筑是有政治指向性的,那便是压过其他所有国家标志性建筑,以突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苏维埃宫殿的疯狂不仅仅体现在高度上,要知道,苏联人打算在大厦顶上树立一座高达75米的列宁镀金全身雕像,以求力压自由女神像,从精神上压美国一头。为了建造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斯大林几乎调集了全国的资源。集一国之力修建一栋楼,这样疯狂的事情恐怕也就只有苏联能做得出来了。然而,当时的苏联并不太富裕,加上不久后二战就爆发了,苏维埃宫殿的修建计划就此搁浅。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教堂没有了,但很多俄国人对它仍念念不忘。许多老年人经常跑到教堂的遗址旁边静静地坐着,注视着已经被夷为平地、渐渐长满野草的空地。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此十分不满,终于下令将这块平地修建成一座巨大的泳池。1995年,为了纪念莫斯科建城850周年,市政府又投入2亿重建大教堂。(这种拆完后悔又重盖的做法我们或许并不太陌生,比如令人惋惜的济南老火车站)
如果说苏维埃宫殿的建筑计划是疯狂,那么第三国际纪念塔则实属“丧心病狂”了。从1919年开始,第三国际纪念塔这一建筑计划就已经被开始考虑,这比苏维埃宫殿还要早。它的建筑计划由建筑师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提出。第三国际纪念塔中心体由一个玻璃制成的核心、一个立方体、一个圆柱共同组成,这个巨大的玻璃体倾斜悬置在一个不对称的轴座上面,四周环绕钢条做成的螺旋梯子。巧妙的是,这个巨大的结构会转动,并且每年绕轴周转一次;圆筒内部不同结构也有不同的周转速度,有的一周转一周,有的一个月转一周。
第三国际纪念塔的体积和高度更加吓人,如果该建筑落成,高度将超过帝国大厦整整一倍(这样一来,少说也有700米了)。苏联计划将该建筑作为一个巨大的信号塔,落成后夜以继日地向世界传递革命的声音,不断地用电报、电话、无线电、扩音器等方式向全世界发布新闻、公告和宣言等。这么大一个玩意儿居然能够整体转动,就算是放在今天,想要修建出来,恐怕真的比登上月球还难。可怕的是,苏联人居然拿出了设计方案并已经开始做开工的前期准备工作了。不幸的是,根据估计,苏联当时的钢铁产量根本不足以支撑建筑计划,加上后来遭遇战争,第三国际纪念塔与苏维埃宫殿一样,最终都不了了之了。不过两者不同的是,苏维埃宫殿作为斯大林式建筑的终极构想,非但不太被西方人待见,反而被视为苏联式集权政治的象征;第三国际纪念塔则被视为一种至高的艺术追求,其透出的强烈的毕加索立体主义和建筑构成主义特征,备受世界艺术界推崇。
当然,上述这些建筑不过是苏联人对建筑极端追求的冰山一角而已,但随着苏联的解体,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独特的历史狂潮已然渐渐退去,这些遗留在不同国家各个角落里带着鲜明的政治指向性、风格奇葩的建筑俨然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话题。有人已经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并开始欣赏它们;有人则认为这些建筑不但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整体性,甚至还把它们视为异类和败笔。即便如此,苏联人天马行空的创造天赋和敢于尝试将一切设想变为现实的勇气,仍然值得我们佩服。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