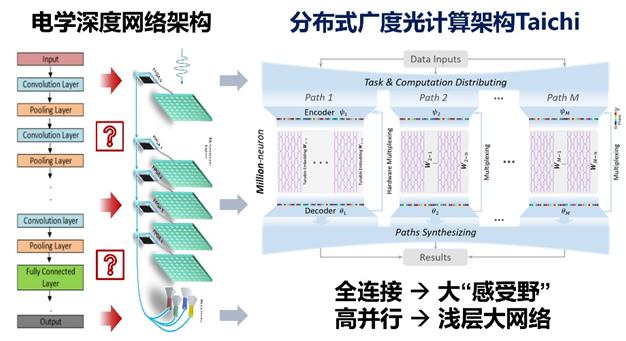於秋水長天處尋味——寫在朱自清誕辰120週年之際
朱自清澄明、乾淨的文章境界值得後人追摹,他對新學術的發生與拓展也起到示範作用,堅持爲大衆寫作、爲中學生編書、大專家寫小文章,雖非一時耀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其精神價值更恆久,也更耐人尋味
世人眼中,朱自清是詩人、學者、散文家,也是戰士。可還有一重身份不該被忽視,那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在我看來,此乃其做人做文做學問的底色。一生如此短暫(1898—1948),居然有那麼多功業,去世多年仍被人掛念與懷想,這很不簡單。
1920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暑假後開始教書:先在杭州第一師範,後移至揚州八中、吳淞中國公學、台州六師、溫州十中、寧波四中、白馬湖春暉中學;1925年秋,因清華學校加辦大學部,轉任國文系教授,開始其大學教師生涯。不同於今日讀研究生、拿博士學位的專門家,朱自清在北大唸的是哲學系,日後教的是語文或中國文學史,按今天的標準,專業還不太對口呢。先是寫詩作文出名,而後才進入大學教書,興趣廣泛,自強不息,有一點始終沒變,那就是堅持爲大衆寫作,爲中學生編書。如此大專家寫小文章,從沒感覺掉份,反而樂此不疲。
五年中學教員生涯,輾轉各地,很是辛苦,但鍛鍊了朱自清的生活態度與寫作策略。做事認真,爲人謙和,腳踏實地,不尚空談,這種生活姿態,更接近於恬淡的散文,而不是激揚的詩歌。因此,不妨就從朱自清最廣爲人知的散文家身份說起。
尊重讀者 透澈爲文
朱自清的散文特別受中學教師的青睞,且很早就進入各種《語文》教材。有政治家的推崇,也含新文學的升溫,但更關鍵的,還是因其文章風格以及寫作策略。教過五年中學語文,成爲大學教授後的朱自清,依舊關注中學生的閱讀。《歐遊雜記·序》稱:“本書絕無勝義,卻也不算指南的譯本;用意是在寫些遊記給中學生看。在中學教過五年書,這便算是小小的禮物吧。”別小看這爲中學生寫作的立意,文學史家王瑤便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稱讚此書“用精練的口語,細細地談着,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聞其聲”。若再考察《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語文影及其他》等後期寫作,均混合評論、隨筆與雜感,既是學問,也是文章。讀者多欣賞朱自清描寫風景的《荷塘月色》《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以及抒寫人情的《背影》《給亡婦》等,這固然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但我更喜歡他那些談古論今兼及社會問題的作品,肯爲讀者着想,從不逞才使氣,偶爾也會來個隱喻或排比,但筆墨極爲簡潔。
在《〈胡適文選〉指導大概》中,朱自清曾表彰胡適對中國文學的最大貢獻,不是新詩,而是文章:“他的長篇議論文尤其是白話文的一個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動人’,可以說是‘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而以下評語,其實可套用來評說朱自清本人的文章:因爲曉得尊重讀者,故“他的說明都透澈而乾脆,沒有一點渣滓”。這種澄明、乾淨的文章境界,很是難得。
多年前,季鎮淮在《回憶朱佩弦自清先生》中稱:“作爲文學的散文,朱先生努力運用語言文字而得其自然。作爲國學的著作,他對運用語言文字亦非常努力,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指出。”這裏說的是抗戰中完成的《經典常談》。朱先生在此書的序言中謙稱:“各篇的討論,儘量採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編撰罷了。”此等提要鉤玄的工作,除了眼光與學識,還得有好的筆墨情趣。以“文第十三”爲例,開篇是“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結束處則是“經過五四運動,白話文是暢行了”,整個一部中國散文史,用萬把字篇幅說清楚,條分縷析,井然有序,而且大致不錯,這談何容易。
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堅實的成果是白話文,而如何“白話”,是個大問題。必須兼及“白話文學”與“白話學術”,方纔可能長治久安。不說詩歌戲劇小說,單是文章如何借鑑口語而不流於鄙俗,朱自清的苦心經營便值得後人追摹。這與日後葉聖陶提倡“想得清楚,說得明白”的《寫話》,頗爲神似。
關注當下 着眼民間
朱自清生前編定的最後一書《語文影及其他》,收錄有《說話》《撩天兒》《如面談》《論廢話》等十則分辨語詞的短文,該書的序言,開篇即自報家門:“大概因爲做了多年國文教師,後來又讀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書,自己對於語言文字的意義發生了濃厚的興味。”至於公開表態追摹燕卜蓀,更是在此前十幾年。《詩多義舉例》(1935)中,作者稱:“去年暑假,讀英國的Empson的《多義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覺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試用於中國舊詩。”在文史研究中,將語義分析和歷史考據相結合,朱自清的《詩言志辨》大獲好評。
《詩言志辨》確實是朱自清的代表作之一,可我還是更關注其學術起步階段的《中國歌謠》與《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1928年8月17日,國民政府決定改清華學校爲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楊振聲和朱自清多方規劃,希望突出自家面目——“那時清華國文系與其他大學最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會”。緊接着,就是朱自清的大動作——1929年春季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秋季講授“中國歌謠”。這兩門讓人耳目一新的課程,同時出現在國立清華大學剛剛誕生的1929年,並非偶然。
據浦江清《〈中國歌謠〉跋記》:“朱先生在清華大學講授‘歌謠’這課程是從1929年開始的,在當時保守的中國文學系學程表上顯得突出而新鮮,很能引起學生的興味。”至於《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早年只是作爲講義在師生間流傳,真正整理面世,遲至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2月推出的《文藝論叢》第十四輯。
一個是悠久但卑下的“民間文學”,一個是年幼而生氣淋漓的“新文學”,這兩門新課的開設,其實是服從於或者說得益於新大學的崛起。關注當下,着眼民間,努力介入思想建設與文學革命,讓清華中文系迅速獲得生機與活力。這不僅是一兩門新課程,更牽涉對大學中文系的定位,1931年的《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概況》開宗明義:“本系從民國十七年由楊振聲先生主持,他提供一個新的目的,這就是‘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朱自清批評其他大學國文系“他們所要學生做的是舊文學研究考證的功夫,而不及新文學的創進”。這裏的鋒芒所向,包括高傲且保守的北大中國文學系。楊振聲、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是北大出來的,當然明白挑戰老大哥,必須找到很好的角度與策略。
因當年各大學尊古之風盛行,這兩門多有創見的課程,沒能長期堅持。但其篳路藍縷,對新學術的發生與拓展,起了示範的作用。半個多世紀後閱讀,依舊很有新鮮感。
誠摯律己 勤勉篤實
曾在清華大學修過朱自清三門課的小說家吳組緗,在《敬悼佩弦先生》中稱:“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着講稿,一手拿着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着紅。”朱自清講課極爲認真,甚至到了有點拘泥的地步。季鎮淮回憶在西南聯大念研究生時,旁聽朱先生講授“文辭研究”專題課,臺下就王瑤一個學生,他依舊認真板書。師生倆一個寫一個記,此舉既見學風,也顯性情。
閱讀朱自清日記,特別感慨其自我要求甚高,故內心十分緊張。雖長期擔當清華中文系主任,在學界及社會上聲譽日隆,日記中卻是不斷地自我檢討。1936年3月19日日記:“昨夜得夢,大學內起騷動。我們躲進一座如大鐘寺的寺廟。在廁所偶一露面,即爲衝入的學生們發現。他們縛住我的手,譴責我從不讀書,並且研究毫無系統。我承認這兩點並願一旦獲釋即提出辭職。”這可不是偶一爲之,請看以下日記——1931年12月5日:“這兩天夜裏做了一些奇怪的夢。在其中一個夢裏,我被清華大學解聘,並取消了教授資格,因爲我的學識不足。”1932年1月11日:“夢見我因研究精神不夠而被解聘。這是我第二次夢見這種事了。”可以和這些夢境相呼應的,當屬1935年1月17日的日記:“浦告以昨晚我醉後大講英語和日語,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現。”如此不堪的夢境與醉態,朱自清居然都記錄在案,目的是自我警醒。其實,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如此律己過嚴,或許與他的胃病互爲因果。
同樣談古論今,胡適之寬容,聞一多決絕,朱自清通達(有時優柔寡斷),這都與個人性格及才情有關,勉強不得。1922年在臺州教書時,朱自清撰寫長詩《毀滅》,很能見其趣味與立場。此詩備受文學史家重視,但在我看來,這與其說是精美詩篇,不如說是人生宣言:“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在《背影·序》中,朱自清說過:“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類似的意思,他在很多地方提及。你以爲是矯情,不是的,他真的就這麼想。性情平和的朱自清,在現代作家中,才氣不是很突出,可他一直往前走,步步爲營,波瀾不驚。《毀滅》長詩的最後是:“別耽擱吧,走!走!走!”如此坦誠、篤實、勤勉,很讓人感動。
有人習慣急轉彎,有人擅長回頭看,有人喜歡三級跳,朱自清則始終穩紮穩打,有堅守有追求也有收穫。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在立達學園、春暉中學、開明書店共同奮鬥過的朋友,如葉聖陶、豐子愷、朱光潛、夏丏尊等,都是低調的理想主義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短期看,並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與毅力。世人多喜歡絢麗的彩虹,那固然搶眼,可也迅速消逝;另一種景色,秋水長天,看似平常,但更恆久,也更耐人尋味。
(作者陳平原爲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製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8年11月23日 24 版)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