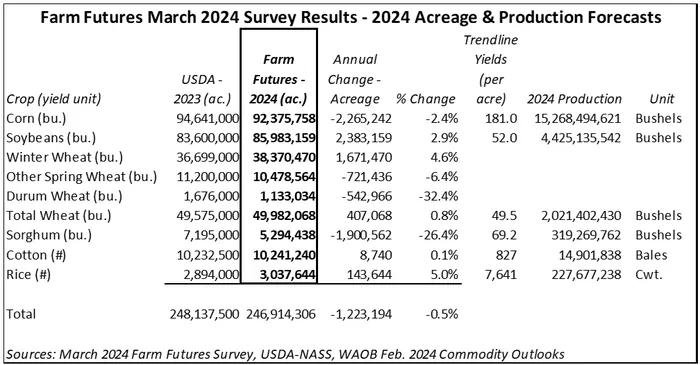逆行 | 太宰治
“Interior. Sunny Day”Stanislav Zhukovsky
/ 太宰治 /
不算老頭兒。二十五歲多一點而已。可的確又是個老頭兒。別人一年一年地過,這人是三倍三倍地過。自殺過兩次,沒成,其中一次爲殉情。看守所進了三次,罪名是思想犯罪。他寫了上百篇小說,一篇也賣不掉。不過,大家知道老頭兒志不在此,所謂放馬閒喫道邊草罷了。能在老頭兒乾癟胸肌上撞出迴響的是這些事:喝個爛醉,把一張刀條臉變成赤紅;流着口水看各色女人,一面浮想聯翩。就這倆事。不,想得起來的事就這兩件。乾癟的胸肌和刀條臉,說得更明白點兒,這位老頭兒,今天死了。在老頭兒漫長的一生當中,能說明白的事就兩件:生和死。死之前所有的事全是謊言。
這會兒,老頭兒還在病牀上。病是玩出來的病。老頭兒有一筆可保衣食無憂的財產,可也是一筆稍加揮霍就見底的財產。眼下,老頭兒快要死了,他一點都不遺憾;對老頭兒來說,節衣縮食度日纔是不可理喻的。
一般人在臨終前,或是凝視自己的兩隻手掌,或是仰望親人的眼眸。這位老頭兒則基本上在閉目養神,眼睛閉得死死,眼皮卻是鬆弛的,還不時地哆嗦幾下。看上去,這事像是滿舒服的。他看見了蝴蝶。綠色的蝴蝶,黑色的蝴蝶,白色的蝴蝶,黃色的蝴蝶,紫色的蝴蝶,水色的蝴蝶,成千上萬只蝴蝶在他頭頂上方麇集、飛舞。它們專程而來,雲霞般地綿延百里,上百萬只蝴蝶一起煽動翅膀,聲音聽起來有如正午時分嗡嗡的牛虻。想必是一場混戰吧:化成粉末的羽翅,折斷的細足,眼珠,觸角,還有它們的長舌頭,紛紛墜落下來。
“想喫點兒什麼?什麼都行。”有人問他。
“小豆粥。”他回答。
老頭兒十八歲起寫小說。“一個快死的老頭兒喃喃道:給我小豆粥……”,他寫過這樣的情節。
小豆粥熬好了。粥裏摻了煮小豆和一點鹽,就是這種風味。鄉間的家常飯。老頭兒面朝上,眼睛依舊閉着,喝了兩羹匙就說夠了。問他,還要點什麼?他淡淡地笑笑,說:“想玩兒。”老頭兒的妻子是個好人,年輕漂亮,沒什麼知識卻心靈手巧,當着衆親屬的面脹紅了臉。她並不喫醋。她一聲不響地握着羹匙,哭了。
“Ornate nasturtium background.” Etude de la plante. 1903.
盜賊
今年鐵定考不上了。可還得考考看。徒勞之美。那種美吸引了我。今天早早就起來了,套上足有一年沒穿的校服,從鑲嵌着菊花徽章的高大鐵門溜了進去。誠惶誠恐地溜了進去。一眼看見了銀杏樹。右側十棵,左側也是十棵,株株粗壯,在枝繁葉茂的時節,整條路被樹蔭遮住,黯淡得像是地下道。這會兒一片樹葉都沒有。林蔭路盡頭,有座正面鑲紅磚的高大建築是講堂。我在入學式那天進去過,就那麼一次。留下的印象宛如寺院。我仰頭看了一眼講堂塔尖上的電子鐘,距離考試還有十五分鐘。這裏有座“偵探小說之父”(所指不詳,一說是江戶川亂步。待考。譯者注)銅像,眼神裏滿是慈愛,我一面看着它,一面沿着右側的緩坡朝下走,進入一座庭園。這庭園過去的主人是一位諸侯。池塘裏有鯉魚、緋鯉和甲魚。直到五六年前,還養着一對仙鶴,草叢中有蛇,而大雁、野鴨一類候鳥也飛來池塘邊棲息。庭園的面積實際不到二百坪,看上去卻有一千坪,全憑造園藝術之妙。我挨着池塘邊的一叢山白竹坐下來,背靠一株古櫟樹,兩腿朝前長長地伸出。大大小小、凸凹有致的岩石分佈在小徑上,池塘就從它們的背面舒展開去。陰雲下,池塘表面銀光閃閃,害臊似地泛着漣漪。我把左腳輕輕搭在右腳上,喃喃自語:
―― 我是盜賊。
前方的小徑上,排隊走來一羣大學生。他們一個接着一個,流水一般源源不斷地走過去。各個都是家鄉的驕子,脫穎而出的秀才。這些人都叫大學生,讀筆記本里一模一樣的文章,下同樣的苦功把它們硬塞進腦袋。我從衣袋掏出香菸,叼上一根。可沒有火柴。
―― 借個火。
我瞄準一個挺帥的大學生喊了一聲。身上裹着淡綠色外套的大學生站住了,眼睛不離筆記本,隨手給了我一根金過濾嘴兒香菸。給我煙時他連腳步都不停,踢踢踏踏仍往前走。居然在大學裏碰上了對手。這根金過濾嘴兒外國煙激發的怒火足以點燃我的低檔煙。我慢吞吞地站了起來,用力將金過濾嘴兒香菸甩到地上,憤憤地用鞋底踩,碾成了粉。之後才舒舒服服地現身考場。
考場有上百名大學生,他們全都拼命往後坐。這就造成了一個懸念:答案是有的,可要是靠前坐,那就寫不出來了。我像個秀才似地坐在了最前排,抖着指尖抽着煙。我的課桌下面沒有可供查閱的筆記本,也沒有可以相互低聲探討問題的朋友。過了一會兒,一位紅臉膛的教授,提着個圓鼓鼓的公文包急匆匆地撞進考場。此人乃是日本頭號法國文學專家,我還是頭一回見到他:身材高大,眉宇間的皺紋讓我莫名地緊張。據說,此人的學生中出了一位全日本頭號詩人,還出了一位全日本頭號評論家。而我挺看好“全日本第一小說家”的,想得臉發燒。教授用黑體字飛快地寫着考題。這功夫,我背後的那些大學生們,拋開課業,嘁嘁喳喳地聊起了肥沃的滿洲。黑體字裏寫了五六行法文。教授頹然坐在講壇的扶手椅上,很不高興地來了一句:
―― 像這種題,你想考砸都很難。
大學生們悶聲一笑。我也笑了。接着,教授用我聽不懂的法語發了幾句牢騷,開始在講壇的桌子上寫着什麼。
我不懂法語。我想好了,不論怎麼出題我都這樣答:福樓拜是個孩子。我假裝想了一會兒,閉上眼睛,從短髮上往下抓頭皮,又看了看指甲的色澤。然後拿起筆來開始寫:
―― 福樓拜是個孩子。學生莫泊桑是大人。到頭來,藝術美要服務於市民口味。很悲哀很無奈,福樓拜不懂可莫泊桑明白。自己的處女作《聖·安東的誘惑》遭受惡評,讓福樓拜引爲恥辱,把一生都毀了。就是說,辛辛苦苦寫了一篇又一篇,評價如何另論,屈辱的舊傷可是越來越重,痛,針扎般的劇痛在他內心開了個洞,越來越寬,越來越深,直到他死。他被傑作的幻影騙了,被永恆之美迷惑了,給這對近親愚弄得飄飄然,最終也沒掙脫出來。所以說,福樓拜是個孩子。就這些。
我可沒寫“先生,讓我及格吧”這類話。我把所寫反覆讀了兩遍,沒有錯。於是,我左手拿起外套跟帽子,右手拿上那張答題紙,站了起來。我一站起來,身後那位秀才嚇壞了。因爲我的後背被他當防風林來用了。哇!這位像兔子一般可愛的秀才,在答卷上寫的竟是一個新銳作家的名字。新走紅的名作家,我一邊憐憫地想着他的狼狽相,一面意味深長地衝着教授施了一禮,交上我的考卷。我靜靜地出了考場,下樓則快得跟骨碌下去似的。
來到戶外,年輕的賊不禁有些傷感。這愁緒是怎麼回事,它打哪兒來?我把外套搭在肩膀上,甩開大步穿過兩排銀杏樹剪出的一條碎石路,走着走着有了答案:餓的。二十九號教室往下走,是個地下大食堂。我徑直朝那邊走去。地下室大食堂那兒擠滿了餓肚子的大學生,從入口處排起了長蛇隊,從地下冒到地上,隊列的尾部都已經伸到銀杏樹那邊去了。在這兒,十五個錢就能喫上相當不壞的午餐,遂有了這個長度。
―― 我是賊。稀世的怪物。沒殺過人的藝術家。沒偷過東西的藝術家。而我屬於有點無聊小聰明的那種。
我被人羣一點一點推擠着向前走,總算來到了食堂入口。那兒貼着一張小告示,是這麼寫的:
今天喜迎食堂創業三週年,爲表祝福,特備少量降價食品,望周知。
特賣品擺放在入口旁邊的玻璃架子裏:燒紅的對蝦在荷蘭芹葉子下邊睡着,煮雞蛋對半切開,截面上用綠洋粉刻着花哨的“壽”字。放眼朝食堂裏邊看,扎堆兒買便宜的大學生儼如黑色叢林,而繫着白圍裙的服務小姐們穿梭其間,翩翩起舞。哇哦,從天井往下看,整個兒一面萬國旗。
大學地下也有這麼個浪漫玩意兒,夠開眼的。今天是碰巧來對了。同喜同賀。同喜同賀。
我這個賊,落葉似地退出了地下,飄到了地上,從長蛇的尾部插過去,一轉眼消失不見了。
“Red Hair Girl at her Toilet” by Frederik Hendrik Kaemmerer (1839-1902).
決鬥
這不是模仿外國。不誇張地說,我想殺了那小子。也沒什麼深層動機。有個男人,他和我一樣厭惡對方這個人世間多餘的存在,就是他,我妻子的舊情人,把他們過去那些細節不加掩飾、五次三番地說給街坊四鄰們聽。有一天天剛黑,我和他在約好的咖啡店碰面,一身狗皮棉袍的他看起來就是一青年農民。剛一會面,我就把他的酒偷走了。就是那種動機。
我在北方一所城市中學讀高中。我貪玩兒。可錢這方面我又相當摳門兒。我平時專抽朋友的煙,不理髮,咬牙攢夠五圓錢才獨自偷偷地跑到街上,花掉一個錢。我不可能一晚花五圓錢以上,五圓以下也沒怎麼花過。要是有五圓錢給我拿着,我必讓它物盡其用。我用積攢的一堆小錢換下朋友的五圓錢紙幣。新紙幣,新到了割手的程度,它讓我的心跳更厲害,而我卻滿不在乎似地把它塞進口袋,來到大街上。這事每月大概一到兩次,成爲我生活的一部分。當時的我正被某種鬧不清楚的憂鬱感折磨着,遺世獨立而又懷疑一切。我認爲比起尼采、皮浪和春夫(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大正時期唯美主義詩人、小說家。譯者注)來,莫泊桑、梅里美和森鷗外更像那麼回事。算我胡說吧。我要拿上五圓錢去玩玩,拼了。
即使進了咖啡店,我也絕不會拿出快活樣子給人看,而是一副玩累的感覺。要在夏天,就說,給我冰啤酒;要在冬天,就說,給我燙壺酒。我鬱鬱寡歡地呷着酒,漂亮的咖啡女孩,我連看都不看她一眼。不管哪家咖啡店,似乎都有個色相已衰可又色心不減那一類型的中年女侍應。我只跟這種半老徐娘搭話:今天的天氣啦,物價啦,就這些。我數酒瓶的本事很厲害,喝光多少空瓶子,一目瞭然,眼神快得連神仙都覺察不到。餐桌上,只要是空啤酒攢夠了六個,或者清酒的酒壺滿了十壺,我便會想起什麼似的“嚯”地站起,低聲咕噥一句:“結賬!”從不會超過五圓錢。
我故意把手伸進各個口袋,意在表明我忘了錢放在哪裏。末了,終於,想起它們是在褲兜裏。我讓右手在褲兜裏磨蹭了好半天,總算把一張紙幣抽了出來。十圓的還是五圓的?我確認之後說了句“沒零錢……”才把錢遞給女侍,不等找零便縮起肩膀,大步走出咖啡店。直到返回學生公寓爲止,一路上我一次頭都沒回過。到了第二天,我一如既往地又積攢起零錢來了。
決鬥當晚,我走進了那家名叫“向日葵”的咖啡店。我身披長長的藏青色斗篷,戴着一副純白色皮手套。我不會接連兩次光顧同一家咖啡店――總是拿出五圓整――這種事多了必遭懷疑。而“向日葵”距離我上次來已經過了兩個月。
我那會兒的裝扮,跟一個剛躥紅的外國年輕影星有幾分相似,所以不時也有女人多看我幾眼了。我剛在一個角落的椅子上坐定,總共四名穿戴各異的女侍應一起走近,齊刷刷站到我的餐桌前。那是冬季,“給我燙壺酒。”我說着,冷得不行似地縮起脖子。扮相接近男影星最直接的好處是,我還沒發話呢,那位咖啡女孩便過來給我點了一根招待煙。
“向日葵”小而且髒。東側牆壁上有幅招貼畫,畫上的女人梳着二尺來長的西式披肩發,慵懶地支着腮,微笑時露出宛如核桃仁般大的牙齒。招貼畫的下首,斜着用黑漆漆了一隻“丸三麥酒”酒瓶;西側正對着這隻酒瓶的牆壁上掛着一面大鏡子,鏡框部分塗上了金粉。北側店的入口處,髒兮兮地掛了塊紅黑相間的平紋薄毛呢布簾兒,在它上方的牆壁上,用圖釘釘着一幅照片:一個洋妞兒在沼澤邊的草叢間裸身側臥,笑得很誇張。緊貼着南側牆壁掛了一隻紙氣球,它剛好懸在我的頭頂上方,彆扭得叫人生氣。一共有三張餐桌和十把椅子,放在正中央。一進門的地方還鑲着塊地板。總之我是不指望這間咖啡店給我帶來穩妥感了,所幸,這裏的燈光是昏暗的。
那夜,我受到了異乎尋常的款待。我的第一壺清酒給燙好了,中年女侍伺候着我正要喝呢,突然,方纔給我招待煙的咖啡女孩把她的右手掌伸到我的鼻子尖下邊。我不驚不亂,慢慢地抬起頭凝神望着她小小的瞳仁深處。“給我算個命吧?”她說。一下兒我就明白了:雖然我不苟言笑,可我身上卻散發着預言家的超強氣息。我沒碰女孩的手,只是掃了那麼一眼,“昨天失戀了,”我喃喃道。“太對了!”異乎尋常的款待就從這裏開始了。有個胖女侍甚至稱我“先生”。我給她們每個人都看了手相。“你十九,寅年生的”,“那男的讓你迷得死去活來”,“你喜歡薔薇花”,“你們家的狗生了,總共六隻狗崽兒”……每件事都被我算中了。那位中年女侍很瘦,眼睛倒還水靈,她一聽我說“你離過兩次婚”就把腦袋低了下去。這都被我說中了,太不可思議了,這真令我興奮不已。已經是第六隻酒壺了。就在此時,身着狗皮棉袍的年輕農民在門前出現。
農民走到緊挨着我的餐桌前,毛乎乎的後背對着我,坐下了,“威士忌。”狗皮的花紋裏摻雜着斑點。農民的出現,使我的餐桌狂歡戛然而止,我的清酒也攢到了第六壺,心裏一紮一紮地開始沮喪。我打算再喝點兒。那樣今夜的狂歡才更盡興。可我只能再喝四壺。遠遠不夠。不夠啊!偷。偷走那瓶威士忌。女侍她們不會以爲我是爲錢偷東西,會當成是預言家開的一個怪誕玩笑,反而會給我喝彩。那個農民也只會當作是醉鬼撒酒瘋,一笑了之的吧。偷!於是我伸出手,抓起了鄰桌那杯威士忌,泰然自若地一飲而盡。沒有喝彩。靜悄悄的。農民起身站在我面前。“到外面去!”他說完就朝門口走去。我“嘿嘿”地冷笑着,跟在農民身後走了出去。經過那面鑲金框的鏡子時,我瞥了一眼那裏的自己:風流倜儻,大帥哥!還想看,可鏡子深處那個二尺長的披肩發笑靨猶在,我只好作罷。我看起來很有自信,“啪”地一聲挑開了平紋薄毛呢布簾兒。
四角形的檐燈上用黃色的羅馬字寫着“THE HIMAWARI”,我就在那盞等下站住了。四名咖啡女侍,臉色慘白地擠在昏暗的店門後面。我們開始打嘴仗:
―― 你太不把俺當回事了。
―― 沒不把你當回事。鬧着玩兒。不行嗎?
―― 俺是粗人。被人耍了就要生氣!
我重新打量了一下這位農民:小臉盤頂着個剃得短短的小平頭,眉毛稀稀拉拉,單眼皮的三白眼,青黑色的皮膚。身高約摸比我矮了五寸(日本的長度單位,一寸爲3.03cm。譯者注)。對付他跟玩兒差不多。
―― 我無非想嚐嚐威士忌,看上去挺夠味兒。
―― 可俺也想喝。俺自己都捨不得喝。就那麼一點兒。
―― 老實人。可愛。
―― 你別狂。不就是個學生嗎?油頭粉面,會寫幾個字兒。
―― 我可不是。我是易學家。預言家。嚇你一跳吧?
―― 別說醉話了。給俺道歉!
―― 要知道我是誰,你得拿出勇氣來,我這都是好話。我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
我留意到,女侍們一直都在等待着事態向前發展。可她們表情冷漠,分明是在等着看我捱揍。我也就是在那時挨的揍。一記右勾拳“呼”地掃來,我飛快地縮起了脖子。――差了幾丈遠呢。我的白線帽子替我捱了這一下。我面帶着微笑,故意慢吞吞地走過去撿那帽子。近來天天雨夾雪,路面化得一塌糊塗。蹲下來,剛從泥漿裏撈起帽子我就在想,是不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能省五圓錢。另找家店,又能喝一頓了。三步變兩步,我開跑了。太滑了。我摔了個四腳朝天,丟人的姿勢恰似一隻雨蛙。真不作臉,我有點生自己的氣了。手套,外衣,褲子還有斗篷,到處是泥漿。我慢吞吞地爬起來,昂頭回到農民那邊。女侍們保護似地把農民圍在當中。沒一個和我是一夥。這個明擺着的事實令我殘暴心起。
―― 我希望你道歉。我冷笑道。我甩掉手套,又把斗篷(很貴的)狠狠甩進了泥巴。上述古老的臺詞以及姿態讓我找回了一點平衡。我已勢不可擋。農民脫下毛乎乎的狗皮棉袍,把它遞到給我香菸的漂亮咖啡女孩手中,又把一隻手伸進懷裏。
―― 別噁心俺了。
我擺開了架勢,盯着他。從他懷裏抽出的是一支銀色豎笛,檐燈一照,光閃奪目。這支銀笛他遞給了離過兩次婚的中年女侍。農民這一連串舉動看得我跟做夢一樣。這可不是小說情節,是真事兒!我想殺了他。
―― 接招兒!我一聲吼叫,使勁全力用我的泥巴鞋朝他小腿踢了過去。踢倒他,再把他那對亮晶晶的三白眼摳出來。沒踢着。泥巴鞋踢空了。我幹得太不漂亮了,發覺這一點,令我悲從中來。一隻帶着些許溫熱的拳頭擊中了我的左眼以及大半個鼻子。我看見有紅色火焰從我的眼前噴出,跟着就是一個趔趄。“啪”,從右耳垂到臉頰這個部位又給抽了一巴掌。我的兩隻手都插進了泥漿,而着地那一瞬,農民的一隻腳又被我“吭哧”一聲啃個正着。腳好硬啊。簡直就是路邊那些白楊樹樁嘛。我在泥漿裏趴着,事到如今我迫不及待想要放聲痛哭,卻連一滴眼淚都哭出不來了。
“Solitude”, 1956, Paul Delvaux.
黑人
黑人進了囚籠。囚籠面積約有一坪,裏手黑咕隆咚的旮旯裏放着個原木做的凳子。黑人就坐在那兒,刺着繡。在如此黑暗之地怎麼可能刺繡呢?少年好像城府已深的成年男人那樣冷笑了一聲,兩側鼻翼隨之凹出刀刻般的皺褶。
黑人牽來過一匹日本曲馬(曲馬,按日文直譯即馬戲團的馬。譯者注),村裏爲此一片騷亂。據說它喫人,生着紅色犄角,周身遍佈花卉形狀的斑點。可是少年根本不信這些。少年長於思考。村裏人在心裏也並不相信那種傳言。無非是沒有夢想的日子過於平淡,隨意編出個傳聞來而已。誰若真信那準是喝多了。每當聽到村人散佈這種不靠譜的謊言,少年都咬緊牙,捂住耳朵,飛也似地跑回家。少年思索着村人編造的愚蠢謊言:這些人何以要言來語往地把這事說得越來越玄呢?黑人好像也不是母的吧?
曲馬的樂隊在狹窄的村路上巡遊,用不上六十秒就能把村子的角角落落都宣傳個遍。一條道的兩側,錯列着幾十戶人家的茅草房。樂隊出得村子後並沒有停步,一面反覆演奏那首《螢光》(蘇格蘭民歌,在日本,該曲含有送別之意。譯者注)曲,一面在菜田間列隊行進,出了插秧季節的稻田後,在逼仄的田邊小道上排成一排,在全體村民的眼皮底下過了一座浮橋,向着森林方向穿過去,一直抵達距離本村八里地的鄰村。
村子東頭有所小學校,從小學校再往東,緊挨着的是一個牧場。牧場的面積約當百坪,荷蘭紫雲英花開遍地,兩頭牛跟半打豬(原文直譯,半打豬,即六口豬。譯者注)正在一起玩得起興。那匹曲馬給拴在鼠灰色的帳篷式小屋子裏,牛跟豬則被轉移到了主人家的倉房。
夜裏,村人用頭巾包住頭臉,兩三人一組,結伴進到小屋子裏。總共有六七十名看客。少年狠命廝打着那些大人擠到了最前面。一個圓形的舞臺,四周用粗繩圈了起來。少年的下巴搭在繩子上,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只是偶爾才眨一下眼,簡直着了迷:驚險馬戲的配樂。木桶。針織品。鞭子的聲音。金線織花的錦緞。瘦瘦的老馬。驚呆與喝彩,以及木炭……二十來盞煤氣燈亂糟糟地吊在小屋的各個角落,成羣的夜昆蟲圍着它們飛舞嬉戲。或許因爲帳篷的布料短缺,小屋的頂棚開着十坪左右的大口子,從那兒望得見星空。
兩個男子押着囚籠裏的黑人來到了舞臺上。囚籠底部像是安了輪子,發出“嘎拉嘎拉”的響聲滑向舞臺。頭巾覆面的看客們高聲吼叫拍着手。少年悒悒不樂,他挑起眉梢,靜靜地觀望着囚籠中的黑人。
冷笑從少年的臉上消失了。那幅刺繡竟是一面“日之丸”旗。少年隱約聽到自己的心臟開始“嘭嘭”響。他並不缺乏對軍人以及與軍人相關的概念。黑人並沒欺騙少年,他果真是在刺着繡,“日之丸”那麼簡單的繡品,當然可以在黑暗中摸索着完成了。多好啊。這個黑人,多麼誠實的人。
不久,一個穿着燕尾服蓄着仁丹胡的當家女藝人出場了。她向看客自報家門後便衝着囚籠連叫了兩聲:“凱恩!凱恩!”右手則甩出漂亮的鞭花兒。鞭子聲鋒利地刺穿了少年的心。女藝人令他嫉恨。那個黑人,站起來了。
黑人給鞭子聲嚇得瑟瑟發抖,一面笨手笨腳地表演了幾個雜耍動作。糟透了的雜耍。可除了少年,那些看客對此毫無察覺。喫不喫人?長沒長紅色的犄角?這些纔是他們的問題。
黑人被套上了一件燈芯草蓑衣,或許因爲經常塗油,身體各個部位都亮閃閃的。末了,黑人唱了一段謠曲。女藝人用鞭子聲伴奏。“嘎……嘭……嘎……嘭……”唱詞簡單至此。可少年喜歡那韻味。唱詞再怎麼差勁兒,可要是發自苦悶鬱結的心,就一定可以發出動人的迴響。少年想到這裏,用力閉上了眼睛。
當夜,少年一邊想着黑人,一邊自瀆。翌晨,少年上學了。他翻過教室的窗戶,縱身躍過校園後門外的小河溝,朝着他的目標曲馬飛跑過去。透過帳篷的縫隙向裏邊張望,只見那些馬戲藝人被褥散亂地鋪滿了整個舞臺,咕容咕容地睡着,就像是一些青蟲。傳來學校的鐘聲。開始上課了。可是少年沒有動。黑人沒在這裏睡。怎麼找都找不到他。學校變得一片寧寂,已經開講了吧……“第二課,國王亞歷山大和醫師菲利普。從前,在歐洲有一位名叫亞歷山大的英雄國王……”少女朗朗的讀書聲清晰地傳來。可是少年沒有動。少年堅信,那個黑人是個女的。平時肯定不在囚籠裏,而是和大夥出去玩兒。幹些洗洗涮涮的活兒,抽菸,用日語發牢騷。就是這種女人。少女朗讀完畢,傳來了教師粗濁的嗓音。“信賴,它是一種美德。亞歷山大國王因爲擁有這種美德而保住了性命。同學們……”少年還是沒有動。不會不在這裏。少年執拗起來,認定囚籠必是空着的。窺探中他在想,黑人會悄悄地來到他的身後,一下子抱住他。所以他對自己的背後一點兒都不敢怠慢,肩頭上稍稍使了點勁兒,擺好了被抱住的姿勢。黑人一定會把“日之丸”刺繡送給我,那時候,我可要把話說得硬氣一點,我就問他:我是第幾個人?
黑人沒出現。離開帳篷的少年,用衣袖揩拭着窄窄的額頭上的汗,慢吞吞地返回學校。“我發高燒,肺子這兒難受。”穿和服裙子和高腰皮鞋的老教師被他巧妙地騙過去了。少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又假裝咳起嗽,咳到像是連氣都喘不上來。依照村裏人的說法,黑人一如從前給塞在那囚籠裏,再被裝入帶篷的馬車,離開了本村。他們還說,那位當家女藝人的衣兜裏還藏了把手槍用來防身自衛。
“uprooted”, 2016
|推薦閱讀 |
如何在靈魂深處做個幸福的人? | 羅素
你的娛樂方式決定你的未來 | 吳淡如
我的漫畫 | 豐子愷
最後一位顧客 | 竹本幸之佑
論美 | 培根
餐館之夜 | 村上春樹
對生活的勇氣 | 叔本華
你想要一份完美的愛 | 村上春樹
夜鶯與玫瑰 | 王爾德
記得心裏的夢想 | 李安
素材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鳥人與魚整理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