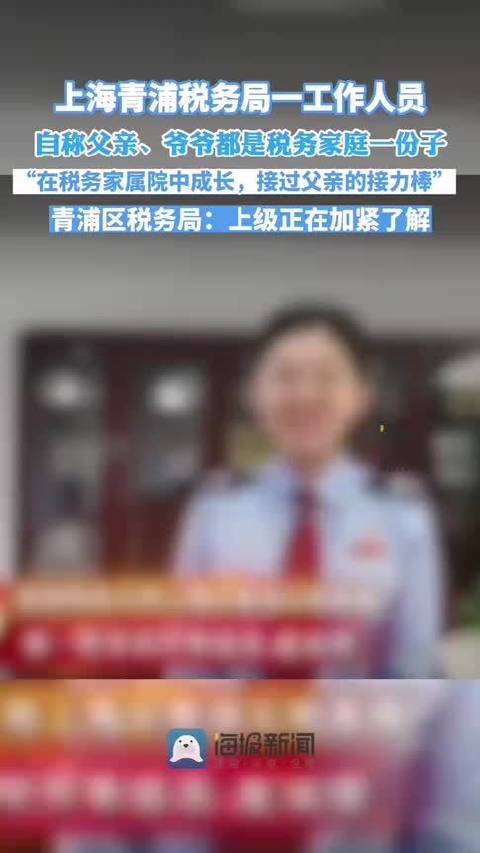華裔繪本家楊志成,一個特殊歷史情境下誕生的人
(原標題:華裔繪本家楊志成,一個特殊歷史情境下誕生的人)
1977年左右,一個人在美國留學、工作的楊志成(Ed Young)在時隔近30年後,終於有機會回到中國探親。
“這是一個驚奇的事情。因爲我20多年沒看見母親,回國我不知道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我母親會有什麼感覺。電影裏看人家20年沒見,哭哭笑笑。那時我坐飛機回來,接飛機都不容易,家裏沒車子,(也)沒有計程車,坐公共汽車從飛機場回到家。公共汽車站在四合院外邊,離家其實很近。我母親那時也70多歲了,她在公共汽車站等我。我是黑暗的。她就到我身邊。我家裏叫我Ed。她說,Ed,你晚飯喫了沒有?我說,喫過了,可是都是喫的飛機上的東西。她說,我做了稀飯,有皮蛋、肉鬆,你今天晚上喫一點。那麼,她攙着我的手,我們就一路上走回去。好像前一天剛剛走,這一天回來,根本沒有興奮什麼,好像沒有出門過。”楊志成回憶道。
今年88歲的楊志成是著名的美籍華裔繪本家。他創作過約100部繪本作品,如《公主的風箏》《狼婆婆》《七隻瞎老鼠》等,獲譽無數,包括美國童書界最高獎項凱迪克獎的一次金獎和兩次榮譽獎、美國插畫家協會授予的終身成就獎、兩度被提名國際安徒生獎、作品入選《紐約時報》十佳繪本等。
在美國,童書歷史學家倫納德.S.馬庫斯(Leonard.S.Marcus)認爲,一位華人能被美國童書出版界和讀者接納、尊重,成就卓然,太不容易了。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童書專家凱瑟琳·T·霍玲(Kathleen.T.Horning)稱:“不論選取何種媒材和風格,楊志成對他插畫的每一本圖畫書都帶着深度的自然與人道關懷。一粒沙中見世界,一朵花中見天堂。”
在中國,兒童閱讀推廣人、譯者阿甲評價道:“他實際上是把中國最好的東西以某種世界性語言,或者西方人能夠接受的語言、當代藝術的語言,重新梳理一遍,以某種方式呈現,對整個世界文化是有某種特殊貢獻的。如果一定要說他整個創作在做什麼嘗試,我覺得可能叫作平衡之道。”
從天津到上海、香港,再到美國,楊志成一生隨着時代變動穿梭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間。其創作與經歷也密切相關,他自稱“在東方的時候學西方,在西方的時候學東方”。置身東西之間,楊志成尋找着平衡之道。某種意義上,他的藝術與人生也是一部中國近代史。
“他是很特殊的情境下誕生的一個人物,生平無法複製。”阿甲說。
楊志成(Ed Young),美籍華裔插畫家。1931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在上海長大,後赴香港和美國求學、定居。畢業於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建築系,後轉到洛杉磯藝術學院學習廣告設計。其插畫具有濃厚的中國風味,曾三度獲得美國兒童文學界最高榮譽凱迪克獎。
從東方來到西方
1931年,楊志成出生於天津。那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局動盪,他在3歲時隨家人搬到上海,度過童年和青少年。1948年,中國處於內戰中,楊志成去了香港唸書。
楊志成覺得,從小學到中學,自己就是一個“混”字。“沒有唸書,及格就行。上海玩,香港玩,成績表不能見人,後來在香港申請大學也沒有太多希望。”
1951年,楊志成赴美留學。因爲父母都在上海,臨走前,他在香港的監護人舅舅叫他去辦公室,對他說:“你以前過了19年,沒有好好學。現在你不能靠別人了,到了美國,要靠你自己。因爲我們和你斷了,在美國就你一個人。這一筆錢給你,以後就沒有了。這是你哥哥姐姐沒有用的錢給你用。還有一件事,你到美國以後,要負責個人事情,你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去美國,你以後做的事情是代替我們做。如果是不好的事情,你把這條路給斷了。”
“這句話在我‘志成’下面種下種子,那就是我要讀書。”楊志成說。
楊志成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兩個姐姐。受父親影響,楊家三兄弟學的都是建築和工程,所以他最先在美國就讀於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建築系。
楊志成的父親楊寬麟是中國第一代建築結構工程設計學家,早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文學院,20歲時赴美留學,在密歇根大學獲學士和碩士學位,1917年回國。後在1920年開辦華啓工程司,這是中國人自己創立的最早以結構設計爲主的事務所之一。他參與設計的建築包括上海的美琪大戲院、大新百貨公司、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新僑飯店等,指導修建的工程還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北京工人體育場等。
簡單考據,楊寬麟的家世很有意思。他的父親楊少亭是一名牧師,母親是美國聖公會首位華人牧師黃光彩的女兒,姨母黃素娥是執掌聖約翰大學52年的校長卜舫濟的妻子。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羅元旭曾寫過一本書《東成西就》,研究上海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他們創建了聖約翰大學、商務印書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國紅十字會等多家機構,成爲百年來中西交流的橋樑,而黃光彩牧師及其後人就是羅元旭寫的第一個家族。
所以,受家庭影響,楊志成像林語堂一樣從小接受的是西學教育,英文非常好,但沒有國學根底。不過最後,他也和林語堂一樣,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當時,楊志成在美國學了兩年建築後,覺得自己喜歡藝術,所以轉入了加州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畢業後,他在紐約從事廣告設計,但覺得“沒太大意思”,賣的東西不是自己喜歡的。平常,他喜歡去紐約中央公園畫動物素描,也熱衷畫紐約各種各樣的老建築,“紐約城是我的大學”。
有一次,他的朋友覺得既然他這麼喜歡動物,不如干脆去畫童書插圖,所以楊志成毛遂自薦,跑去出版社投稿。“我穿得很普通,就揹着一個大破包。到了童書出版社,看門的看了我一眼,讓我從後門(專供送貨人員出入)上去。我是無所謂,上去以後,我就坐在那個編輯的辦公室,放下包,也不走。編輯看看我,問我要幹什麼,我這才告訴編輯我是來投稿的,指指包。原來他們都把我當成送盒飯的,奇怪我爲什麼放下包還不走。”
當時,被譽爲“20世紀美國童書界最偉大的編輯”、“兒童文學界的麥克斯·珀金斯”的厄蘇拉·諾德斯特姆(Ursula Nordstrom)看過楊志成的畫後,給了一部賈尼思·梅·伍德里(Janice May Udry)的書稿。但是,楊志成回絕了這本書。因爲他覺得動物有動物的生活和尊嚴,不應該用動物講人的故事。厄蘇拉讓他先把書帶回去再想想。經過朋友相勸,既然他不喜歡沒尊嚴的動物,那可以按照他的心思畫他認爲有尊嚴的。他思考後,認爲這也是學習如何製作童書的一個方法,所以最後接了這部書。
1962年,這部名爲《討人嫌的老鼠及其他討人嫌的故事集》(The Mean Mouse and Other Mean Stories)的童書一經出版,就獲得平面設計協會優秀作品獎。各家出版社紛紛向初出茅廬的楊志成邀約。結果,他陰差陽錯地進入童書界,一干就是50多年。有意思的是,後來他再也沒和厄蘇拉合作過。
同樣在1962年,楊志成偶然遇到改變他創作的一個人——鄭曼青。當時,楊志成的膝蓋患病,看了很多西醫都沒用。經人介紹,他找到“五絕老人”、蔣介石的私人醫生鄭曼青求助。鄭曼青使用中醫的方法治好楊志成的病,楊志成也對鄭的“五絕”(詩、書、畫、中醫和太極拳)產生興趣,向其拜師學藝,同時幫他翻譯。也是從那時起,楊志成對中國文化的瞭解越來越深,作品中的中國味道越來越濃。
他在接受臺灣和英出版社採訪時曾說:“我的國畫老師對我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常常爲我指點迷津,幫助我參透那些自己無法明瞭或看不清的事理。有一回我們相約去散步,他便要我留意樹梢上竄冒出來的綠芽,看看樹枝上的‘氣’。當時我不明白他話中的意思,也看不見他所謂的‘氣’。於是他要我再仔細看,當我靜下來潛心端看的時候,彷彿真的體會到他話中的意涵。造成一株樹生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樹的成長方式、枝葉的伸展、風、樹根、甚至樹旁的石頭和人類,而樹的心靈都是由這些‘天地人’的因素造就出來的。我在藝術學院裏從未聽聞這些事,因此覺得中國人對自然和事物的觀點特別深奧。根據我國畫老師的說法,我必須將自己化身爲一株樹,才能領略和體驗樹的成長,因爲每一個生命都有一段屬於他自己的故事。”
《葉限:中國的“灰姑娘”故事》,[美]路易·愛玲/文、楊志成/圖,常立 譯,蒲蒲蘭丨新世紀出版社2019年4月版
在西方講述東方
1968年,在爲童書畫了6年插圖後,37歲的楊志成憑藉《公主的風箏》獲得凱迪克獎的榮譽獎。
這本書的插畫採用中國民間剪紙技法,並像中國畫一樣大量留白。故事講述在古代中國,有一個公主叫小小,在她父皇眼中,她的四個哥哥就像太陽,三個姐姐就像月亮,而小小就像一顆小不點的星星,因此父皇常常忽視她。可是,當皇帝被綁架,哥哥姐姐們全都束手無策時,只有小小一個人勇敢地追了過去,成功用風箏救出她的父皇。
“做《公主的風箏》這本書時,中美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寫書的是美國人,他寫的算是民間故事,可是他對中國民間也沒有什麼研究。他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用中國背景講了箇中國故事,但不是中國人靈魂裏出來的故事。我對這個故事不反感,因爲講的故事是一個全世界的故事,可是我覺得這個故事我能學到什麼東西?從民間的藝術裏面找到剪紙?我想,剪紙我從來沒做過,也沒學過,趁這機會學剪紙。怎麼剪?自己剪。剪了,壞了,又剪一個。壞了,又剪一個。紙是用什麼紙?刀是用什麼刀?顏色是用什麼顏色?怎麼切?怎麼做?結果不知道畫了多少次,後來成功了,覺得有點像,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本書。”
“還有一點,中國民間故事裏邊,插圖畫都很古板,都是一種靜的狀態,不是活的。而這本書像風箏一樣,是在天上飛的,是活的。這對我是一個難題,因爲我要從正宗中國藝術裏找一個活的東西。在這本書裏,我要把風箏畫得可以在天上飛起來,要在靜裏面找活。做完了以後,我覺得讓它活起來了。”楊志成說。
得到凱迪克獎後,楊志成對自己的創作多了一點信心,“在這時候已經得到這麼高的獎,我覺得有資格能夠再學多一點,所以我放心學別的東西,就是從這一本開始的”。
楊志成愛說自己“基礎不夠”,喜歡學習,所以他的作品沒有固定風格,整個創作生涯是一個不斷突破的過程。《公主的風箏》之後,他就不再完全用剪紙技法做書,開始嘗試用鉛筆畫。題材上也是如此。“我最開始的一本書是關於動物的,所有編輯都喜歡你的書,讓你畫動物的故事。我變成一個只能畫動物的畫家。我說,我不是專門畫動物的,我喜歡的東西特別多。我學建築,我喜歡畫房子。爲什麼單單畫動物呢?我就畫了一個房子的故事。他們總是給我一個網,把我抓在這裏。我喜歡自由,我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我要畫這個!”
“當然,不能怪他們,他們不知道我會畫什麼。我的條件就是,你要給我全部自由,我要怎麼畫就怎麼畫。他們信任我,那麼我就可以自由地選用材料。所以我的每一本書都會突破另外一本書,每做一樣東西,總是學到一種藝術。到了一個程度,不能再上去的時候,就成功了。”
楊志成的工作方法很有趣。據說他每天去畫室,同一個故事,先用鉛筆畫,再用水彩畫,或剪紙,或拼貼,以不同媒介、不同表達方式排成一排,讓每頁連接成故事。就如同一家人,畫的構圖、排序,自有其韻律。“如果這個故事值得講,我要找到最好的方法。”
1990年代,楊志成迎來創作的一個高峯。1990年,他的《狼婆婆》(Lon Po Po)獲得凱迪克獎金獎。兩年後,《七隻瞎老鼠》(Seven Blind Mice)獲得凱迪克獎榮譽獎。
《狼婆婆》採用中國畫中的粉筆渲染和具有東方審美情趣的“屏風式”構圖,講的是很久以前,每當媽媽出門之後,狼婆婆就會來敲門,阿珊、阿桃和寶珠最後智取狼婆婆的故事。《七隻瞎老鼠》則採用剪紙和拼貼,並用大範圍的黑色分割空間。故事改寫自印度民間故事“盲人摸象”,講述七隻瞎老鼠在池塘邊遇到一個怪東西,誰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於是每一天,不同的老鼠輪流去“觀察”,並回來報告同伴他們的發現,但是每一次的答案都不讓人滿意。最後一天,輪到白老鼠去了。白老鼠從怪東西的上下左右全跑了一遍,最後才下了一個結論,這個怪東西是一頭大象。
兩本書都有關東方,在西方講述東方的他獲得美國童書界的更多認可。相比之前的作品,他不僅在繪畫風格上有所突破,也成爲用文字講故事的人,不再只是插畫家。
後來,他又講述了許多東方故事,比如中國的《生肖鼠的故事》、《美猴王孫悟空》、《塞翁失馬》、《葉限》、《心之聲》,日本的《侘寂》、《海嘯》,尼泊爾的《雪山之虎》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心之聲》中,他以圖畫的方式還原中國象形文字的內涵,所有部首都和“心”有關,曾希望能解釋完《康熙字典》裏的214個偏旁部首。另外,他的個人網站也以中國象形文字作爲導航。
中國文人畫中字畫同體的觀念也影響了他的創作。在接受《出版人週刊》採訪時,他說:“一幅傳統的中國文人畫若沒有題字,往往便失去了重心。文與圖是相輔相成的。文字能傳達的意涵,有時是圖畫永遠無法傳遞的,反之亦然。文與圖共存時,便建構了整體的閱讀經驗基礎。”
但是,如果說楊志成只是一個在西方講述東方的藝術家,那也沒有完整理解他。其實,他不僅會採用東方技法,講述東方故事,也會融合西方藝術,講述西方故事。比如近些年他喜歡拼貼,稱靈感來自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啓發過他創作《七隻瞎老鼠》;艾爾·帕克(Al Parker)和瑪麗·卡薩特(Mary Cassatt)也影響過他的插畫。這種穿梭在東西之間,交融多元文化,尋求背後普世價值觀念,也許正是楊志成受到國際認可的原因。
他曾說:“我參與繪本工作,一方面是想要引介中國故事,我們有太多好故事了!另一方面,以一個異鄉人的身份來到美國,我也希望多理解西方故事,好拓展我自己的眼光和表現形式。每次我投入一個異域文化故事,我都從中受益匪淺。”
不過,多元文化融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能會遭遇誤解。比如《七隻瞎老鼠》在美國出版後,受到一些批評,比如爲什麼第七隻老鼠是白老鼠,不是黑老鼠?這是不是影射美國的黑人和白人的種族問題?楊志成回應稱,其實不是爲了聯想,是爲了光線。太陽光是白的,放大鏡一來,七個顏色就出來了。你不能用一種眼光來看故事的思路。他還說,外國老鼠有雌雄,幸好英文版的故事裏六隻老鼠是男的,最後發現大象的老鼠是女的。如果六隻老鼠是女的,最後發現大象的老鼠是男的,估計問題就大了。
事實上,他畫的時候根本沒考慮性別、種族之類的問題。所以很多時候,他覺得“有問題的不是這個故事,是人自己”。
《雪山之虎》,[美]羅伯特·伯利/文、楊志成/圖,阿甲 譯,蒲蒲蘭丨新世紀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從西方回到東方
2012年,楊志成來到北京宣傳新書《月熊》,阿甲也第一次見到了他。“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喫飯聊天的時候,他忍不住講起他小時候在上海,他爸爸造的房子。我當時都聽傻了。”阿甲說。
“他的爸爸給他們一家人建了一個房子,這個房子居然可以扛炸彈。最精彩的是,他爸爸當時居然給他們在房子旁邊建了一個游泳池,那是上海第二個私人擁有的游泳池。其實以他們家的財力沒有辦法支撐游泳池運作,他爸爸又採取俱樂部的方式把那些海歸們拉在一起,幾家人一起運營。他們家不出錢,但是共同維護。他們一家人,尤其是幾個孩子身體都特別好,一天到晚,能游水的時候就游水,不能游水的時候就在那個地方騎車瘋跑,就是那樣一種童年。挺讓人驚訝。而且他們一家人雖然生活在上海,平常主要跟父親說的都是英語,其次是上海話。我以前沒有想象過有這樣的家庭。”
楊志成生活時的上海是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先後經歷日本佔領和國民黨統治,是“一種很特定的情景之下的童年”,“他的父親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包括楊寬麟先生的家族對中國其實是有很大影響的,只不過一般人不大提及”。阿甲那次聽說楊志成以這段經歷創作過繪本《爸爸造的房子》後,立馬買了英文版,覺得“太有意思了”,之後翻譯了這本書。
楊志成也對我們講起這本書的故事:“那本書做了兩年多。因爲題材不夠,我要把爸爸的那個房子的實際結構(做出來),沒有圖案,要自己想象。我自己畫出來的,不對,還是我兩個兄弟幫我做的,因爲他們是工程師,尺寸什麼的比較拿手。後來親戚們有照片都寄給我,收集的材料很多,所以做了很長時間,越做又有趣,覺得把自己從前的故事在回憶裏邊提出來了,好像又活了一輩子。”
他還談起父母的影響:“我母親在藝術上特別有眼光,家裏的東西都是她設計的。我父親那時做教員,在大學教書,沒有錢,我母親就各個地方掙錢做東西賣,補貼家用。那時家裏非常辛苦,我們5個孩子要成長,喫東西都不夠。家裏邊都要添東西,飯沒有,就是紅薯什麼的加在裏面,多喫一點。我們孩子也不知道,只知道家裏東西不夠喫。所以這是我母親的特點,她在藝術這方面多才,什麼都會做。”
“我母親一直擔憂我將來,不懂我到底是怎麼一棵樹。她說,你總是跟人不一樣,我不知道你以後怎麼辦?”相比母親,“我父親很懂孩子,他是教書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天才),所以這一方面我是在他身上得到的。”
2019年12月,時隔17年,楊志成回到上海,經過一番周折,在惇信路(現爲武夷路)找到了爸爸造的老房子,門上竟還保留着代表楊家的字母“Y”的設計,也去爸爸曾經工作過的聖約翰大學(現址在華東政法大學)看了看。
“美國有一個故事,一個叫瑞普·凡·溫克爾的人出去打獵,到了一個樹林裏,看見一羣小人有鬍子,像白雪公主裏的那種小矮人,戴着長帽。他從來沒看見過這種人。他們有他們的運動,打球,非常喜歡喝酒。他跟他們喝了酒,睡着了。醒來,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醉的地方已經長了很多樹木。他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才醒過來,看到自己的槍鏽爛了,狗也不見了。他回家,發現家也變了,鄉村的人都不認識。他就問人。他說,我從前是從這個村莊出來的,不知道你們見過門口這家人嗎?那個人說,哦,這個家已經沒有什麼人了,都過去了。他說,我是去打獵剛回來。那個人說,是有一個人沒有回來。”
“那個故事就是我回到上海的故事。回到上海,看老家,看聖約翰大學,變得不認識。人都變了。街道都是市中心,就在我的房子的地方,都造滿了。從前一個房子是單獨的,是郊外,現在都裝滿了。大門也看不見,邊上都是東西。所以這是我一個感覺,已經不是以前了,都是過去的事情。”
除了回上海,楊志成這次也回到北京,宣傳他的新書《葉限》和《雪山之虎》,同時探親。在一場講座中,楊志成坐在瑜伽球上回憶了《葉限》的創作過程。當時,他需要研究苗族,包括服裝、頭髮、鞋子等,所以到處收集資料。因爲那時北京的展覽會不能拍照,他的嫂子錢媛(錢鍾書和楊絳的女兒)就憑藉記憶畫了苗族的服飾寄給他。
《葉限》插圖
楊志成回憶,錢家幫了他很多忙。“她跟我有相同的地方。她是讀書人,寫詩。她從前讀書也不見得好,所以很同情我,給我一個綽號是‘黑羊’,就是白羊裏有隻黑羊。所以我給她寫信,有時會畫一隻黑羊。錢媛他們一家對我很有好感。錢老師給我幾部書,都是白的,讓我畫畫,很器重我。我做書,有許多是中國題材,都是錢先生幫我。有時候說得不對,他會寫信。比如這是這個朝代,穿這個衣服不對。他們有他們的基礎,我沒有基礎,所以有時候他就指點我。”
“我後來出一本書是《龍生九子》。《龍生九子》的原文是錢媛給我的。錢媛看有地方可以幫我的,她會寄給我。她說,Ed,你看看,這個很有意義。我一直襬在那個地方沒有做。後來她‘過去’以後,我就看《龍生九子》,我說這太有意思。龍的九個孩子有九個性情,每一條龍給它一個才能。有了才能,它就做它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家教了。”
楊志成稱,未來他會在自己的100部作品中,挑選13本左右最具突破性的繪本,講述背後的故事。而且和之前的繪本不同,這本書會在中國率先出版。
活了快90年,他說一生最大的遺憾是“世間有太多東西要發現!”“我經常想爲什麼上天給我們這麼多去學習,但是我沒有多少時間去實現。”
他覺得,人大概分兩類,一類靠的是“心”,一類靠的是“腦”。他是靠“心”的人,無論是創作還是人生,他都聽從內心。某種意義上,他也認爲這是“命”。
《雪山之虎》插圖
在採訪過程中,服務生端來一杯咖啡,楊志成看到咖啡上有兩顆“心”形的拉花,馬上對旁邊的編輯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畫,你把它照下來。”放了一會兒,最後喝前,他還不忘提醒編輯:“你照片拍了嗎?”
心和靈魂相關。在他看來,所謂好的繪本,“一句話,每一個故事有一個靈魂,沒有靈魂的書不用談了,你能夠抓到那個靈魂就是好書”。但是,抓到靈魂的書可能並不爲大衆所熱愛。阿甲稱,楊志成在美國不是特別主流,但很多人都說了不起。因爲他真的是在追求一種藝術,追求一種道,好像不是太遷就大衆。有的老外真的受不了他,但喜歡的人非常喜歡。這點比較像同爲華裔畫家的陳志勇,大衆讀者不是特別能夠欣賞,但專業畫家和評論圈裏認可比較多。
不過,阿甲認爲,楊志成找到了自己的平衡。“如果孩子讀不懂,不喜歡怎麼辦,那也就由它去吧。藝術家就是這樣一種氣質。爲什麼說平衡?如果一個藝術家這麼幹,怎麼過日子?他賣的插畫是給普通讀者看的,而且還是小孩看的,但楊志成做到了。他一輩子都在追求,都快90歲了,還在幹這種事情。他還能幹,還能夠掙到錢來幹,人家還給了他名譽、這個行當中的特殊地位,然後他還可以肆無忌憚地幹。這就是他人生的平衡之道做得特別好。”
阿甲覺得,88歲的楊志成像孩子一樣單純、真誠,直接爽快、完美主義,活得簡單、通透。“接觸多了,一想起來就覺得,啊,世界上有這樣的人真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