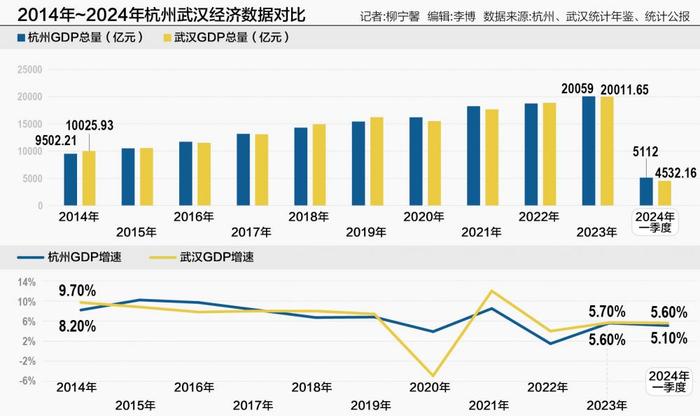翻滾吧!武漢95後雜技少年
_No.
1141
//
六歲那年,一輛載着“釋小龍報恩”海報的皮卡車從我老家駛過,鼓聲撼地,塵土飛揚,成功吸引住全鎮人的目光。
傍晚,十餘位面圓耳大的光頭壯士,斜披袈裟,腰繫青絛,足蹬黃靴,閒庭信步在小學門口,搭起幾丈高的帳篷,銅鑼敲得哐當響。
“門票5塊錢,進來看驚喜!”
攥緊老人頭,瞪圓雙眼,走進帳篷,我的確見識並收穫到很多驚喜。
比如,釋小龍的“師哥”竟然是位40多歲的東北精壯漢子。比如,一把開光的桃木寶劍售價60元。再比如,時隔多年後,我才知道鋼槍刺喉、鐵圈脫身、掌劈紅磚,不是電視裏的少林72絕技,而是民間的傳統雜技。
上週,武漢剛剛上演一場雜技盛會——第十三屆“中國武漢國際雜技藝術節”開幕。它地位很高,規模很大,與摩納哥蒙特卡洛國際馬戲節、法國巴黎“明日與未來”國際雜技節、中國吳橋雜技節並稱爲國際四大雜技節。
近300㎡的舞臺,被燈光照得亮如白晝。掌聲雷動,驚歎起伏,武漢本土節目《寒梅疏影—槓上技巧》更是掀起當晚高潮:
七個孩子,時而在空中飛轉,時而翻個跟頭,從一根杆迅速攀爬至另一根杆,接着又是360°空翻,跳上另一個夥伴的肩頭……
掌聲雷動,鞠躬謝幕,笑容在他們臉上氤氳開來,漾起波浪。相比而言,我其實更關注舞臺背後的他們,於是距離演出五個小時前,帶着攝影師悄悄溜進他們的化妝間。
推開門,清脆的笑聲撲面而來,他們以各種舒服的姿勢躺在椅子上,喫薯片,喝奶茶,打遊戲……你蹭蹭我,我靠靠你,再大喊一聲“老師,下一個該誰化妝?”整個化妝間童趣盎然,看不出半點比賽前的緊張。只在言談間,流露出一點小情緒。
九歲那年,拉着父母給自己報芭蕾舞的嬌嬌,最後被父母“忽悠”進了雜技班。因爲“舞蹈學完還得自己出來找工作,但雜技包分配,學完就可以進團。”
雖然對芭蕾念念不忘,但嬌嬌也不怨恨父母,“雜技確實可以掙錢。”看着同齡人還在伸手向父母要錢,嬌嬌露出一種大人的自豪,“我比他們都獨立”。
對於是否還想回去學芭蕾的問題,她沒有回答,只嘟囔着嘴“練了這麼多年雜技,不能白費,我還想堅持下去。”
今年23歲的黃婷進雜技團也有九年,當初入行完全衝着包分配。但練到第三年的時候,她做了一次“逃兵”,跑到江蘇哥哥那裏,在嫂嫂所在的一個醫療工廠做紗布。
流水線的工作枯燥寂寞,黃婷又想回到雜技團,“因爲有很多學員在一起,比較開心。”恰好彼時,有一個比賽,團裏缺人,命運給了她一次回頭的機會。
又過去三年,在天津的一個比賽,她獲得人生第一個大獎。也是在那次比賽中,她認識了武漢團的一個男生,兩人成爲男女朋友後,便隨之來到武漢,既是情侶,又是同行,風花雪月之餘還可以互相切磋一下技藝。
看着老家一些童年玩伴已經結婚有了小孩,黃婷更加滿意自己目前的生活。她喜歡在舞臺上的感覺,“所有人都在看我,爲我鼓掌”,說這話的時候,她的眼睛閃閃發亮,不一會兒又黯淡下去,“但現在身體只適合晃圈,就只能託底。”由於雜技對身體的特殊要求,年紀小,身輕,筋骨柔韌,就做“尖子”,大了就只能當“託底”。
“誰都想做主角,但最好的光陰也就7-12歲那五年”,說完黃婷又給自己圓回來,“不過也沒什麼,今天你做主角,明天我做主角,都這樣的,熬着熬着就過去了,等到三十歲都去做(雜技)老師。”她嘿嘿地笑着。
“比如這次的主角就是他倆”,黃婷指着不遠處的兩個小男孩。
“哎呀!”那邊突然傳來一聲驚叫,好像是輸掉了遊戲。這個頂着雞冠髮型、長得像泰國小孩的男孩叫唐粒栩,12歲,是這些演員中最小的。哥哥唐英栩15歲,也在這個節目中。兄弟倆都是這次舞臺上的主角。
老家在湖南,父母常年在福建打工,兄弟倆很小就被送到中國雜技之鄉,河北吳橋。2014年的一次比賽,兩人被武漢團挑中。
一個鬧騰,一個安靜,但兩個都是手機不離手。“每天就是練雜技,很難熬,只有手機陪我。”哥哥望着遠處,睫毛很長,眼睛很亮,眼神有些閃躲。
“只能靠手機來發泄嘛,每天練雜技練得發矇”,弟弟在旁邊嘟噥着。
唐粒栩的節目有七分鐘,全程他都得用手支撐自己的重量,前期是漫長的手臂力量訓練,倒立,腳靠在牆上,全身力量都落在胳膊上。“時間一點點累加,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唐粒栩的口氣像個歷經滄桑的中年人,忽然又冒出一句“生活可能就這樣了吧”。
“但有時候還是會生悶氣“,唐粒栩提高嗓音,一字一頓。
“生什麼悶氣?”
“爲什麼別人能做好,我就做不好!”小傢伙既生氣又不服氣。
“哎呀!英師父!又死啦!”唐粒栩好像又輸掉了遊戲。他倆互相不叫哥哥弟弟,也不叫小名,他們稱對方爲“英師父”和“粒師父”,頗有點江湖俠義味道。
化妝間的對面是審片室,裏面坐着曹心,《寒梅疏影——槓上技巧》的導演。
曹心出身於一個文藝世家,1998年他進入成都戰旗文工團,起先學舞蹈,後來轉到雜技,“舞蹈跳轉翻就到頂了,人不可能在空中翻轉兩次。但雜技可以,藉助一個道具,就可以挑戰更高的難度”,他說“雜技可以把你拔起來”。
他還喜歡雜技團的單純,就像雜技表演本身,一個託着一個,底下的人問上面的人“站穩了沒有”,上面的人問託底的人“還撐不撐得住”,大家都是以性命相交。
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也困惑過,不願對外稱自己是搞雜技的,一說就有人讓他表演吞劍、胸口碎大石。
雜技起始於民間生活,鍋碗瓢盆皆可入戲,疊羅漢頂梯子五花八門。影視劇要高於生活,才能引人入勝,於是吞劍、胸口碎大石常出現於熒幕。只要一落難,人們就得捂着瓷碗,上街耍個雜耍,討些盤纏。楊鐵心穆念慈、蘇乞兒、包龍星、小燕子、周瑩都沒能逃過這命運的插曲。
雜技歷來都與“寒磣”抱團取暖。有家長帶孩子來看錶演,曹心聽到最多的兩句話是:
“不好好讀書,就送你來學雜技。”
“不好好讀書,將來就只能像他們一樣搞雜技。”
今天再說起這些糟心事兒,曹心不再介懷,笑出滿臉皺紋。
影視、音樂、話劇都有它們強大而穩固的受衆羣,雜技依然還在理想與現實的窄巷蹣跚前行,但曹心不信這個邪,每次都想着法兒地玩出花樣。比如這次的《寒梅疏影》,作爲國際性藝術節,格局上,他取梅花爲武漢市市花的標誌性意義,又取“梅花香自苦寒來”的精神象徵。
可看性上,他將雜技融入傳統戲曲元素,同時運用高新科技進行設計,使得梅樹既可以左右搖擺、又可以360°的3D旋轉,以此增強雜技給觀衆帶去的視覺衝擊和互動效果。
演員選用上,曹心還使了個“小心機”,“我們出少兒團隊跟世界比,我們雖然是少兒的團隊,但作品還是成人的、大團的品質。要讓大家看到,武漢團依然是武漢團。”
時間撥回到1950年,“頂碗皇后”夏菊花一路唱着《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從湖南衡陽來到武漢,進入了漢口民衆樂園。
當時民衆樂園雍和廳被形容爲“雜技窩子”,每天輪換演出雜技節目20多個。前有道光二十年,天門、沔陽等民間雜技藝人到武漢賣藝;後有武漢解放之時,著名雜技家、魔術師等雜技團體固定在民衆樂園演出。雜技在武漢孕育、壯大。
1953年,武漢雜技團成立;1992年,武漢雜技廳建成,從此,兩年一屆的“中國武漢國際雜技藝術節”,在這裏如期上演,80多個國際大獎,武漢團拿到手軟,風頭一時無兩。
今年的武漢雜技節還在繼續上演。
舞臺中央,演員們演繹着一份遠離江湖的孤傲與野逸,曾經的恩怨情仇和流離顛沛,走街串巷和風吹雨打,都化爲一朵凌寒綻開的梅花。
武漢世界級的雜技盛會
送你2張11月1日閉幕式門票
快帶上家人和朋友現場感受吧
福利獲取詳情
請後臺回覆關鍵字“武漢雜技節”
文 // 廖文婷
圖 // 束也
錯過將再等兩年~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