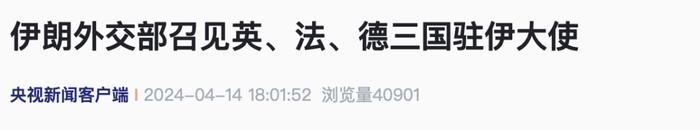錢學森與“火箭軍”
2009年10月31日,兩彈元勳錢學森逝世。今天,讓我們一起回顧這位上海交通大學校友和他的“火箭軍”往事。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回到新中國。新政府對這位國際著名科學家極爲重視,事前已對錢學森回國後的工作安排給予了充分的考慮。儘管回國後錢學森名義上是中國科學院新成立的力學研究所的所長,但實際上,錢學森的工作重心是在領導中國火箭武器的研製上。火箭武器的俗名“導彈”,就是錢學森建議的。“導彈”一詞,兩個字表達了兩層含義,既表達了可控之意,又表明是一個炸彈,是火箭武器的最好表達,一直沿用至今。
錢學森回國後,赴東北考察,其中很重要的一站,就是考察著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國防科技大學的前身),哈軍工第一任院長陳賡大將親自陪同錢學森參觀哈軍工。考察參觀期間,陳賡與錢學森關於新中國研製導彈的一段對話,已成經典臺詞,屢被引用:
陳賡問:錢先生,你看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
錢學森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什麼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不成?
陳賡豪氣頓生:錢先生,我要的就是您的這句話!
陳賡當時是兼任哈軍工的院長,他實際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因此是可以代表中國軍方高層的。正如錢學森所回憶的那樣:“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說這事的是陳賡大將。”
12月26日,病中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在北京醫院的病房中會見了錢學森。彭德懷也是最爲關心火箭武器的軍隊領導人之一,他和陳賡都是打過朝鮮戰爭的,對中美在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上的巨大差異,有着痛切的親身感受,故而對發展尖端武器格外上心,對錢學森這樣的人才也格外關心。錢學森回答了彭德懷關心的導彈研製的一些關鍵問題,這讓彭德懷看到了中國導彈事業的希望。彭德懷還指示陳賡,要請錢學森給軍隊高級幹部講課,讓軍隊高層指揮員知道導彈是怎麼回事,爲什麼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用導彈武裝起來。這從另一個側面可以看出彭德懷對發展導彈事業的良苦用心。正是有了彭德懷的這個指示,纔有接下來錢學森在給高級將領講課中呼籲成立“火箭軍”之事。
對於新中國來說,1956年是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既是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開局之年,又是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向科學進軍”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中國應當有大批知識分子。他號召全黨要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爲迅速趕上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而奮鬥。
在這樣的背景下,錢學森給軍隊高級將領講課,意義特殊而重大。
圖說:大學生清明祭奠先驅 “錢學森”手捧菊花 來源/視覺中國(下同)
據當事人總參作戰部空軍處參謀、後來的二炮司令員李旭閣回憶,錢學森的講課安排在1956年元旦下午三點。賀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元帥也特意趕去聽課,錢學森授課規格之高以及所受重視程度,由此可知。據記載,錢學森在講課時,在黑板上寫下“火箭軍”三個字。他說,這“火箭軍”,也就是導彈部隊,是一支不同於現有的陸、海、空三軍的新型部隊,是一支能夠遠距離、高準確度命中目標的部隊,是現代化戰爭中極其重要的後起之秀。興之所至,錢學森大聲疾呼:“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製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議中央軍委,成立一個新的軍種,名字可以叫‘火軍’,就是裝備火箭的部隊。”
“火箭軍”之名由此而來。歷史總是在傳承中發展,今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之成立,就是對歷史的最好詮釋。
其實,就在錢學森1955年底考察哈軍工的前幾天,時爲哈軍工教員的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駿三人給陳賡寫了一個報告,並請陳賡轉交中央軍委。這個報告提出,我國應當重視發展火箭技術和研製火箭武器。由此可見,錢學森並不是提出在中國發展火箭技術、研製火箭武器的第一人。遺憾的是,由於此三人當時的分量並不重,所提報告也不具體,軍隊高層對火箭又不瞭解,因此,這個報告並未產生什麼影響。
儘管錢學森不是提出新中國要重視發展火箭技術和火箭武器的第一人,但是,新中國確定優先發展火箭、導彈的重大戰略決策,卻與錢學森密切相關。
1956年2月4日,周恩來會見錢學森。這是錢學森回國後,周恩來第一次會見他——儘管這次會見並不正式,會談的主題當然是火箭。周恩來指示錢學森,儘快起草一份關於發展我國火箭事業的報告,提交中央審議。
2月17日,錢學森向周恩來提交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這個意見書要解決的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中國到底是要優先搞導彈還是要優先搞飛機?
圖說: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資料
3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錢學森與新中國的將帥們展開了討論,中心議題就是爲什麼中國要優先選擇發展火箭導彈而不是戰鬥機?錢學森給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首先看發展戰鬥機的問題:一代戰鬥機的研製週期,發達國家是十年,形成武器列裝到部隊,要15年。發達國家尚且如此,那麼我國呢?我國工業薄弱,能設計卻不能生產,有能力製造,但大量的儀器儀表、電子元器件和配套的雷達等,都難以保證。15年的週期肯定不夠!即使解決了這些,以我國的經濟實力,大批量生產也不現實。
再看導彈的比較優勢:飛機有人駕駛並需要反覆使用,各部件都必須過關才能保證安全。導彈就不同了,它是自動尋找目標,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們工業落後,不能確保每個部件是最好的,但根據系統工程原理,把一般的部件組合起來,同樣能達到很好的效果。
最後,通過上述兩點的比較,可以得出優先發展導彈的高性價比:導彈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科研、試驗上,一旦研製成功,國家再窮,生產一部分應該不是問題。即使從戰爭角度看,導彈不僅對地面,也可以對空中、海上來犯之敵進行有效打擊,在我國空軍、海軍還很弱的情況下,選擇從導彈上突破,不失爲一條捷徑。
應當說,當時的決策層和錢學森都是務實的。僅憑中國當時的經濟實力、工業水平和製造能力,短時間內大批量造出飛機併入列部隊用於實戰,的確很難做到。於是,新中國做出了研製“兩彈”的戰略決策。事實證明,這個決策是對的,“兩彈”全面成功,壯我國威、軍威,影響深遠。但是,也不是說這一決策就沒有負面影響。由於飛機研製沒有享受到“兩彈一星”那樣的戰略地位和扶持——儘管飛機的研製一刻也沒有停步,因而其發展水平無法在根本上得以提升,大大落後於世界。軍用飛機的命運尚且如此,民用大飛機的研製就更加沒有影子了。這也是進入新世紀之後,爲什麼黨中央下大決心,研製大飛機的深層原因之所在。
作者:黃慶橋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