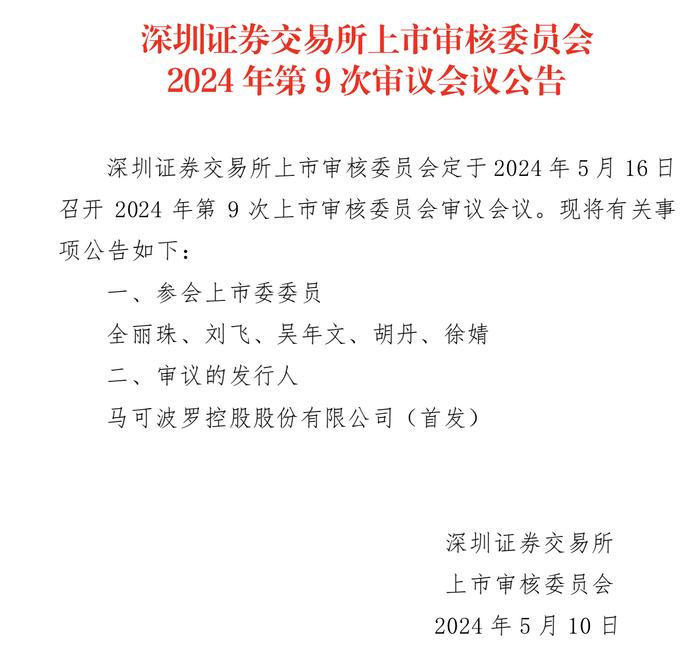巴黎圣母院,我们的误读
烈焰熊熊,浓烟滚滚中,巴黎圣母院标志性的93米高的塔尖在大火的吞噬中像一根脆弱的细竹竿拦腰断裂坍塌……这一活生生的视频画面像当年911恐怖袭击的飞机穿过双子星一样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巴黎时间2019年4月15日,教堂大火持续中,巴黎大主教Michel Aupetit发了一条信息给“巴黎所有的神父”:“消防队员仍在努力拯救巴黎圣母院的塔楼。(大教堂的)框架、屋顶和尖塔被吞噬。让我们祈祷。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敲响你教堂的钟声来邀请人们一起祷告。” 主教的呼吁中,我悲哀地看到人类无助的面孔。
说真的,这些年人们祈祷的事情已经多到令这个庄严的动作似乎变得随便和轻佻了,更让那毫不费力可以显示自己“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尚的人变成了一种作秀姿态。而所有善良人的祈祷不过是无奈中的无奈,向种种毁灭的宿命默哀而已。
2015年夏,陪女儿去法国参加音乐节,音乐节结束后在巴黎短暂驻足,自然要去巴黎圣母院。不巧的是,那天圣母院因故关闭,我们只好在教堂外逗留,在广场上和塞纳河旁以巴黎圣母院为背景拍几张照片。虽然心里想着圣母院又不会长脚跑掉,总有机会再来。然而那一刻心里却掠过一层阴郁和忐忑。我们到达圣母院广场时正是阳光灿烂的午后,一直留恋徘徊到太阳西沉到塞纳河。在夜幕开始降临时才登上旅游线路上最后一班巴士。回望夕阳下的巴黎圣母院,突然想象到她在夜幕下的景象禁不住一阵心悸:这庞大的美丽,也仿佛是一个庞大的忧患。
第一眼看到新闻上深陷火海的巴黎圣母院,立刻想到当初离开时回眸一瞥的心悸,不禁喟然。这些年时常被莫名的悲观情绪笼罩,特别是面对巨大的辉煌和至真至善的美好。近日网路上不少人引述了电影《Before Sunset、If Not Now》(《爱在日落黄昏时》)的台词:But you haveto think that Notre Dame will be gone one day(你不得不想到,有一天巴黎圣母院会消失的)。李察•斯图尔特•林科雷特在2004年的这部爱情片里让主人公说出如此宿命感强烈的悲观话语,是咒语还是预警啊?
想起17岁刚靠进大学中文系,处于好奇,也不乏虚荣,跑到图书馆抱了一堆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每一本借出的《巴黎圣母院》的前两章上百页都新得像没人碰过的,后面的部分每一页的角都卷着边,烂熟不堪,而那部分很新的页码,恰是雨果浓墨重彩、细致入微地描述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的文字。显然大多读者略过了描述教堂建筑的“枯燥”文字而直接跳到故事情节。老师们和文学理论家们的解读,也只是把这当作烘托人物和故事的环境描写。其实,我们长期误读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稍稍回顾一下历史。法国大革命摧枯拉朽地横扫了旧制度下的一切,以“平等、博爱、自由” 代替了君主专制,固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革命也带来极大的破坏,粗暴地将传统与现代一刀两断,捣毁一切过往的文化成就,艺术品和建筑遭到尤为惨烈的毁灭。全世界的暴力革命都有一种可怕的共性。本文就不说了。回到雨果的年代,欧洲社会各阶层尤其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后深感失望,他们发现大革命所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远非启蒙思想家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于是寻找新的寄托的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了。雨果则是浪漫主义第三波高潮中(1827-1848)的中流砥柱,他和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公开向捣毁文物古迹和修道院的激进分子宣战,称他们为“黑帮”团伙。他写诗撰文呼吁保护中世纪建筑,认为那些建筑身上有“古老民族光荣的证据”和“有关国王以及民族传统的记忆”。
从1163第一块石头奠基至1345年全部完工,巴黎圣母院的建造历时180年。落成后也曾历经劫难,尤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教堂内大部分财宝都被破坏或者掠夺,被移位的雕刻品和砍了头的塑像散落四处,唯一的大钟幸免没有被熔毁,雨果写作《巴黎圣母院》之前看到的巴黎圣母院已是千疮百孔。与其说伟大的作家以巴黎圣母院来烘托埃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以及书中包括主教在内的所有主要角色的命运,不如说是借人物命运来书写巴黎圣母院这座民族文化、人类文明载体的命运,更为契合雨果的写作初衷。他在书中写道:“在这个堪称是我们所有大教堂的年迈王后的脸上,每一皱纹的旁边都有一道伤疤。时毁人噬。这句话我情愿这样译为:时间是有眼无珠,人是愚不可及。” 可惜很久以来,我们只看到了雨果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却不懂他的浪漫主义艺术构思中蕴藏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和对人间世事的终极洞察。而那时的雨果才29岁,敢情是上帝派他来省察人世的悲苦命运?
正因《巴黎圣母院》的发表引起的巨大反响,引发了法国上上下下对代表着自己民族记忆的这位“年迈的王后”的悲悯与振兴的热情,1844年开始了重现圣母院旧日荣光的修复计划,工程历时23年。修复后的巴黎圣母院几乎保持了最初的原始风貌,那地标性的高耸的塔尖就是那时获得修复而呈现给后世的,挺过了一次战火,却未料在一个貌似平静春天的傍晚葬身于大火。
让我们再度翻开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天才的作家早在故事开始之前的一段序言中,就表达了他对这座人类旷世杰作的建筑物的命运深深的忧虑。他说自己曾在参观圣母院时,或者说在那里追踪觅迹时,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发现一个被岁月侵蚀而发黑、已深深嵌入石壁的手刻希腊文字ANARKIA(宿命),立刻感觉到其中“难逃定数的命意”而“凛然心惊”。他在序言中写下了今天读来令人背脊发冷的话,如同警世恒言:“ 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几百年前就消逝了,历经几代人,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就连这座大教堂,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
看到介绍说,巴黎圣母院93米高的塔尖上有个金属公鸡,里面安放了三样圣物:耶稣紫荆冠上七十根刺中的一根刺,巴黎的第一位主教圣德尼——就是那位抱着自己被砍掉的头颅继续奔跑的忠贞信徒、和巴黎守护圣人圣日内瓦耶夫的圣骨。这个塔尖本身也是一根避雷针。公鸡身上刻着拉丁文:“上帝,在雷电、风暴、邪恶中拯救我。”
原来这个塔尖一直感觉到自己身处危机,随时有厄运袭来啊。这和雨果述说自己写作《巴黎圣母院》的因由竟然不谋而合。
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誓五年之内修复巴黎圣母院,重建塔尖。奇迹的是,塔尖上的公鸡居然被找回,尽管被摔得变形了,但毕竟幸免于烧毁。93米的塔尖和整个大教堂十字架屋顶是彻底烧毁了,这屋顶则是大教堂最古老的部分。而在火灾情势尚不能预测发展和结果之际,媒体竟然一致地报道了火灾的起因是翻修工程电线短路引起。只是我很疑惑这毁灭人类文明、艺术、智慧的火灾轻而易举地就被推断为一次“意外”,真不敢想象还有什么不能发生于意外呢?
雨果早就断言巴黎圣母院所遭受的和继续将要遭受的破坏,人为的破坏远远胜过时间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坏。难怪雨果在书中不惜大量笔墨描绘巴黎圣母院建筑的精美绝伦,真是用心良苦深远啊!他恐怕已经思虑到将来某日这辉煌的教堂万一消失,人们或许还可以从他的文字里追怀她昔日的光彩,正如他自己凝视着刻在圣母院钟楼石壁上的神秘文字,想象着那未知的命运,“就这样湮没无闻,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如缕的追怀了。”
宇秀(Yu Xiu):祖籍苏州,现居温哥华,有“痛感诗人”之称。作品被收录于五十余种文集,各类获奖不提。散文随笔集《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盛行坊间,影响广泛。新近出版诗集《我不能握住风》、《忙红忙绿》,由洛夫、痖弦等海内外名家联袂推荐,被评为“2018年度十佳华语诗集”。
文字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及时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