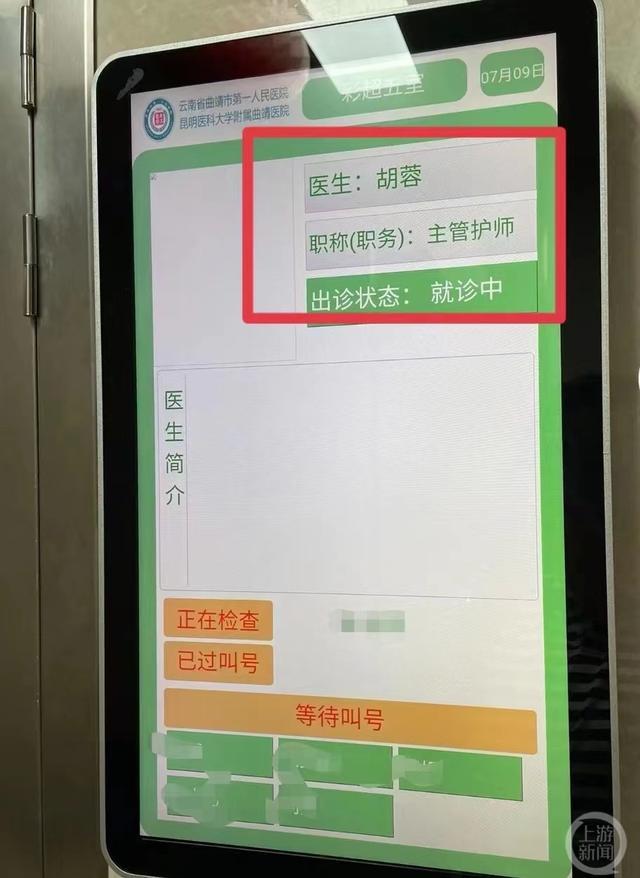進入ICU的患者致死率高達67% 活着意味着一切!
摘要:1月24日除夕,範學朋領着8個醫生和20多名護士來到武漢市第五醫院時,一夜便收治了60名患者。爲了“保留患者的尊嚴”,翻身的時候,護士們用藍色毛毯遮住她的私密處——這是ICU病房裏的慣例。
(原標題:【特寫】凌晨裏的ICU:活着意味着一切 | 疫中人)
護士們爲患者調整氣管插管,他們用一次性手套爲導管做了個支架,並寫上祝福的話語。
在咪達唑侖(一種鎮靜劑)的持續作用下,這位73歲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已昏迷數日——她的血氧飽和度一度低至60%,黏液充斥着她的肺部。
每4個小時,護士們會對她進行一次鎮靜評分,用輕拍和呼喚名字的方式來測試她的反應。在她最危險的時候,重症醫學科主任範學朋爲她接上了全院唯一一臺ECMO(人工肺)。這臺數百萬元造價的設備體外接管了患者的肺部,通過靜脈向患者的臟器運送氧氣,並泄出二氧化碳。
這是武漢市第一醫院3樓ICU負壓房內的景象。它危險重重,被層層包裹。進入這裏的患者,致死率高達67%。
範學朋穿過一樓空蕩蕩的大廳後,通過扶梯抵達3樓ICU門外。發放物資的護士們早已備好防護設備,他必須小心翼翼,嚴格按照流程穿戴它們,避免任何部位暴露在高濃度病毒中。整個過程通常需要消耗30分鐘。以護士們在每個人前胸、後背上寫下他們的名字,範學朋的稱呼是“BOSS範”。
他推開藍色大門,便是另一個世界。在這間20平方米的ICU房間內,患者被機器和導管包圍。從鼻腔進入的氣管插管深入她的體內23公分,胃管則深入100公分,直抵腸道。這一切,她一無所知。
她雖仍身處險境,但病況已有好轉。爲了增加她的身體活性,迫使她陷入昏迷的鎮靜劑已減至40毫克/小時。例行尋房時,範學朋拍了拍患者的臂膀,呼喚着她的名字,又湊近她,翻開對方的眼瞼。患者沒有反應。
護士們開始爲患者翻身。這通常是他們交班後的第一項工作。爲了避免長期臥牀所引起的褥瘡,護士們用枕頭改變患者的體位,使她的身體側往不同的方向。患者身無一物,以便導管插入。她像一艘船那樣停滯下來,寂靜,沉重。爲了“保留患者的尊嚴”,翻身的時候,護士們用藍色毛毯遮住她的私密處——這是ICU病房裏的慣例。
另一個慣例關乎時間的力量。ICU負壓房被數盞燈光照亮,除了藍、白,再無他色。監測設備和導管是冷的,取血針是冷的,只有病榻上昏迷的患者是熱的。這兩間負壓病房沒有窗戶,門總是緊閉。對於危重症患者來說,外面的時間沒有意義。護士們說,待到患者生命特徵完全平穩、恢復神智後,他們會在夜裏儘量減少對他們的打擾,只留一盞牀頭橘黃色的小燈,“以便讓他們知道日夜。”
翻身這樣的體力活需要四個護士協作。防護服裏的人們早已被汗水溼透。房內只有儀器的運轉聲,但他們交談時,還是要貼近彼此。
就在護士們爲患者翻身時,她的右腳輕輕顫動,隨後她慢慢睜開了眼。護士急匆匆叫來了正在門外電腦上查看病歷的範學朋。他又湊近看着她,他們四目相對。範學朋明白,這位73歲的患者病情正逐步平穩。而她的病友——隔壁負壓病房裏57歲的患者,情況也正在好轉,新冠肺炎導致的缺氧使她總是無意識地睜眼,護士們便用溼紗布搭住她的雙目。
這位從醫十多年的重症醫學科主任說,“活着意味着一切。”他必須細緻縝密,並且快速地來做這道生死判斷題。
現在,人們對於新冠病毒的認知仍然有限。範學朋說,新冠病毒的可怕之處,是沒有特效藥。“大部分人要靠自愈。”其中氧療、營養補給和抗菌最爲關鍵。SARS疫情後,人們的共識是不要大劑量使用激素。“而這一次的共識是,不要所有人都用激素。”
他見證了武漢疫情從開始到爆發,再到如今“牀等人”的整個過程。2019年12月末“不明原因肺炎”爆發後,作爲業務領頭人之一,範學朋帶領着同事們從本院輾轉多地,參與定點收治患者的武漢市第五醫院、雷神山醫院救治工作。隨後,他又回到這裏,參與搭建第一醫院新冠肺炎患者收治病區。
這個身處疫區中心的醫院,很早便建立了規範的發熱門診。疫情之初的1月5日,一醫院將散落在各個科室疑似病例集中管理,並讓前去診治的醫護們穿上了防護服。就在1月10日,範學朋也在臨牀發現多個病例並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他提醒同事們,要注意聚集形態發病病例。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一醫院醫護人員們感染的風險。直到現在,在範學朋所在的重症醫學科80多名醫護人員隊伍中,僅有3名人員感染,且都是輕症。現在,他們都已被治癒並歸隊。
現在,已經不是他最勞累的時候。1月24日除夕,範學朋領着8個醫生和20多名護士來到武漢市第五醫院時,一夜便收治了60名患者。他們連續工作了24個小時,出艙時已幾近虛脫。
他通常會在上午9點進入隔離病區,中午出艙,下午參加會診療會議,處理管理上的工作。病人症狀有變,他還要時刻待命入艙,索性在醫院對面仍在營業的酒店開了一間房,在最短的時間裏趕赴病房。
這本不是他的夜班。他仍然選擇深夜巡房,以便目睹“夜裏真實的情景”,查看患者病情,並與下屬們在一起。他覺得,武漢現在一線的護士比醫生更稀缺,“瞭解你的戰友,理解他們的辛苦。”
他很早便把兒子送回了湖北黃岡老家。兒子已經14歲了,父子倆每天會通視頻電話,聊聊這一天的生活。範學朋說,疫情發生後,縱然穿着防護措施,醫護們還是會害怕。“自己倒下是其次,家人倒下才是致命的。”
爲了避免風險,大部分的護士也選擇在醫院暫住。院方將他們安置在騰空的三人間病房裏。護士程詩雨也將20個月大的兒子送去了老家蔡甸區,丈夫則留守在武昌的家中。他們通常也會在晚上7點撥通視頻電話。夫妻倆常常沉默無言,看着屏幕裏的兒子喫飯,玩耍。
她第一次跟兒子分開這麼久。剛剛分離的那幾天——比如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程詩雨剛剛看見母親抱着她的兒子出現在視頻裏,眼淚便忍不住地流了下來。
一個多月過去,母子倆也都習慣了這樣的見面方式。父母給外孫看她穿着防護服的照片:“看,這是媽媽。”兒子便形成了這樣的認知,每次在電視裏看着抗疫前線穿着防護服的人們,他便會指着屏幕喊:
“媽媽。”
程詩雨和丈夫相識5年。他們會在兒子睡覺後繼續聊一會兒。女主人會在這個時候指使丈夫去做家務。以前每逢於此,他時常會試圖反抗。現在,他總會爽快地答應她。他們也數月未見,程詩雨說,疫情也深刻地改變了他們。
護士們通常會在凌晨1點半到達病區。爲患者翻身的工作結束後,他們還需要給患者抽血、在泵裏續藥,或者爲其做氣壓治療,以阻止患者因長期臥牀而導致的靜脈血栓。
他們還將持續地檢測患者的生命體徵。一般而言,體溫和血糖等常規監測的週期從1到4小時不等。對於危重症患者來說,血氧飽和度等重要指標則需要時時檢測。這意味着護士們需要長久盯住數值。他們記錄患者們體徵所發生的一切變化,以便通知醫生判斷。
現在,兩名躺在負壓ICU房內的患者,體徵已逐步平穩,醫護們也將迎來最難熬的時光。
程詩雨說,忙碌的時候,他們感受不到防護服內部的沉悶和身體的疲乏。“稍微輕鬆下來後,各種痛苦便隨之而來。”他們的衣服早已溼透,在防護服裏會聞到身子發出的餿味。長時間的壓迫式佩戴口罩,帶子會像刀子一樣割在耳朵上。當他們停下走動和體力勞動時,會感到衣物貼身的冷。凌晨5點,他們普遍感到飢餓和口渴,伴隨而來的是胃部疼痛。但這些感受,他們不能說出來。體感的痛苦,會像“傳染病”一樣傳遞給在場的其他人。
範學朋沒有表露痛苦。這一夜的工作快要結束了,他又坐回了辦公桌前。時間已近6點,早班的張醫生推開了病區的大門。他們先後來到兩位患者的病牀前,範學朋給她詳細交代了接下來4個小時裏的注意細節。
倒數第二段 範學朋的攝影作品,被擺在病房外面。攝影:魯巷
他隨後退出了病房。他曾經在交流學習時拍攝過國外的風景,便把照片掛在科室的走廊上。這些來自波士頓、荷蘭等地的風景照被他嵌入紅色相框內。他穿着防護服路過這些風景時,會抬頭看看這些生機勃勃的自然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