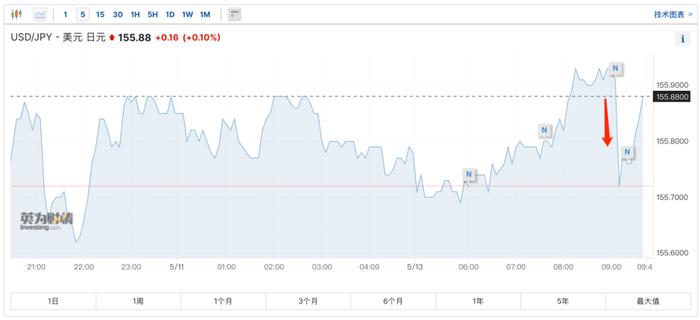翁同龢在世时的士林评价为什么那么差?
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
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
这是一段在甲午战争后流行于京师士林的人物风评。所指的人物是谁?今天的国人如果仅仅从教科书上了解那段历史的话,可能会大跌眼镜。这风评说的是两朝帝师翁同龢。
在今日历史教科书中,翁同龢可是一个形象高大的政治家,他是两朝帝师,是清流领袖,是主战派,坚决反对投降,是维新人士的有力支持者。
这些说法从字面上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评价历史人物,远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化那么简单。后世许多人评价从甲午之战到戊戌变法,总认为主战派是正义的,主和派是懦弱的;帝党是维新的,后党是守旧的。而翁同龢站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帝党中坚,自然也代表正义。
历史评价往往各取所需,以政治立场来取舍。而在当世时,时人对一个重要人物,更着重于他的人品,他的功过。
简而言之,翁同龢是甲午之战的重要推手。他如此做并非爱国,而是因为翁氏家族和李鸿章的私怨。据说是早年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因为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任安徽巡抚时,错用苗沛霖,而拟稿参劾,翁同书几乎丧命。他希望通过对日之战来消耗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如果清廷赢了,他是主站第一大臣;如果输了,李鸿章的政治势力自然受到打击。
胡思敬《国闻备乘》有《名流误国》条,详述了翁同龢促成了“甲午浪战”
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
同龢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
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也。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且献夺嫡之谋。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
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恐,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后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自是党祸渐兴,杖珍妃、谪志锐、罢长麟,汪鸣銮、同龢亦得罪去,謇及廷式皆弃官而逃,不敢混迹辇下。德宗势日孤而气日激,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难作矣。
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的记述佐证了胡思敬之说。
是时张季直(注:即张謇)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
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
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
“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就是借刀杀人之术。借国事而报私仇,这样做无论如何称不上忠臣吧?
翁同龢能青云直上,固然和自己的文章之才有关,更与其门第昌隆相关。其父亲翁心存也曾是帝师,是大学士,门生故吏遍天下。当治国理政,文章之才并不是最重要的。翁同龢一辈子呆在中枢做官,教导小皇帝,历任各部侍郎和尚书,却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那样带兵打仗、任一方封疆大吏的经验。他脑子活,会来事,却心胸狭隘,嫉贤妒能。
官场公认这位翁师傅“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接纳而不能容异己”。对崭露头角的官场新秀和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一副礼贤下士的面目,延揽为自己所用。如对同乡张謇是这样的,对力主变法、名声甚著的康有为、梁启超亦是如此。甲午战败后,很难说他真心赞成变法,只是当时变法维新已成共识,各方所争论的是如何变。翁同龢以惯用的手法,笼络这一浪潮中的士林领袖,抢占话语权和人事权。说来说去,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如果说翁同龢给李鸿章使绊子,是因为两家有宿怨,还可以理解。甲午战败,李鸿章替整个帝国背锅,因之失势,一意主战的翁同龢仍然身居中枢,炙手可热,而对政坛上影响越来越大的另一位大吏张之洞打压排挤,足可见其人品。
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中法因越南的控制权而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是鸦片之战后清朝军队少有的一次佳绩,可在报销军费时,主政户部的翁同龢处处刁难。随着张之洞声望日高,有让其入军机之议,翁同龢担心张之洞进了军机,削弱自己的权力,大力阻挠。张之洞的《广雅堂诗集》中有一首《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药房先生即翁同书,被曾国藩参劾后,本来判了斩监侯(死缓),后来改为流放伊犁;翁仲渊即翁曾源,翁同书次子,翁同龢之侄,同治二年中状元,这一科的第三名即探花是张之洞。可见两家交情匪浅。在辑录诗集时,翁、张已经交恶,张之洞在此诗下自注:
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注:翁同龢字叔平)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
这等于一个大佬公开吐槽另一个大佬,张的幕府劝他将这段删去,以免引起风波。张之洞坚持己见,将这段注释保留,可见其心中之愤怒。
翁氏作为,可以说辜负了太后,也辜负了皇帝。所谓“后党”“帝党”,原来并不泾渭分明,慈禧太后对翁氏父子是相当信任的,否则怎么把亲儿子和嗣子同治帝、光绪帝都交给他教导?作为帝师和大臣,他本应该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极力弥合母子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年轻气盛的皇帝进行劝导,而不是相反。
若没有甲申易枢——1884年(光绪十年)4月8日,慈禧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的事件,恭亲王仍然在中枢主持大政,翁同龢的势力起不来,很可能就没有甲午之祸。对翁同龢这个人,恭亲王看得清清楚楚。马勇先生于《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写道,恭亲王临死前对来探视的太后和皇上叮嘱要提防翁师傅。
对于翁同龢,恭亲王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他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注:应该指数千万两银子打造的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列强乘此机会大有瓜分中国之势,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貰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人品,恭亲王也相当瞧不起,他告诉皇上和皇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的遗言,以及其他大臣的进谏,加上光绪帝本人的认识,终于让皇帝做出决定,驱逐翁师傅。1898年6月15日,变法刚刚拉开序幕,是日为翁同龢的68岁生日,皇帝对他下了一道旨: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让翁同龢离开朝廷回家养老,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共识,并非一些人所言是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而做出的,此时太后还是基本上让皇帝做主。但翁同龢被罢官,也并不能使变法维新顺利推行,此前埋下的隐患太多了。
翁同龢的苏州同乡、同朝为官的潘祖荫对他的评价可谓精到:
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
也就是说他对少年时的朋友依然玩心眼,使手段,可想而知对其他人了。潘祖荫预判他将来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果然是应验了。可这样的大人物,误己是小事,他误的可是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