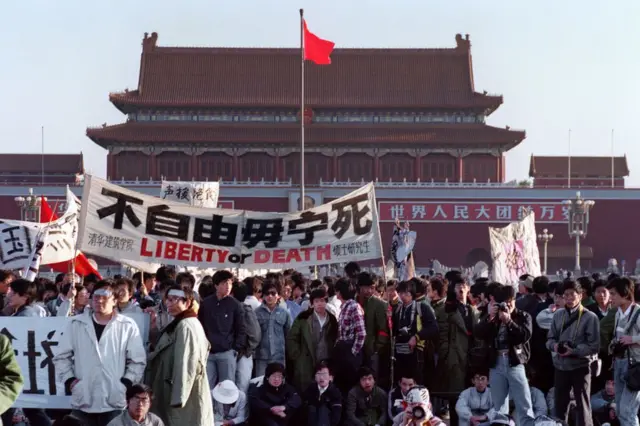周作人藏書的收繳及其佚文一篇
一、戰後周作人藏書的下落
南京《新民報》於1947年3月18日刊登消息《冀高院整肅法紀嚴禁各漢奸裝病保外就醫每週調查董康馬連良一次》:
漢奸逆產清冊,現正由敵僞產業處理局移交冀高院監察處辦理。……周作人,董康逆產中,以書籍佔大宗,張仁蠡逆產數字亦甚可驚,金條手飾約一箱,皆系僞天津市長任內搜刮者,夏肅初,錢稻孫,羅錦等逆最窮,僅有少數破爛傢俱,及舊三輪車各一輛,……聞最近即可拍賣。
郭墨狼1947年4月6日致信胡適:“報載周作人先生書籍即予拍賣,誠覺可惜,因作小文呼籲。”並給胡適寄了份題爲“周作人的書不應該拍賣,應加保存”的剪報,其中說:“周作人的財產要拍賣了,連書籍箱也在內。……應該有一個補救的辦法,使這些珍貴書籍不致有散失之虞。……不過站在文化學術的立場來說話,總覺得周的藏書輕描淡寫地因此拍賣而散失了去來,總是一種很大的損失。我們主張周的書籍最好是由國家明令交給北平圖書館或北平大學,最爲妥當。如果北平法院當局認爲這些書籍可以拍賣很多錢,那末我以爲胡先生也應該而來設法一起收買了下來。……爲什麼,因爲周的書籍頗多海內孤本,不能讓因拍賣而散失。”(《胡適來往書信選》,中華書局1980年版,下冊第194頁)
不過這些藏書並沒有被拍賣。1947年5月14日北平圖書館復原後第一次館務會議討論:“接收各漢奸書籍案。決議:聽取楊殿珣君報告後即行移運來館,現須先事預備者爲交通工具、書箱、麻繩、照料人員及存放地址等。交通工具擬借北大卡車或改僱排子車,照料人員須多派幾人,地址先借本館舊滿蒙藏文書庫存放,如不能容,再借團城後院各房存放。”(《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909-1949》,第881頁)就是此後稍晚,知堂等人藏書由平館接收。
北平《世界日報》1948年2月2日報道說:“朔歷年末即臨的一天上午,記者到八道灣北區憲兵隊的駐地,也就是當年的苦雨齋,在探望周的長子豐一君……因爲豐一君今天太廟日文圖書館上班去了,所以就由豐一君的太太帶我到他們現在住的後院西廂房裏去。房子雖很狹小,便被日本文學書籍佔據了大半個房間。外間是客廳,書房及小孩的用功地。裏間屋便是臥室,南牆上掛着一幅橫軸,是周作人坐讀的畫像……周原有的書房現在由別人住用。書籍均在北大圖書館中。”(《歲暮天寒裏訪問“苦雨齋”》,載肖伊緋《苦雨齋鱗爪》,第213頁,第215頁,引者找來原報縮微膠捲,補齊了遺漏文字)看來這時知堂藏書還剩下一部分,以日文書爲主。
二、周作人對藏書收繳的態度
南京《新民報》在1948年2月20日第二版《新民副刊·二月篇》刊載了一篇文章:
周作人與希臘學術
編者按:周作人在中國學術上的造詣與文藝方面的成就久爲世知,至其對希臘學術方面的研究則外界知者較少,最近周氏曾有一函致本報周綬章先生,自述其研究希臘學術之經過甚詳,爰爲刊佈,以饗讀者。
綬章先生左右:
去年夏天傳聞先生有文章發表,主張量移鄙人於中央研究院安置,至日前承蒙枉顧,始得見全文,對於盛意至爲感荷。唯文中稍有錯誤之處,鄙人並非專攻拉丁語文者,只是古希臘語曾經讀過幾年,雖然也曾讀過一點新約所用的那種希臘古代白話文,當初所學的原是柏拉圖克什諾封的正宗古典語,但私心所喜的還是後世頹廢時代的作品,如亞歷山大時代的牧歌擬曲,希臘羅馬時代的神話,《希臘擬曲》已譯出刊行,希臘原本的神話亦已譯出,只有註釋未曾完成。希臘神話集現代英德學者有很好的編著。可以有更爲達雅的譯本,而鄙人不自量力從事於此者,亦自有故。
鄙人於此所私淑的學者爲英國之安特路朗氏(A ndrewLang),他是一個弄雜學的人,於希臘文學外,又開創人類學派的神話學,對於神話乃禮俗有正確的新解釋,研究編著童話兒歌,寫詩人隨筆,換句話說乃是多能鄙事的。
我的希臘學力實在有限得很,但是自信對於希臘精神與神話意義的瞭解卻有一點,這也就是從雜學出來的,因此覺得還有愚者之一得,或者比較別人有點不同。
這兩年在幽囚之中,也未嘗不想利用閒暇,來寫一點東西,譯述一種科學整理過的希臘神話集,或是兒童的神話故事,但是參考書不可得,終於只好擱起。
鄙人所有的研究參考用書籍悉被查封,去年在大文發表的兩月後,移至北平圖書館,當時小兒不曾見告,由上海友人間接告知,頗表示不平之意,鄙人其時也曾想對法院聲請,其理由是所謂財產原列有書畫一項,但書籍並不在內,而是書籍非是古董,至少鄙人所有的中文書明板也絕少。外國文書並無珍本,卻只是參考用書,可以說是職業用的工具,不當在沒收之列。但是反覆考慮之後聲請的意思也就打消了。
前年我出過幾次庭之後,有新聞記者問我,從前稱許倪雲林被張士信所打,絕口不說話,以爲一說便俗,爲什麼這回如此不憚煩地辯解,我答說這回是對於政府的辯訴,所以不相同。可是這一次,我決心不再多說了,因爲覺得說也沒用,而且爲了些書籍而爲此喋喋,不免無聊,也就是雲林的所謂俗。
近十年來的大戰禍裏,有多少生命財產被犧牲了,這一點兒算得什麼,現在不曾被炮火毀盡,寇盜搶光,還能夠保存在圖書館裏,可以供有志者的閱覽,這真是十分幸運的事了。我只感覺一點抱歉,便是這些書恐怕不大能供給學人利用。中文書都只是普通刊本,只有近三十年中所蒐集的清代山陰會稽兩縣先賢的著作共約三百五十部,如不散失或者於圖書館可以有點用處。外國書也沒有什麼貴重書,而且因了我偏頗的雜學關係,這些書大抵於別人沒有什麼用的,有如關於歐洲巫術的,特別是英國怪人散茂士的著書,如《巫術史》,《巫術地理》,《殭屍》和《變狼人》等。劍橋大學出版的一本湯姆普生教授的《希臘鳥名辭彙》,雖然於我當時做神話註釋頗有用處,恐怕不見得有人會要查它,或者哪一個圖書館會得購置吧。
希臘先賢的著作中,我最佩服的是歐利比臺斯的悲劇,特別是那一篇《忒洛亞的女人們》,翻譯的志願懷抱了二十年,終於未能也不敢動手,參考書也未能多得,其原文全集,只有兩部,其一送給了北京大學,其一則在北平圖書館了。因爲承先生提及,文中有錯誤,故略爲說明,不覺說了許多廢話,尚望鑑原是幸。草草,即請近安。二月,十日,作人啓。
看來知堂於藏書被收繳不久就得知消息了。這應該是知堂第一次在獄中發表文章,而知堂相關文集都未收入此文,因而在這裏把全文錄出。據年譜,知堂1948年7月作《〈吶喊〉索隱》,刊於8月31日《子曰》叢刊第3輯,署名王壽遐(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4頁)。這篇文章的發現,把知堂發表文章的時間提前六個多月,何況還是用本名發表的。據唐弢在《關於周作人》裏回憶:“日本投降,他(知堂)以漢奸罪在南京服刑,友人將他三十首《往昔》詩抄給我,末附《狂人》、《天才》等雜詩九首,我錄了一份,卻不想在自己主編的《筆會》上發表,只登了黃裳同志的一篇《老虎橋邊看‘知堂’》。”(《唐弢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頁)當時知堂積極尋求發表作品的渠道,都被拒絕了,所以南京《新民報》刊發他那封親筆信算是破例了。
三、周作人藏書餘話
江紹原在1948年3月1日北平《世界日報》發表文章稱:“現在南京老虎橋,首都監獄愛字三七六號之周作人氏,於本年上月十日致同城某報周綬章氏一函,自述其生平對於古希臘神話及文學的研究,十九日該報刊佈全函,二十四日晚我在北平讀到。我想說的話當然很多,今天先說兩樁而已。(一)……實則據我目睹耳聞,周氏藏書早先要監禁存他家後院一間大屋子裏,後被裝箱運到國立圖書館(以上目睹,以上耳聞),而至今保存在木頭書牢中。書被種種文武男女人摸弄過是真,供有志者閱覽則決無其事。周公本身的徒刑雖已一再定期,周公的書卻尚在文津圖書獄中等候宣判。安有機會爲國家社會服務,安有自由接見有志的閱覽人?(二)……然而據我所知,至少北平有個怪人,此刻正天天想看《希臘鳥名辭彙》之類的書籍而不可得。此人已經把多年前中法大學重印的一本法文《上古神話集》譯成英文,所缺僅五分之一,此外他還計劃把德國喜陶埃丁教授的小著《希臘羅馬神話學》(增訂第五版,一九一九)也譯出供初學者研讀之用。例如昨日他所譯的那條,講晨光女神之子M e m n o n死後化爲M em nonides,這究竟是什麼鳥,他不請教湯姆普生請教誰?然而其書正在文津街坐監房,此人又安能不望洋興嘆?活人坐牢,活書也坐牢,不坐牢的人呢,天天發現整個世界便是一座大樊籠,大牢籠。”(《讀周作人致周綬章函———有感於活書坐牢》,寫於1948年2月25日,載《苦雨齋鱗爪:周作人新探》,第216-217頁)
對於《希臘鳥名辭彙》,知堂在《亞坡羅陀洛斯〈希臘神話〉引言》(1944年8月20日)裏說:“這最值得記憶的是湯普生教授的《希臘鳥類名匯》,一九三六年重訂本,價十二先令半。此書系一八九五年初板,一直沒有重印,而平常講到古典文學中的鳥獸總是非參考他不可,在四十多年之後,又是遠隔重洋,想要搜求這本偏僻的書,深怕有點近於妄念吧。姑且託東京的丸善書店去一調查,居然在四十年後初次出了增訂板,這真是想不到的運氣,這本書現在站在我的書櫥裏,雖然與別的新書排在一起,實在要算是我西書中珍本之一了。”這部“除了爲做註釋的參考用以外無甚用處的書籍”,知堂在1956年4月-6月間在翻譯《瘋狂的赫剌克勒斯》並做註釋時又用到了:“湯姆卜孫(D‘A r a yW .T hom pson)在《希臘鳥類名匯》中列舉古代傳說,但結果以爲各種天鵝均不歌唱,天鵝之歌的故事並非事實,恐另有神話的典故關係,今未能詳。”(《歐里庇得斯悲劇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62-463頁)查國圖無此書,或許就是劫後餘物,所以知堂可以作註釋時使用。
前在國家圖書館查到一套《歐里庇德斯》(E u r ip id e s,F o u rV olum es,w ithanEnglishT ranslationbyA rthur S.W ay,T he Loeb Classi-cal L ibrary,L ondon:W illiam H einem ann;N ewYork:G.P.Putnam‘s Sons,1919-1924),四冊序言開篇都有朱文長印:苦雨齋藏書印。這就是知堂信裏所提及的在“北平圖書館”裏的那套歐里庇得斯原文全集之一了。而散茂士的作品,在國圖查到一冊《巫術史》(M ontagueSum m ers,AH istory ofWitchcraftand Dem onology,London:K .Paul,T rench,T rubner& C o.,L td .;N ewYork:A .A . K nopf,1926)扉頁朱文方印:周作人印。
另外國圖古籍館有:范家相《範蘅洲先生文稿》稿本,有墨筆題記:“計文十八篇三十二葉,三十二年一月重訂,知堂所藏”,鈐朱文印:知堂書記。目次頁都是知堂所抄,鈐有朱文印:知堂書記。卷後跋語:“右範蘅洲文稿一卷,從杭州書店收得,篇首蓋有棟山印,蓋系僞爲者。此卷疑亦從皇甫莊範氏散出也。民國壬午大寒後二日,知堂識於北京。”並有朱文印:苦雨齋藏書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國家圖書館藏鈔稿本乾嘉名人別集叢刊》9)另有《舌擊編》五卷五冊(會稽粟山沈儲稿,清咸豐九年[1859],索書號:6062),卷一鈐朱文印:苦雨齋藏書印,知堂收藏越人著作。《紹興縣館紀略》(曾厚章編,民國九年[1920]共和印刷局,索書號:地240.119/9413)鈐朱文印:苦雨齋藏書印,知堂收藏越人著作。這幾種都屬於知堂信裏所說的“近三十年所蒐集的清代山陰會稽兩縣先賢的著作共約三百五十部”的一部分。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