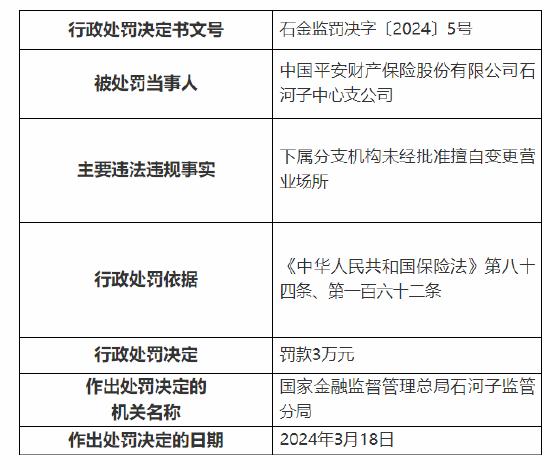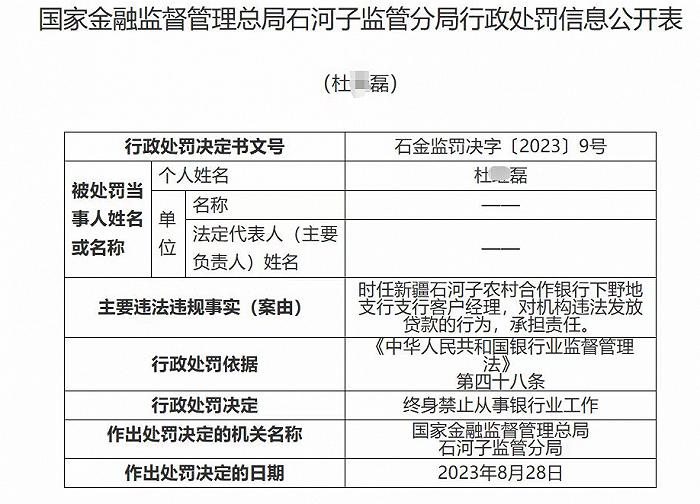石河子奠基者之一趙錫光
原標題:石河子奠基者之一趙錫光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王恩茂(右)與趙錫光(左)合影。
1950年,是春滿大地,萬象更新的一年。原國民黨駐南疆第42軍軍長趙錫光,懷着高舉義旗的勝利喜悅和盡忠祖國的凜然雄心,告別了喀什噶爾古城,揮師北上,榮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2兵團副司令員兼9軍軍長。隨即,他奉黨中央和毛主席之命率部屯墾,與老部隊的指戰員一起,披荊斬棘,舉步滄桑,在寂寥冷漠的瑪河西岸破土驅荒,踩出第一條路,栽植第一棵樹,開墾第一塊田,蓋起第一間屋。那第一代捷足先登的開拓者們,揮起了時代的巨筆,飽醮着熱騰騰的汗水,繪製了戈壁新城——石河子的宏偉藍圖。
全國解放後,根據建設邊疆和保衛邊疆的戰略需要。司令員王震提出:22兵團必須在瑪納斯河西岸創建自己的紮營基地,只有花大力氣屯墾,才能更有效地戍邊。不久,王震、陶峙嶽、張仲瀚、魚振東等視察了這一帶,經過周密踏勘,當即拍板定案,確定了建城的中心位置。
當時的石河子,低頭亂石千頃,抬頭遙空一碧,除了現今老街一帶有幾戶人家之外,舉目四顧,人煙寥寥,雜草叢生,蘆葦遍地,更有蚊蠅爲禍,野獸猖獗,部隊的生活和工作的艱辛就可想而知了,那是名副其實的“天當被,地當牀,煮把野菜當乾糧”。
同年8月,一支由30多名幹部、戰士組成的勘察隊來到石河子,梁客潯爲隊長,我是副隊長。我們的任務是要弄清石河子的水文地質情況和南山裏煤炭和木材的分佈特點,爲大部隊的進駐和開發活動提供有關數據。
經過緊張的工作,我們很快完成了勘察任務。我趕到瑪納斯,借用26師的電臺向兵團首長作了彙報,說明這裏具備建設新城的自然條件和物質基礎。建設石河子的戰鬥很快打響了。
次年春,正式組成了石河子工程處,由趙錫光任處長,張仲瀚任政委,梁客潯和周茂任副處長。工程處下屬工程組、材料組、財務組、總務組、政治處等,由我任工程組組長。趙錫光和我們一起步入了風雨同舟、甘苦與共的拓荒者的壯闊歷程。
趙錫光是一個爲人正直,作風正派,工作火熱且一絲不苟的人。在短短四五年的時間裏,他爲建設石河子新城日夜操勞、嘔心瀝血。
工程處建立之初,工程技術人員非常缺乏,趙錫光親自過問此事,四處調人。爲求賢於一位工程師,他終日奔波,坐臥不寧。最後,不得不親自出馬,登門求援於張希欽,纔將人調來了。
技術骨幹馬文達也被他請來,爲新城獻智獻力。技術人員們邊學邊幹,刻苦鑽研,我和馬文達經常爲大家講授建築設計和製圖原理。由於學用結合,大家的知識技能提高很快。
趙錫光是一個講求工作實效和珍惜時間的人,他一貫主張少說多做。他常說:“如今我有幸爲人民服務,要跑步前進。”所以,他多次強調,一切工作要從提高效率出發。每當他視察施工現場和深入班組瞭解情況的時候,手裏總是提着一個行軍凳,這樣可以就地而坐。他和廣大幹部戰士心連心,研究情況,討論問題,大部分問題都在現場解決,一分一秒地提高着工作效率。在那舉步維艱的創業年代裏,他和戰士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
爲了不影響施工進度,趙錫光力避在工作時間開會。一般的會議能免則免、能減則減,非開不可的業務會、幹部會,一律在下班後進行,經常是夜深人靜,戰士們都已休息了,他還帶着幹部們開會,安排明日的工作。
爲了加強基建隊伍,兵團領導陸續給石河子調人調物。如,後來的工程四大隊,就是從26師78團的1營抽調組建起來的。
第一連的任務是燒青磚。燃料呢?就地取材,無非是遍地皆是的葦子和蒿子。趙錫光常到磚場指導工作,聽取彙報,每次進場手就不閒着,不是壘坯就是挖土,或是動手修模子。爲了早日把新城建設好,他不讓自己的雙手有一分一秒的停歇。
有一次,磚窯漏水,很可能會造成塌窯,戰士們奮不顧身地奔向窯底,很快把漏洞堵住了。趙錫光聞訊趕來,二話不說就要下窯排險,卻被大家攔住了。當他聽說沒有任何傷亡,險情已排除時,才鬆了一口氣說:“沒傷着人就好,人可是寶貝。”
部隊上山伐木,是個苦差事,山高坡陡,雪地路滑,威脅着戰士的安全,影響着勞動效率。趙錫光看到此景,緊鎖眉頭思考了良久。當天,回到石河子後,他安排專人給戰士打了防滑的鐵爪,每人一雙,綁在腳上,戰士腳下生了“根”,他才放了心。
木工廠有位幹部叫張德燦,也是石河子的建城元勳之一。那時,部隊施工點很分散,他每天要徒步往各個工地跑,指導施工工作。趙錫光見他如此辛苦,便派人給他送去一輛自行車。可是事隔數日,張德燦依然是徒步。趙錫光關切地問他爲啥不騎車。他憨然一笑說:“我不會騎車。”趙錫光說:“你們不是有馬嗎?以後出去可以騎馬,成天跑路又累身體又拖效率。”張德燦笑笑說:“好,好。”
又是幾天過去了,張德燦既不騎馬,也沒騎車,還是兩腳疾風。趙錫光再沒問他什麼,直接送給他一副新馬鞍。原來,他了解到木工廠有馬無鞍,所以,給這位下級幹部來了個“雪中送炭”。我們的副司令員對下級是多麼關懷備至、體貼入微呀。
建城之初,部隊生活是艱苦的,我們住着蘆葦建的窩棚,趙錫光也不例外。由於積勞成疾,他患有嚴重胃病。按規定,可以到小竈用餐的,可是,一個成天與戰士同甘共苦,形影不離的人,哪有心思爲享受這特別待遇而中斷工作和甩開部隊呢?許多戰士都知道,趙錫光的口袋裏經常備着幹饃片兒,只要胃病一發作,他順手取出個饃片來嚼嚼,即充飢又止疼。
由於當時食油和青菜奇缺,部隊的伙食標準很低,趙錫光多次爲部隊食堂跑油、討米,改善戰士的生活。有一次,我隨他到南山,行至半路,他突然叫司機停車。我見他躍出車門,跑到半山腰,不一會兒,就捧着一把野菜跑回來。我恍然大悟,原來他忙於出發趕路還沒喫午飯,這一把野菜就是他餬口充飢的唯一“能源”了。
1953年秋天,當兵團第二醫院(現今石河子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破土動工的時候,趙副司令員的胃病已經相當嚴重了,陶峙嶽和張仲瀚多次勸他住院治療,他執意不肯。他表示,一定要把醫院建起來再考慮自己的病。
醫院的施工過程,不同於一般建築,設計要求高,施工難度大,爲此趙錫光幾乎是事事過目,處處把關,一絲不苟地狠抓工程的優質高工效。如手術室的地板上漆返工四次他才點頭認可。
但是,就在醫院建成的喜慶日子裏,趙錫光病情卻突然惡化,竟然臥牀不起。1955年10月,就在石河子市建成還不滿5年的時候,這位壯志未酬的將軍竟把自己的血肉之軀融進了瑪納斯河西岸的沃土中。
(本文摘自《兵團文物故事》)
來源:石河子新聞網
長按識別關注下方二維碼
搜新聞 搜美食
搜工作搜房子
搜男女朋友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