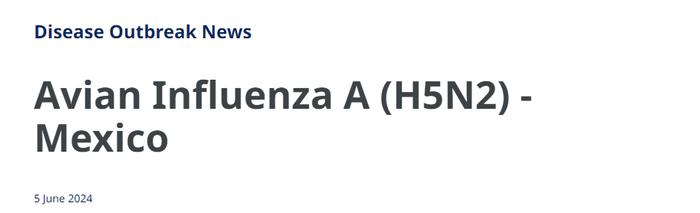新冠疫情中,國際公共衛生體系爲何失靈?
原標題:新冠疫情中,國際公共衛生體系爲何失靈?
當前以國家爲中心的疫情應對模式,不僅延緩了國際社會對疫情做出迅速有效反應,也增添了國際間合作協調的難度。
3月8日,韓國首爾,醫護人員轉送一名重症患者前往傳染病專科醫院。圖/紐西斯通訊社
“滿分100分,所有國家的平均得分爲40.2分。”
2019年10月,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與經濟學人智庫合作發佈了一份“全球衛生安全報告”(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這份報告對全球195個國家的公共衛生安全狀況進行了評估,其結果如上。
不幸的是,這項評估結果正被新冠病毒的全球性爆發證實。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斯圖爾特·帕特里克稱,疫情發生時,全球公共衛生系統有序運轉取決於三件事:主要受災國政府採取及時、可信的行動;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協調國際應對方面的正確領導;其它國家爲保護本國公民免受疾病侵害而採取負責任的行爲。
帕特里克補充說:“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疫情以及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都證明,要做到這三件事並不容易。”
“節省”,讓我們此刻支付更多
民衆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嚴重程度感到不解和憤怒。在請願網站Change.org上,一份要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辭職的請願被超過50萬人聯署。
凱利·李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健康科學教授,也是加拿大全球健康治理領域的一級學者(Tier 1 CRC),曾參與建立世衛組織全球變化和衛生合作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on Global Change and Health)。
對於我們爲什麼會對新冠疫情感到措手不及,凱利·李告訴《中國慈善家》,首先,我們原本應該對世衛組織投入更多資金,因爲各國協調行動是抗擊重大疫情的最佳方式。她指出,當前世衛組織的年度預算約爲20億美元,僅相當於美國一家小型醫院的預算。“公共衛生科學家、醫生、政府官員和其他許多人一再呼籲增加對全球衛生治理的投資,但這些呼籲基本上被忽視了。”
凱利·李進一步指出,許多國家在內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以及向所有公民免費提供醫療保險方面,也沒有充分投入。包括很多高收入國家在內,其領導人都做出了削減公共衛生資金的選擇。“我們先前在用以保持社會安全的公共產品上沒有合理投資,結果是我們此刻支付更多,” 凱利·李說。
3月15日,印度新德里,工作人員爲公交車消毒。圖/法新
她還提出,這次疫情的爆發在警醒我們需要更加尊重自然環境以及野生動物。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疫情爆發的次數明顯增加,引發這些疫情的病原體種類也明顯增多。“人畜共患病是這些疫情爆發的主要原因,而這一時期恰逢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告訴《中國慈善家》,這次新冠疫情,一方面反映了發達國家應對國際性緊急衛生事件的疾控體系是有瑕疵和漏洞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健康治理的思路和規則需要進一步改變。
黃嚴忠認爲,當前以國家爲中心的疫情應對模式,不僅延緩了國際社會對疫情做出迅速有效反應,也增添了國際間合作協調的難度。
資金不足、議程超載的世衛組織
世衛組織是聯合國下屬的專門機構,也是國際上最大的政府間衛生組織。1948年成立以來,世衛組織在協調全球公共安全應對上曾取得巨大成就——比如其40年前推動國際合作消滅天花。
然而當前,捉襟見肘的資金、龐雜的管理事物以及僵化的官僚體制,正使世衛組織運轉乏力。
在此次新冠疫情應對中,世衛組織被質疑反應遲緩。3月11日,世衛組織宣佈此次新冠疫情經評估可定性爲“大流行”(pandemic)。較多專家認爲,世衛組織“大流行”的宣佈得太遲。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湯勝藍更指出,世衛組織對“大流行”的宣佈缺乏量化指標:“到底多少國家出現多少病例、多少病死數可以定性呢?”
《英國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就埃博拉病毒2018年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爆發而言,世衛組織於2018年10月和2019年4月舉行了會議,並建議不要宣佈其爲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儘管在這兩次會議時都滿足宣佈的標準。文章認爲,世衛組織對疾病的定性,存在政治考量等不相關因素。
在此次疫情應對中,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2月初就呼籲國際社會籌集6.75億美元,以增強發展中國家防疫能力,但到3月4日僅收到2.89億美元。爲繼續籌資,世衛組織只得發起一項“COVID-19團結應對基金”,號召世界各地的個人、公司和機構直接捐款。
自上世紀90年代,美國便以世衛組織部分主張觸犯其商業利益爲由,削減對世衛組織的預算。近日,美國政府更在向國會提交的2021財年聯邦政府預算報告中,將向世衛組織提供的資金支持從1.23億美元減至5800萬美元。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新加坡前駐聯合國代表馬凱碩批評稱:“如今,美歐都在飽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它們是時候嚴肅地捫心自問一下,數十年來削減對世衛組織的經費支持是否明智。”
20年前,在世衛組織的資金預算中,成員國分攤會費與其收到的捐款是持平的。而如今,成員國分攤會費僅佔其總資金的20%左右。在其收到的捐款中,用於指定項目的捐款佔比達80%以上。也就是說,這些捐贈大多帶有附加條件,資金必須用於特定項目或疾病。
這些捐款有些來自希望提供額外捐助的成員國,有些來自教育機構、信託機構和慈善機構。在世衛組織2018-2019年預算來源中,捐款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美國、蓋茨基金會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
捐助資金遠高於成員國分攤會費資金的弊端是,世衛組織的優先事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捐助者左右。蓋茨基金會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根除小兒麻痹症,世衛組織2016年的財政細目表明,其用於小兒麻痹症的資金是最充足的,佔比爲23.5%,其後纔是疫情應對,佔比15.3%。
英國傳染病專家傑里米·法勒認爲,世衛組織成爲“一個完全受人尊重的組織”的最佳方式,是爲全球公共衛生事務制定最高優先事項。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的前首席執行官芭芭拉·斯托金指出,疫情應對應該是世衛組織的核心,“如果世衛組織不處理世界各地的衛生緊急情況,那麼它的作用是什麼?”
然而,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的報道,2016年建立的世衛組織衛生突發衛生事件規劃(WHO Health Emergencies Program),也正是此次領導應對全球新冠疫情的部門,長期資金不足。該部門內部多次評估這會對世衛組織造成嚴重危害,因爲“它無法充分管理多個、同時或連續的高級別緊急情況”。
在資金不足、無法掌控優先議程之外,世衛組織還被認爲承擔了超出其能力範圍的工作。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健康科學教授理查德·沙利文說,在世衛組織成立的1948年,全球健康治理的焦點就是控制傳染病,“事情要簡單得多”。“重要的是記住WHO的成立初衷是什麼,非傳染性疾病根本不應該在它的管理範圍之內,” 沙利文指出。
然而,世衛組織正被其成員國決定的過於廣泛的議程分散注意力。從曬傷、家庭暴力到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和鼠疫,這種覆蓋議題的複雜性,被認爲是世衛組織功能失調的原因之一。“世界上沒有任何組織能夠覆蓋所有這些主題,並保持足夠的深度和權威性,” 傑里米·法勒表示。
凱利·李告訴《中國慈善家》,從艾滋病到寨卡病毒,世衛組織正將其原本就匱乏的資金,分攤到廣泛的管理項目上。

2月28日,瑞士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中)在當天的世衛組織例行記者會上講話。圖/法新
目前,在譚德賽的領導下,世衛組織還在試圖解決一個持續多年的難題:總部與六個區域辦事處之間的溝通不暢。
世衛組織的組成架構在聯合國機構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爲它旗下設有六個區域辦事處,每個辦事處都有自己的主任,由區域成員國選舉產生。批評人士認爲區域辦事處享有太多自主權,降低了世衛組織的運行效率。
譚德塞內閣負責人伯恩哈德·施瓦特蘭德稱,譚德賽正通過改革來強調世衛組織的核心使命,雖然世衛組織現已形成的複雜官僚架構“就像一艘大型油輪,讓人無法輕易地扭轉局面”。
凱利·李稱,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發後,包括世衛組織自身在內的很多組織都在討論其可以如何做得更好。“世衛組織再次進行了改組,增設了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還學會了更加精簡地處理流行病情報。”
專家呼籲國際合作而非各自爲政
15年前,世衛組織對疫情的全球應對行動框架《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進行了重大修訂,旨在糾正全球在2003年SARS疫情中的應對缺陷。
《紐約時報》指出,簽署該條例的各成員國給自己留了一個漏洞,並正在新冠疫情應對中利用它。當時,各國談判代表達成了一項折中協議,即在“公共衛生考慮和保留最終政治權力”之間取得平衡。該協議的本質是各國不願意將疫情應對的全部控制權交給一個國際機構。
在此次疫情應對中,各國的各自爲政表現得尤爲明顯:爲保證內部供應,限制防護用品出口;在沒有通知世衛組織的情況下實行國際旅行限制;特朗普甚至試圖買斷一家德國企業正在研製的新冠疫苗。
凱利·李向《中國慈善家》指出,《國際衛生條例》規定了世衛組織成員國的義務,規定了每個國家爲支持全球衛生安全系統而同意提供的核心能力,也規定了各國在疫情發生後應如何採取行動。“問題是世界各國政府忽視了這些條約的關鍵部分。”
她認爲,我們應該把新冠疫情的爆發看作未來更嚴重、更致命的疫情爆發之前的一次試運行。“我們需要停止以民族主義爲名而削弱多邊機構,全球團結一致才能制止病毒。”
2015年,22名研究人員反思世衛組織在非洲埃博拉疫情中的應對遲緩後,在《柳葉刀》(The Lancet)發佈了一份針對世衛組織的改革建議報告,號召各國政府、科研界、產業界和非政府組織制定一套在疫情期間運作的規則框架,以共享流行病學、基因組和臨牀數據。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人口健康信息技術中心創始人喬納森·韋納教授,向《中國慈善家》進一步肯定了這種國際合作在抗疫中的重要性:“目前關於新冠病毒最好的科學數據都來自中國”,這種對於數據和研究的迅速、自由的分享應該成爲未來的常態模式,以“改善我們共同居住的地球的健康狀況”。
世衛組織之外,NGO活躍在舞臺
針對世衛組織的主角光環漸失,還有一種觀點認爲,其原因在於近十幾年來從事醫衛工作的國際組織越來越多,世衛組織的人才與資金被分散。
蓋茨基金會是新冠疫情應對中表現活躍的國際機構之一。早在1月27日,蓋茨資金會便宣佈向中國提供500萬美元緊急捐款用於抗擊新冠疫情。3月10日,蓋茨基金會宣佈其將牽頭另外兩家大型慈善機構捐款1.25億美元,加快對新冠病毒治療方案的研發。
世衛組織的主要職能並不涉及直接的臨牀醫療護理,而這恰恰是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MSF)的活動核心。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來,無國界醫生在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等國家開展醫療救援工作,甚至在聯合國批准下向朝鮮捐贈了醫療設備。根據無國界醫生官方網站3月30日發佈的消息,該組織在西班牙雷加利斯及馬德里最新提供了超過200張病牀。
黃嚴忠指出,和國內的抗疫模式不同的是,在歐美,除了政府組織之外,民間的非政府組織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不管是公司、學校還是非盈利機構。
凱利·李告訴《中國慈善家》,完全依賴私營公司和商業激勵來開發藥物、疫苗會導致很多問題,因爲私營公司將被最有利可圖的產品和市場所吸引。她認爲,包括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在內的非政府組織,正在相關事務上發揮積極作用。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對凱利·李的最後一個提問是“你對全世界隔離在家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她的回答是這樣的:年輕人需要爲未來幾個月的隔離生活建立一些結構。人們感到壓力是因爲他們感到對生活失去控制,那麼就試着保持一些控制——去建立一些“每日例行”,去設立一個目標,去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
“最後,我想說的是,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面對面,那就保持精神上的聯繫。保持距離並不意味着陷入孤立。我們都將以不同的方式記住這次經歷。讓我們利用這段安靜的時間來反思,然後分享我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