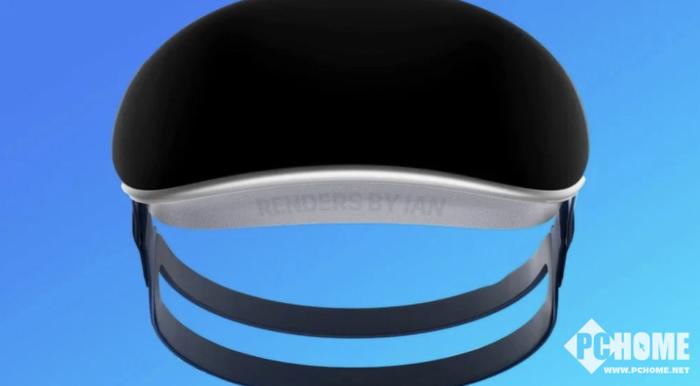帶着滑雪板登上了「薩普神山」| 藏東探祕
Base Camp at Sepu Kangri, reflected in the waters of Sam Tso Taring——Chris Bonington 1999
去年,色浦崗日峯(sepukangri),或者說薩普神山,因爲舒小簡的一篇文章被「首次發現」,巍峨壯美的山峯、冰川漂浮的湖水與荒誕志怪的傳說,使之成爲雪山圈第一網紅。但早在上世紀 90年代,這座隱祕山峯就吸引着一批批優秀的國外攀登者前來。2002 年 10月2日,美國嚮導 Carlos Buhler 和 Mark Newcomb成功首登色浦崗日,此次攀登也登上了美國高山雜誌封面,下文即爲此次攀登報告的中文翻譯版,希望爲潛在的中國探險者提供參考。
打算登色浦崗日源於一個夢想:合適的季節、合適的地點、合適的山峯、合適的團隊。我們是幸運的登山者:那些特別尊崇這座山峯,試圖去攀登的人們會迷失在廣袤的東部青藏高原。念青唐古拉,一個我甚至念不出來名字的山脈,位於喜馬拉雅主峯以北,一個西藏人都極少到達的地方,外國人更是從未涉足。該區域與拉薩隔絕的如此嚴重,在拉薩都無人知道去往念青唐古拉山的路能否通行。在過去的歷史中,可能有不超過 20 個登山者見識過此山的真面目。據我們所知,只有克里斯蒂安·伯寧頓和查理·克拉克 1996、1997 和 1998 年的隊伍曾經嘗試過攀登這座神祕的色浦崗日峯。(譯者注:1992 年西藏登山隊偵察攀登到達 6500 米)
我們選擇了登山的季節:2002 年的秋季——距離伯寧頓上次攀登 4 年後。很顯然這座山峯並不熱門,即使對西藏人也是如此。在無比美麗的撒木措(Sam Tso Taring)湖岸邊只有七戶人家居於此地,該湖位於山峯令人恐懼的北壁下方。七戶家庭和一位修行者,Sam Ten Tsokpu。這位西藏修行者居住於原始冰磧末端的一個高點,遠高於湖面,能看到山下有湖的山谷與令人暈眩的位於西部和北部的尖峯形成的壯麗景色,他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據我們瞭解迄今爲止,他從未下來過,哪怕是下到湖岸。
從色普湖看尚未處女峯的色浦崗日峯頂,6956 米——卡洛斯·布勒
到達拉薩
自 1983 年我第一次達到這個讓人寧靜的宗教城市,它發生了太多的變化。那時我還是一支攀登珠穆朗瑪峯康松東壁 Kangshung face 的美國隊隊員。到了 2002 年,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滿大街穿着西裝的生意人,電話亭裏擁擠着穿傳統藏族服飾的家庭,汽車搖晃着開過那些並不適合車輛行駛的狹窄街道,現代百貨公司裏漂亮的小姐向那些懼怕自己白皙肌膚被高海拔的強烈日光曬黑的內地遊客們兜售着精美的化妝品……面對這些,我不知所措。起初我接受不了這麼劇烈的變化。布達拉宮對拉薩而言就好像迪斯尼對聖地亞哥,或者埃菲爾鐵塔對巴黎:一座現代城市包圍之中的一個吸引遊客的旅遊景點。它是送給西藏人的禮物,造成讓人以爲強大和優美而聞名的藏傳佛教在拉薩依然存在的外部表像。
然而,在這樣一座現代化的城市可以使我們遠征隊組織一支廚師隊伍同我們在阿拉斯加一樣便利。儘管在拉薩的食品市場一些隱蔽的角落裏會有些我不熟悉的蠕動的,黏糊糊的東西,但是一般來說,那裏有大量誘人的五花八門的新鮮食物。在中國政府的管理下,原本的樸實無華已不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到達撒木措湖大本營
9 月 9 號,我們(馬克·紐科姆,遠征隊隊長,來自美國懷俄明州;卡瑞娜·奧斯伯格,馬克的妻子;喬丹·坎貝爾,來自莫阿布,猶他州;艾斯·科費兒和凱特·克萊頓,都來自奧弗,科羅拉多州;我來自博茲曼,蒙大拿州)爬進兩輛現代豐田 SUV 和一輛中國大卡車在路況持續惡化的路面上行駛了三天進入西藏東部的心臟地帶。
這種磨人的,顛簸的,能挫傷骨頭的行駛標誌着我們進入了幾乎消失的西藏文明;我們彷彿坐着時光穿梭機,遠離中國,帶我們穿越過去50年的悲愴,回到過去。我們穿過了荒涼的西部城鎮那曲,比如和 Khinda,然後忍受了 20 公里的只有四驅車能通行的路到達念青唐古拉地區的心臟地帶撒木達(Samda)村,海拔 14000 英尺(4267m)。
色浦崗日在西藏那曲地區比如縣和嘉黎縣之間
7 個小時令人愉快的徒步後,我們到達了 15500 英尺(4724m)的位置, 1997 年和 1998 年克拉克和伯寧頓的隊伍兩次正式登峯時在此建立大本營。我們在四戶人家叫一聲就能聽到的範圍內,這四戶人家是我們從克拉克和伯寧頓所著《西藏的神祕山峯:色浦崗日的勝利》一書中的照片中辨認出來的。
這些居民們起初有些害羞,很快他們變得很熱心和友好。距離他們上次見到西方人已過去了四年(除非他們去拉薩朝聖,否則英國人的隊伍是他們唯一遇到的西方人),現在看起來也沒有太多改變。在我們到達後的幾天裏,他們邀請我們喝茶、喫煎薄餅和美味的新鮮濃稠的加糖酸奶。剛開始時我們對這種由手工劈出的邊緣粘有犛牛毛的木桶盛出的完全沒加工的食物很謹慎,但很快我們就放鬆戒備了,我們建立了一個和他們以貨易貨的系統,可以每天給我們提供含乳酸奶。
向山峯進發
攀登線路示意圖
我們很快見識了雨季過後的天氣是怎樣的潮溼——以及爲什麼冰川那樣大。極少有完整的一天,山峯能不處於雲的籠罩之下。由於接近 10 月中旬,可以預見將會有整個冬季的嚴寒,我一直在不停的數還剩下多少日子,我很清楚一場風暴就能輕易的從我們的登山計劃中奪走一個星期的時間。
C1
9 月 18 日,我們在 17700 英尺(5395m)的山脊上搭起帳篷,很顯然英國人曾在此辛苦的勞動過以建立一個能搭帳篷的營地。我們帶了登山滑雪靴、雪板、止滑帶以及再往上我們會用到的裝備。現在,上面的雪況看上去可以接受。經過 1000 英尺(304m)的雪坡上升,馬克,卡瑞娜和我成功的在位於左側冰川上的冰塔和右側岩石之間形成的一個陡峭拐角處固定了 200 英尺(60m)的繩子。這是個越過冰塔的捷徑,解決了如何到達上部Thong Wuk 冰川的問題。第二天,所有7個人揹着上面掛有雪板的揹包,全部來到這裏。在這裏,我們穿上雪板,用了 40 分鐘抄近道穿過一條令人膽怯的位於冰崖之上的邊坡,直到我們到達 19200 英尺(5852m)高的山脊頂部,從這裏下去 300 英尺(91m)就是山脊和 Thong Wuk 冰川的結合處。
正午之前,令人討厭的暴風雨雲層正從南面包圍我們。我們把裝備埋在雪裏,回到了大本營。接下來的 6 天裏我們等待着這場風暴結束,在和藏民朋友的交流和閱讀書籍中度過許多令人愉快的時光。
Climb Sepu Part 2 of 4
到達High Camp
9 月 29 日,我們中 5 個人回到了 C1 營地。馬克和卡瑞娜,焦急的想要攀登,2 天前就已經爬到更高的位置去了。厚厚的新雪極大的減慢了我們的速度。通過我們的第二次偵察,普遍的共識是從此處出發可以嘗試找到登頂線路。9 月 30 號,我們把更多的食物和裝備搬到山脊頂部我們之前埋裝備的隱蔽處。滑雪降至山脊與上部 Thong Wuk 冰川聯結處,我們在19000英尺(5791m)高的地方一個 40 英尺大小的冰塔下一個隱蔽的雪盆裏紮營,大風吹不到。
下午別人都在搭建帳篷時,馬克和我向上攀登雪坡進入冰瀑區。我們知道從下面往上看來衡量這個障礙物比較困難,我們反覆嘗試這個難點,但總是被冰裂縫給阻斷。下午稍晚一些的時候,我們完成了一次終結之旅,繞着冰瀑區的右側找到一條路上到了 20100 英尺(6126m)。我們得到的回報是上去後第一眼看到色浦的最後斜坡的景色。太美妙了!
薩普的最後難點——極有可能雪崩的坡面以及冰塔形成的大牆映入眼簾。回到帳篷時我對即將到來的攀登持謹慎態度。雖然既疲倦又飢餓,但帳篷裏的士氣高昂。看到的最終路線非常鼓舞人心,儘管最後 2000 英尺(609m)很危險,但我們一致認爲它是可以克服的。
第二天夜裏,卡瑞娜病了,她身體脫水,馬克想陪她撤回大本營,但登頂行動中我們需要他。最終馬克決定陪她下到固繩點,與我們在 21000 英尺(6400m)處會合。上帝保佑我們的雪板!我們很快通過了這片地區,如果沒有雪板,在齊膝深的雪裏行進將非常耗費時間。但是正如薩普的天氣風格,威脅性的雲朵佈滿了西部的天空。曾經 2 個英國人在風暴中返回,懷着這個不受歡迎令人沮喪的念頭,我們祈禱在暴風雪到來前再給我們 24 小時。
到 C3 的路上
下午稍晚時分,馬克與我們會合,我們 6 個人到達了環狀的雪壁前。在陡峭的頂峯覆蓋的冰雪下面,冰川上到處散佈着巨大的雪崩殘留體。儘量靠近環狀陡山壁的右側,我們把兩頂小帳篷紮在 20700 英尺(6309m)的位置。艾斯開始出現高原反應,爬進了睡袋。
Climb Sepu Part 3 of 4
登頂日
清晨 2 點我們點燃了爐子。我感到眩暈無力,昏昏欲睡,因爲整晚我都很焦慮,一直在權衡各種方案的利弊。艾斯感覺稍好點了,但凱特的腳還沒暖和過來,弗蘭克喫不完他的熱巧克力,這是一個不好的徵兆。5 點半之前,馬克、喬丹和我出發,從可能會雪崩的雪坡朝我們右側的山脊前進。在頭燈的照射下,我們攀過有雪崩殘留的雪坡,繞過 2 英尺(0.6m)的頂端裂縫,此時我仍然很焦慮。
在固繩點之上朝着色普崗日攀登雪坡——卡洛斯·布勒
接下來 600 英尺(183m)斜坡比較容易,直到從山脊南面刮來毫無阻攔的狂風肆虐着我們。喬丹因頭頂上的危險神經緊張。如果打保護的話,第三個人就會減慢前進的速度,喬丹很清楚這一點,停止了前進。他在退出之前,把嚴寒中的救命之物——他的Marmot 頭罩借給了我。馬克和我在黑夜中攀爬西壁,一個 55 度暴露感很強的懸冰川,技術難度 3 級。早晨的陽光溫柔的籠抱着位於我們北邊的峯頂。
卡洛斯在攀登中
我們穿冰爪爬上了另一個巨大的陡峭的滑坡面,一條 8 或 10 英尺(2.4-3m)高的頂部斷裂帶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橫穿我們整個的斜坡,我們在斷裂帶下部朝前 35 度橫切,“經驗告訴我們”直到下一次大規模降雪之前它都不會滑落。馬克勇敢地用手掌撐起身體,然後腳踩在同一點站在第一級上,橫切攀登到左面,在這裏他能夠到裂縫的上一級。當雲層吞沒了色普的峯頂的時候,我要求保護。
馬克·紐科姆觀看日出,雲層過來了
九點前當我們到達一個很陡峭的山脊時,一團巨大的風暴雲已經包圍了色普崗日山巒。我再一次感覺到沮喪,1998 年伯寧頓的隊員們被迫在離他們的目標還有 500 英尺(152.4m)的時候返回時,一定也有這種感覺。馬克和我還不準備放棄。我們爬上了另一個陡峭的雪坡,我給馬克作保護,他爬上了 20 英尺(6.1m)高,幾乎垂直的,由風吹形成的一個雪檐,不怎麼結實。很少有人能過這種令人緊張的地區,但是馬克很自信的爬了上去。僅靠馬克的安全帶上吊下來的繩子,我把自己拉了上去。風雪橫掃山峯,能見度降到 60 英尺(18.3m)。但我們已經到達山脊頂部,路線很明顯了。
從湖右邊,到陰影山脊,在面對壁後面,頂峯在左山脊
沿着狹窄的山脊向上走了 150 英尺(45.7m)直到它融進了寬闊的雪域。能見度很低的霧狀天氣讓我們感到害怕。那些很快就會被雪覆蓋的腳印,以及我手腕上松拓表的指南針是我們返回山脊的唯一指引。風夾着雪抽打着我們的臉,使我們感到刺痛,且看不到任何東西。經過 300 英尺(91m)平緩的上升,馬克停下來等我。沒有往上的路了。我們到達峯頂了嗎?我們穩固住自己的身體,看看周圍的情況。看起來這個平臺在我們前面就消失了,但是我們很猶豫要不要在四周探查一下。一些雲朵移動開,露出一小塊空隙。我們看了看周圍所有模糊的下降途徑。當馬克掏出步話機聯繫在 C1 營地的卡瑞娜的時候是早上 10 點。是的,我們正站在峯頂上;不,我們看不見任何東西。
下撤
我們得在夜晚之前下撤,運氣好的話,會一直下撤到1號營地。
竭盡全力找到了幾乎被雪覆蓋的腳印後,我們沿着陡峭的雪壁下降。我們將裝爐子的布袋裝滿雪當作錨點,非常謹慎的用前齒沿固定繩索下降。當我在 55 度暴露斜坡用前齒的方式下降了一段,在霧狀天氣裏快離開一塊垂直冰岩點的時候,繩子到尾端了。我們把繩子抽下來,用一支冰鎬又做了一個錨點,沿繩下降到一個臺階。我們花了四個小時到達 C1營地。當我們到達的時候,另外4個人正準備下降。但我還需要半個小時從風雪中恢復一下再收拾東西。我們滑雪下了3公里,在迷宮似的冰川裏滑行,整個冰川在陽光的照射下象一條桔色的光帶,這一頭看不到那一頭。我們不斷的感謝腳下的雪板。一個小時內我們滑行並繞過了冰瀑區上巨大的冰裂縫,兩小時內我們回到了 C2,在那兒我們曾留了一個帳篷和補給。我們喝了點熱飲,向固繩點的頂端出發。我的腦子只想着“下降”。
傍晚時分,我們到達了 1 號營地牢固的 Marmot 帳篷前。我脫水的身體亟需休息,進入帳篷倒下後,我聽見喬丹往爐子上扔了一鍋雪,喜悅在心頭彌散——今晚可以睡個好覺了。
Climb Sepu Part 4 of 4
廣闊的念青唐古拉山脈朝我們東西兩面延伸數英里,在隱密的羣峯中,我們只造訪了其中一座的峯頂。和未登的色浦崗日一樣,鄰近的那些山峯一樣也使人容易迷失方向等待着人們的探索,但是現在這片山脈的最精華如皇冠上的寶石引誘着我走向它。這片美麗絕倫的地方有着無盡的垂直的線路,我知道我們還會回來。
作者:卡洛斯·布勒 翻譯:醉明月/華仔
- END -
文章授權轉自探索源泉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