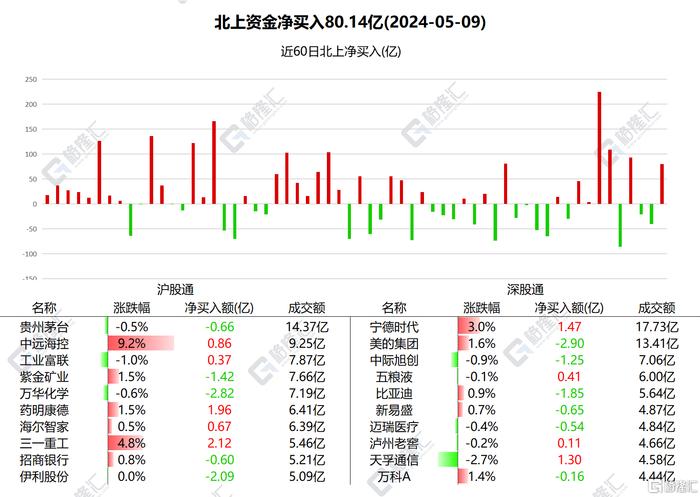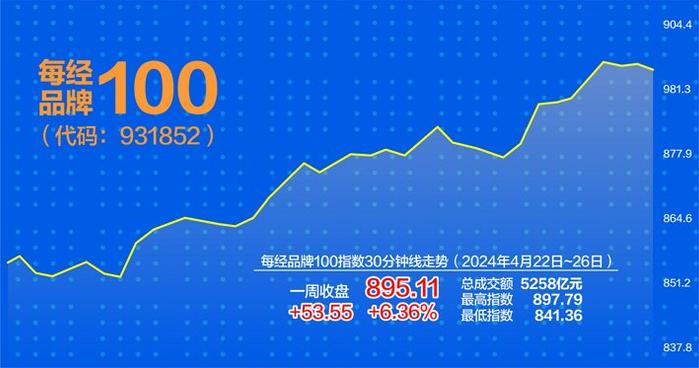餐飲行業集體發難“佣金門”背後:屠龍少年終成惡龍
摘要:“行業都不行了,商家都死了,美團作爲平臺還能賺錢嗎。張文軒說,他們店門從來都是美團和餓麼了雙平臺運營,外賣佣金也一直居高不下。
廣東人務實,敢說敢做,生意人尤其如此。
僅僅4天后,4月14日,廣西烹飪餐飲行業協會也約談了美團外賣廣西區負責人,遞交了廣西餐飲行業致美團外賣交涉函,提出了行業訴求,要求維護行業利益。
這似乎已經不是偶發事件了,從2月開始,陸續已經有四川、重慶、雲南等各地協會紛紛有類似表態和動作。
O2O行業,是中國互聯網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的十幾年時間裏,它改變了中國經濟結構,重塑了中國人的城市生活。長久的搏殺中,美團脫穎而出,無數中小商家與之同行。但如今,站出來用腳投票的,幾乎是同一批人。
這會是另一個“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故事嗎?
漩渦中的商家、用戶與騎手
“打針是死,喫藥也是死,大不了不幹了。”隔着電話,也能聽到陳瑜語氣裏的惱火。
陳瑜是餐飲連鎖品牌“蛙來噠”廣東省中山市利和廣場店的店長兼廚師長,也是此次“佣金起義”的參與者。
這家以牛蛙爲主打的餐廳,開業於2017年12月。生意一直不錯。陳瑜說,過去的兩年時間裏,店裏的生意以堂食爲主,不靠外賣賺錢。不過,早就有美團工作人員上門,雙方簽了約。
“能跟美團合作,我們也很期待,畢竟在廣東,美團是最大的。市場份額佔了65%以上,滿大街都是穿着黃衣服的騎手。”陳瑜說,當時雙方約定佣金的份額是18%。“做餐飲,硬成本要佔去4成,扣除人員、房租、稅務等成本,做外賣根本不賺錢,我們希望美團能給店裏帶來更多影響力,帶來二次消費的回頭客。”
微妙的戰略平衡,持續了兩年。卻因爲疫情被打破。
“比起其他餐飲店,牛蛙店受到的影響更大。”陳瑜說,除了到店客人少,還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談牛蛙色變。整個二月,店裏就是空轉。“一個店有27、8個人,但人工成本,就超過15萬。”
3月份後,情況稍好一些。堂食漸漸恢復,外賣也有了些單子,此刻,外賣的比例佔到店裏一半左右。但這仍不足以抵消成本。
爲了自救,“蛙來噠”與附近的社區電商達成合作,開啓團購;開了直播,提升影響力;還入駐了餓了麼平臺,希望能有更多訂單。
沒想到,包括利和廣場店在內的三家蛙來噠,就很少接到來自美團的訂單了。
“沒下架前,一天有7、80單外賣,能有個8000塊收入,現在,只有500。”陳瑜找美團要個說法,但當地負責人的話就是,“如果要維持現在的佣金水平,就存在排他性。”
“合着我做外賣不賺錢,還要賠錢?”陳瑜一肚子不理解。
若說連鎖品牌依然還能苟延殘喘,更小的創業團隊則正在遭遇滅頂之災。
接到電話時,張文軒剛剛從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出來。
前媒體人張文軒,2019年春天,跟幾個朋友合夥做起了甜品生意,開了一家叫亞信芒椰奶花的門店,其中一個泰餐廚師出身的朋友負責產品,他負責運營。
摻了椰汁的豆花,很符合廣府人的口味,流水、收益都不錯,去年一年,這個創業團隊就開起了5家門店。
就在去年年底的總結會上,幾位年輕人還豪情萬丈,“明年廣州每個區都要開一家。”
不想,突然爆發的疫情,讓門店的生意一蹶不振。
沒有門店,總還有外賣。張文軒說,他們店門從來都是美團和餓麼了雙平臺運營,外賣佣金也一直居高不下。“當然,如果是按照比例來收,25%我也有得賺,但美團是有保底佣金的。一單最少4.5元。”
“賣一杯才十幾元,扣除成本和佣金,我還得賠錢。想要賺錢,客戶至少得點兩杯。”
如今,張文軒的門店也得不到美團的流量支持,他的5家門店一下子成了最大的負擔,“已經賠了100萬,更重要的是,我們團隊內部也有了分歧,這一行還能賺錢嗎?”
在採訪中,幾乎所有的餐飲從業者都在表達自己的悲觀和憂慮。
“正在緩慢的失血”,有人這樣形容行業的狀態,“疫情這樣的情況,大量的商家只能堅持3-5個月,沒有改觀的話,超過30%的餐飲企業要死亡。而且,當用戶的消費能力持續下降,對行業的傷害將無法逆轉。”
這也是廣東省餐飲服務行業協會介入此事的原因,在他們看來,並不能理解美團“竭澤而漁”的行爲。
“行業都不行了,商家都死了,美團作爲平臺還能賺錢嗎?”
不過,商家中也有明白人,“衣食住行都是剛需,前一批小商家死了,總會有新人蔘與進來的。美團已經壟斷了流量,怕什麼。”
在這樣的對立中,受傷害的不僅僅是商家,實際上,一切傷害都會轉嫁到用戶身上。
“買單的永遠都是消費者,這就是點外賣價格越來越高,品質卻越來越差的原因,商家也要賺錢,只能壓縮成本。如果平臺大公司這樣做,會讓行業越來越不健康,而且是個惡性循環。”有餐飲店老闆道出真相。
實際上,疫情以來,用戶對於外賣的品質日漸不滿意,而騎手就好過嗎?
“騎手也賺不到什麼錢,一個月能到1萬塊的都是少數中的少數,反倒是衆包公司的老闆們最近賺翻了。”一位騎手說。
鐵三角的建立與崩塌
縱觀中國互聯網商業的發展史,幾大領域一直是時代主角,完善了商業模式,改變了生活方式,甚至影響了歷史進程。比如電商、比如社交,也包括O2O。
O2O,是Online To Offline的縮寫,即“線上到線下”,是指將線下的商務機會與互聯網結合,讓互聯網成爲線下交易的平臺,這個概念最早來源於美國,但真正發揚光大,是在中國。
過去十年時間裏,O2O行業在中國飛速發展,美團既是其中翹楚,也是行業的代表。
從千團大戰,到收購競爭對手大衆點評,再到與餓了麼的數次交鋒。愈戰愈勇的美團,因爲外賣業務的蓬勃發展,迅速從團購網站迅速成長爲一個綜合性的生活服務平臺,而自2017年起,美團就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餐飲外賣服務商,“拔劍四顧心茫然”,想必就是美團站上行業巔峯時的心態寫照。
在這段成長的過程中,美團,或者說O2O行業,都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打法,先通過補貼形成流量優勢,再憑藉流量優勢去吸引商家加入,不斷滾雪球,不斷擴大規模,不斷獲得資本青睞。
當然,資本不會持續燒錢,美團佔據絕對優勢之日,就是開始謀求盈利之時,提升佣金,降低補貼,是一條必然之路。
2019年,美團終於實現了從概念到盈利的質變,成功扭虧爲盈,財報中,美團全年實現營收975.29億元,同比增長49.5%;毛利爲323.2億元,同比增長114.0%;經調整淨利46.57億元,佔收入比重爲4.8%。
其中最大頭,就是“佣金”——這也是O2O行業的主要盈利方式。
不過,也是在這一年,因爲佣金,商家與美團的矛盾集聚增多,廣東省餐飲協會之前,已經有多個省份的餐協向美團開炮。與此同時,用戶也在日漸高企的外賣價格和漸漸降低的品質中趕到厭煩。
一個花費10年構築的“鐵三角”,平臺、商家、用戶之間的平衡漸漸被打破。
加速“鐵三角”崩塌的,是2020年的疫情。
疫情阻隔流通,餐飲行業首當其衝,盈利下降導致的實際損失、信心喪失,讓餐飲行業身處寒冬,但是,當他們向相互依存的美團求助時,卻遭遇謀求盈利的平臺的當頭一棒。
這並非單一的行業事件,它將被記錄在互聯網商業史的歷史進程中。對於很多行業和平臺來說,發生於上半場的行業洗牌已經完成,下一步,是予取予求。
現在再想王興關於“互聯網下半場”的論斷時,竟像是另有所指。
行業的未來,不在於佣金,而在於不斷升級
“如果佣金能壓在15%左右,平臺、商家、用戶,都能健康的發展。”接受採訪時,一位資深的餐飲從業者說,他很感激美團,正是美團的幫助下,中小型餐飲從業者,有了擴大輻射半徑,打破行業天花板的機會,也有了與大商家同臺競技的勇氣。“平臺要養騎手,要運營,還有其他成本,這些我們都能理解。”
實際上,在廣東省餐協向美團發難後,美團也做出了回應,“佣金將幫助更多商家存活。”
美團最大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佣金,而在於“只有佣金”。或者說,多年來,進步不大。
一直以來,美團都是靠餐飲外賣這一條腿走路。從歷年財報來看,美團的外賣營收佔總營收的比例從2016年的41%,上漲至現在的56%,最高的是時候在2017年,曾經達到62%。而餐飲外賣的主要收入,就是“抽傭”。
從全年來看,美團2019年全年的佣金收入達到655億,而在2018年則爲470億元,同比上漲39.4%。此前一年,美團的佣金收入漲幅爲67.8%。
相較於傳統企業,互聯網企業的優勢是技術,也是從不停止的奔跑。問題是,當美團成爲阿里巴巴和騰訊之外最大的互聯網經濟體時,盈利模式卻依然沒有突破。
如今看來,如果美團能找到一個完美的佣金標準當然這並不容易,想必能度過這次危機,但長久看來,美團或者說整個O2O行業來說,最主要的是脫離舒適區,重新找到奔跑的方向和動力,比如行業的數字化升級,比如生態的構建。
這樣的處境,當年3Q大戰時的騰訊也遇到過,當時的騰訊果斷反思自己,進而從一家大公司,迭代成一家偉大的公司。
王興當年曾經設想過美團“一橫一豎”的未來,打通本地生活上下游,構建生態,遺憾的是,美團的轉身速度太慢了。
疫情改變了很多,讓許多人看清現實——多年洗牌之後,互聯網巨頭已經實際存在,巨頭的存在遠不如競爭更有利於行業發展。
“在廣州,竟然找不到一個能跟美團競爭的平臺,要知道,這個市場是一個慢慢積累的過程,平臺可以慢慢競爭,但餐飲企業是熬不過這段時間的,估計很多商家最後只能妥協。”廣東的一位商家充滿悲觀。
儘管美團不願意承認,但這次事件爆發在廣州,已經能說明很多問題:廣東餐協表示,美團外賣在廣東餐飲外賣的市場份額高達60-90%。
互聯網的本質,是一場去中心化的活力革命,但在成長的過程中,有些平臺自己就成了中心,成了曾經想要打到的寡頭。而流量作爲用戶共同締造的資產,如今也已經成爲壁壘高築的私家資源。
“不斷進化,不斷適應,不斷超越自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互聯網從業者,還記得自己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