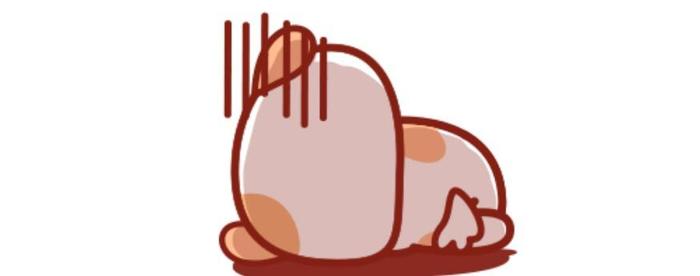曾進|意象·丹青福盈來系列書畫展——中國畫聯展(二)
首圖作品《溪山問道》局部
作者 曾進
距離開幕式還有
1 7 天
福盈來文化
意象丹青
曾進藝術簡歷
曾進,著名山水畫家,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湖南美術家協會理事;湖南省直書畫家協會副主席;湖南中國畫學會副會長; 湖南畫院特聘畫家;長沙畫院副院長;湖南省美協水墨藝術委員會副主任。
集罷歸來擔簍足,斜陽蹊樹照眼明
意象·丹青
曾家圖式新氣象
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
李蒲星
繪畫是藝術,以個性及風格爲本。個性既是一個多樣統一的整體,又有其核心突顯的方面。以現代山水畫而論,耳熟能詳的是“賓虹墨”“抱石皴”“可染黑”等等,說的都是幾代大師的個性核心所在。“曾家圖”也是指個性中最突顯的核心。要說清何謂“曾家圖”,先要從山水畫的本源說起。
中國的山水畫,按照現代美學的認識論,乃主客合一,主中有客,客中有主的文化形態。主指的不僅是藝術家個人,還指作爲羣體的文人畫家。山水畫的主觀性,首先指的中國文人集體所崇尚、信奉、追求的審美理想和人格精神,其次纔是個體的藝術家,客則指的是自然萬物及人文景觀。主中有客是一種美學理想,也是一種審美要求,同樣,客中有主也是一種美學理想和審美要求,不能是照相攝影形式的寫實主義。
中國山水畫千餘年的持續發展和獨尊畫壇固然得益於文明古國文人勢力的強大及巨大影響力,同樣也得力於中國特殊的地理條件和東西南北中自然萬物的無限多樣性。
雲繞千山合 牛蹊帶小橋
任何事物都是在時間中展開進而形成歷史。山水畫之初,崇尚自然,形成了客顯主陷的繪畫格局。南宋以降,科舉制度日趨完善,獨立的文人精神人格日益彰顯,於是山水畫爲之一變,主顯客陷到明漸派吳派清四王時代。山水畫家不再以行萬里路爲必須,畫中的自然幾成僵化模式。明清數百年一味摹古走極端,破壞了平衡的陰陽之道。於是以石濤爲代表的在野勢力振臂高呼搜盡奇峯打草稿,到現代傅抱石等人更是重舉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大旗,與現實主義的新文化新美術運動遙相呼應。於是,山水畫又爲之一變。而山水畫的“曾家圖”就是形成於這樣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時勢所造,與時俱進的產物。
曾家圖的創始人是曾曉滸。曾曉滸四川人,50年代就學於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受業於嶺南大師黎雄才、關山月諸人,畢業後定居湖南長沙,近半個世紀常年往來於湘川之間。受時代風尚驅動,更有嶺南宗旨訓示,深入生活,深入自然,腳行萬里,寫生不斷。
山水畫千餘年,董其昌簡之爲南北宗,而畫史之南宗,卻以江浙一帶爲代表,湘川腹地少有人傑。雖同爲江南,地理學上曲折的丘陵地茂。自然之勝,不在一山一水之奇絕,而在山山水水之間相互結構的千變萬化與幽深曲直。此種自然,外地少有,此種地貌,畫史鮮見。無論是古代畫家筆下的瀟湘景物,還是現代畫家偶到湖南的寫生創作,都未能盡識湖湘山水的真實面目。
居住在湖南幾十年,從未間斷的寫生查探,日積月累,自然是胸有丘壑。只是這個丘壑之獨特爲湖湘山水,這個山水之勝在它的山與山、水與水的結構之中。於是,就形成了以山水結構爲核心突顯的現代山水“曾家圖“。
染盡青樹做黃金
北派的高遠,東南的平遠,均極一時之盛,後來融合南北,但只是在南北畫跡中各取一端,揉爲一爐。固然不可,但並非自然山川的真實感悟感受,在真實的自然世界,其實又是另一番景象。
面對真情實景的湖湘山水巴蜀山水,三遠的概念黯然失色,無所作爲。要麼是以固有的模式去看真實的自然,得出似是而非的結果,要麼是直筆所見所聞所感所悟,走一條山水圖式的創新之路。曾曉滸選擇了後者,這即是個人的選擇,也是時代的要求。
這是一條不歸路,佈滿荊棘,意志力、創造力和定力,一樣都不能少。
誰家茅屋在雲間
藉助於新時代新美學觀念的力量,想擺脫模式山水畫,直面真實的自然景物,卻又有淪爲西畫寫生的危險,有悖中國山水畫的文化規定。於是就像石魯所言,一手伸向生活之外,還要一手伸向傳統。對於中國的文人畫家而言,最重要的傳統繪畫語言,自有與衆不同的體悟認知。對於曾曉滸而言,最重要的傳統繪畫語言是山水畫的結構或是“勢”,因爲只有通過對傳統山水畫結構美學的把握,才能避免淪爲“西畫風景”的局面,但古代山水畫跡和近現代大家的創作中所示的結構,都難以直接運用於湖湘巴蜀山水的描繪,惟一之途就是通過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創造出一種中國山水畫史沒有卻又符合中國美學規律的山水結構圖式。這是一個不斷學習傳統文化不斷思索感悟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在畫面上實驗探索的過程。吹盡黃始見金,曾先生終其一生終於形成了人們所熟知的山水畫“曾家圖”獨特的畫面結構,這是曾曉滸山水畫最突顯的個性。四年科班薰陶,嶺南的美學理念,色彩成爲山水中不可少的藝術語言。然而,在對傳統的研究揣摩中,對筆墨獨特形式意味日見鍾情,於是在畫面中,嶺南大師們崇高的寫生筆墨爲傳統的文人形式趣味的筆墨所取代。曾曉滸是四川人,雖然定居長沙,常年遊走在川湘之間,巴蜀文化的飄逸之氣爲湖南本土畫家所沒有,於是,他的畫中,結構複雜卻不沉重,筆墨色彩千變萬化。
楓林愛晚圖
曾進是曾曉滸之子,大學時學的卻是西畫,畢業之後從事教學,教的也是西式的素描色彩。教學之餘隨父學畫三十餘年,卻已窺其堂奧,幾可亂真。由此可見家學淵源事半功倍之效。
說到中國畫的家學淵源,也是代不乏人,唐朝的李思訓、李昭道叔侄,宋朝的米蒂、米友仁父子,都是史澤流芳的典範。現代畫史上更多,李可染李小可,李苦禪李燕,傅抱石傳益瑤。曾曉滸曾進只是其中之一,但顯現出來的文化傳承關係,卻是一致的。
雨過春歸綠意濃
和父親一樣,曾進的山水畫均以自然爲粉本,不僅遍畫瀟湘勝景,視野所及也包括北方的山山水水。但無論何處自然,描畫於紙素之上,就是別一樣的曾家圖式,其最明顯的特徵是構圖飽滿,大多不留天際。總有山石衝出畫外,不求自然的表面完整,如《匡廬千重翠》、《大圍山景》、《青崖絕谷》等,山峯都走出畫外。有的畫如《幽谷嗚溪》更是如近景撲面,不見山峯輪廓。峯無主次之分,重重疊疊,起承轉折,環環相扣,令人想起劉國松的畫若下棋的理論。一子落下,因勢利導,雖似漫無章法,實則步步相生,形成統一的圖式和複雜的結構。因爲沒有事先的預構,所以能隨機應變,千變萬化,從不流於模式化的複製和變相複製。遍覽現代山水畫壇,在藝術觀念和創作實踐頗與曾家山水圖式類似的是陸儼少的山水畫及其理論,不同之處在於陸儼少山水圖式趨平面化,在平面圖式中顯示結構的無窮變化。而曾家山水圖式是立體狀,在立體圖式中顯出結構的豐富多樣。這自然是湖湘巴蜀自然山水的贈予。此種山水之間,多有鄉民憩居,山與山之間,多有山道相連。於是,在曾進的山水中,總有顯現縱深的山道和行走在山道上的人與牛羊。鬼斧神工的大自然與人物結合得如此生動有趣,實屬罕見。
近水樓臺先得月,識得乃父精髓,承中國畫之優良傳統,熔中西技法於一爐,曾進的山水流露出屬於他自己的氣質,他可以隨時利用所掌握的西畫寫實造像的理念去觀察對象,又能迅速自然潛心到中國傳統山水大寫意藝術中去探索追求,可以說西畫的基礎增加了他創作魄力與膽量,讓傳統繪畫更具生命力。在《溪山問道》一畫中就可窺見到一股雄強之氣,剛毅之氣。“青壁下寒泉,陽崖隱深觀。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湘西山水宏闊、神祕、幽深,此畫構圖取一般人不敢嘗試的頭重腳輕之手法,劈面邪壓的主峯以出穴形式呈現;遠山折落有致,樹有傾斜與扭轉,溪山深虛,水若有聲;層層遞進的道觀在墨色中虛虛實實神祕莫測,屋脊、飛檐、斗拱、廊柱、石階用筆質樸厚重、準確生動,既有西畫的透視又不失中國畫的筆墨寫實;點景人物與拱橋飛瀑相得益彰。該畫整體手法上以小畫方式處理大畫,在氣象萬千中求得剛骨、大氣磅礴之勢。以物寫景,不以景限我。滲透古法,在古法中獨闢蹊徑。
溪山問道
作爲一箇中國畫家,特別是山水畫家,家學淵源雖是重要緣由。但曾進的人品與藝品也是成就他的因素之一。他謙卑,低調,從不張揚的性格,與父親如出一撤。他的畫,有中華民族藝術渾然一體的充盈與豐沛,更有積極的心態。他是單純的藝術家,對鋪天蓋地的炒作不以爲然,應了他那句:少一份世俗,就會多一份天真。其實畫家的天真,正能體現作品的純粹。
迴歸到主題,千百年來中國山水畫偏重筆墨皴法,究其原因,是圖式的單一。實際上,以繪畫語言而論,整體的圖式語言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具體的筆墨皴法語言。當代山水畫的創新固然是各求其勝,但圖式語言卻是最有寬度的一條傳承大道,得湖湘巴蜀自然之功,曾曉滸大刀闊斧創新於前,曾進必定是站在巨人肩上繼續披荊斬棘、繼承與創新的那個人。 曾進作品欣賞
集罷歸來擔簍足,斜陽蹊樹照眼明
雪峯山寫生
溪山清茗
林壑有佳色,白雲映清秋
雨過春歸綠意濃
石徑盤盤入晴霞
飛流幽壑鳴
走馬瀑布
永順小溪寫生
楓林愛晚圖
雨晴山色慾入秋
青壁下寒泉 往期
精彩回顧
王羲之、米芾、趙孟頫“書”《靜夜思》,誰更勝一籌?
真功夫!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名狀元……
從垃圾堆裏撿回的國寶!
品味生活,閱讀人生,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長按識別圖中二維碼,
帶你領略浩瀚的文藝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