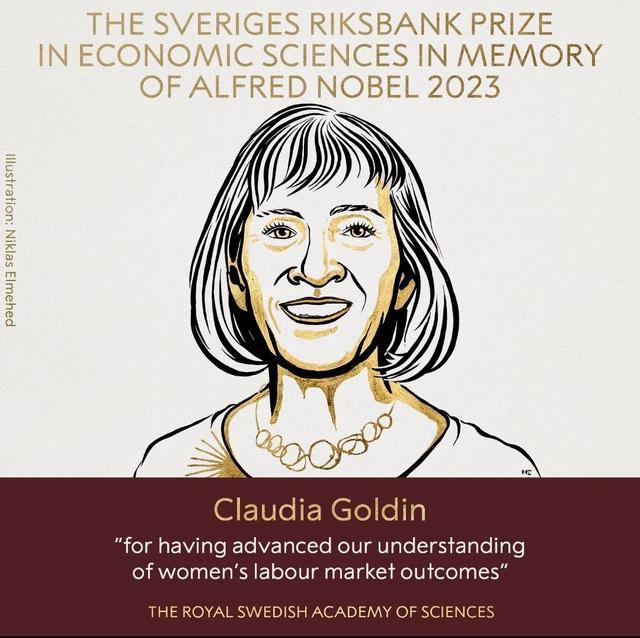從哈佛大學歧視亞裔學生案,看美國精英教育潛規則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大家(ID:ipress),作者:吳晨(《經濟人·商論》執行總編輯,曾任職新華社等)。
哈佛大學最近攤上了一場大官司。
哈佛成爲被告的原因,是有非營利機構提出,亞裔美國人在哈佛大學錄取過程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原告認爲,哈佛大學在推進“多元化”的美名之下,對非洲和拉美裔學生予以照顧,其實是建立在犧牲亞裔美國人錄取機會的基礎之上。
在中國,大學的高考常常被用帝制時代的科舉來比喻,一方面一卷定終生,與科舉考試選材是同樣的機制;另一方面只有極少數人才能進入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能入名校的考生在各地都可能是當地考試名列前茅的學生,也被等同稱之爲狀元。而在大洋彼岸,哈佛耶魯這樣的常春藤名校,申請競爭也十分激烈。哈佛每年只有不到5%的申請者能夠錄取,淘汰率之高,也堪比中國的科舉。
哈佛大學在錄取流程中採取一種稱爲“全面評估”的錄取流程,這種評估過程不僅僅考慮學生的學習成績,還要同時考慮課外活動、種族和很主觀的“個性評分”。 此外,哈佛大學也很強調“祖蔭”,也就是會優先錄取校友的子弟。根據一份哈佛自己的內部報告,校友子弟的錄取規模跟黑人申請者差不多,這意味着校友子弟的錄取率爲34%,比普通申請者要高出好多倍。舉個例子,美國前總統小布什雖然平時是C等生,但仍然被哈佛商學院錄取,靠的就是爺爺和爸爸的祖蔭。
不過,這次把哈佛大學推上風口浪尖的案子,關注點並不是“祖蔭”對錄取機制的扭曲,槍口對着的是實施了五十多年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亞裔人士抗議哈佛大學
什麼是平權行動?簡言之,就是在給弱勢羣體和少數族裔在就學和就業上更多機會,因爲在歷史上這些人曾經遭受過苦難的生活,而在現實中,他們也可能因爲家境的困難輸在起跑線上。而平權行動主要的受益者是黑人,這多少也反映了六十年代美國的政治現實——平權行動是肯尼迪和約翰遜這兩任總統推動黑人享有平等公民權利改革的重心,其中也含有對兩百多年奴隸制度和歧視黑人的補償。
2014年,由反對平權行動的保守派人士愛德華·布魯姆(Edward Blum)創立的非營利機構“公平招生”(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把哈佛大學告上法庭,指控哈佛歧視亞裔美國學生。這場官司最近在哈佛大學所在的馬薩諸塞州開庭審判,庭審披露了大量資料,爲外界揭開了哈佛錄取流程的一角。
布魯姆認爲這種平權行動可能固化爲給不同族裔配給一定的配額(美國最高法案已經有過裁決,認爲按照種族給錄取新生設置配額的做法違憲),而這種變相的配額制讓人數不斷增加而平均成績更是名列前茅的亞裔子弟在哈佛這樣的名校錄取中遭受了歧視。
按哈佛招生辦自己的評定,亞裔美國學生的學業能力和課外活動質量都高於白人申請者,但他們的錄取率卻相對低出許多。比如說,學業能力處於前10%的亞裔學生中只有13.4%被錄取,相反,白人的錄取率則是18.5%。
布魯姆認爲,亞裔在“個性評分”這項很主觀的衡量標準平均得分都低得多。和學業成績或者課外活動不同,“個性評分”純屬主觀意見,而且是在招生人員還沒見過申請者本人的情況下評斷的。
同樣根據哈佛大學2013年的一份內部報告,如果僅僅考慮學業成績一項,亞裔美國人在當年大學新生錄取的佔比會達到43%,超過白人成爲哈佛大學新生的第一大族裔,而黑人的錄取比例則會低於1%。如果考慮體育特長生和“祖蔭”,亞裔可能被錄取的比例下降到31.4%。如果再考慮課外活動和“個性評分”這兩項指標,亞裔的比例下降到26%。而亞裔當年實際的錄取比例只有18.7%,黑人爲10.5%,因爲錄取流程中還考慮了種族、性別和其他一些因素。
布魯姆又聘請了杜克大學的經濟學家彼得·阿西迪亞科諾(Peter Arcidiacono)建立統計模型,分析種族因素對錄取結果的影響。據阿西迪亞科諾的估算,一名達到錄取標準的亞裔美籍男性非貧困生有25%的幾率被錄取,假如換成白人,錄取機會就增加到了36%,如果換成是西班牙裔,機會翻番到77%,如果換成黑人則上升至95%,幾乎篤定錄取。
哈佛錄取案暴露出的問題
“公平錄取”的布魯姆訴哈佛大學案,凸顯了幾個問題。
首先是哈佛大學的錄取流程到底是否公平?在這個時代應該怎樣詮釋錄取的公平?其次是,平權行爲是否已經失去了它本來的進步意義而淪爲保護特定種族而歧視另一類種族的不公平?可以說,這場訴訟揭示出的問題,比希望解決的問題更多。
先看哈佛錄取流程中的公平問題。
哈佛新校長勞倫斯·巴科(Lawrence S. Bacow)認爲哈佛的“全面評估”流程標榜了哈佛錄取學生的多元性。他認爲,將來自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族裔,不同地區的人,熔於一爐,會給班級乃至學校帶來巨大的收穫,因爲學生們不僅能從學校汲取知識,也能從不同成長背景的同學身上相互汲取養分。
但是如果把平權行動等同於多元化是一種顯然的偷換概念,因爲多元化與平權行動所倡導的保護弱勢羣體和族裔遵循完全不同的邏輯。而且,遵循多元化的邏輯在實操階段也很可能被固化成爲某種配額制度,因爲哈佛可能爲了確保種族的多元化而變相規定各種族裔在每一年錄取新生中的比例。
如果看一下歷史數據,就不難發現,雖然過去十年全美亞裔高中生的數量不斷增加,但是哈佛錄取的亞裔美國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相比之下,因爲上世紀九十年代加州通過了不必遵循“平權行動”的法案,加州的一些大學亞裔錄取比例大幅增加。
這種現象並不是哈佛所獨有。最近美國就有一個案例,申請人是黑白混血,之前申請了一所常春藤名校沒有被錄取,之後父母決定修改一下申請人的姓名,讓名字變得更像黑人名字,在族裔一欄也申報爲黑人,之後申請人提交了同樣的申請材料,結果卻被好幾家常春藤大學錄取。
這一案例的家長就認爲,自己的確花了很多心思在孩子的教育身上,對孩子最終能被名校錄取感到欣慰,但是他們質疑錄取流程中過度看重“族裔”是不是正在創造新的不公平?
當然,如果從一個動態的角度去看名校的錄取過程,這種可能存在的錄取配額潛規則,會給輔導班和諮詢顧問很多賺錢的機會。如果有——哪怕是不成文的——規矩,去確保不同族裔在錄取新生中都有一定的佔比,就可能出現和中國一樣的高考移民。這恐怕是美國式精英教育面臨最大的問題。
那平權行動是不是已經失去它的歷史意義了呢?也有持完全不同想法的人。一些亞裔活動家就擔心布魯姆只是借用亞裔在名校的錄取過程中可能遭受歧視這個案子做文章,目的是爲了在美國全社會取消平權行動,而這麼做對於亞裔是受損的。
一位比較活躍的亞裔人士就表示,如果你告訴亞裔美國人平權行動會給亞裔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會鼓勵政府僱傭更多亞裔法官或者大學僱傭更多亞裔教授,大多數亞裔都會選擇支持平權行動。相反,哈佛的案例並不具備平權行動導致亞裔整體遭到歧視的代表性。畢竟,哈佛有着95%的錄取失敗率,申請哈佛的競爭非常激烈,即使一些亞裔覺得自己成績優秀課外活動是佼佼者,那種篤定要進哈佛的勁頭,背後也有一種應得的權利(entitlement),這種盲目自大,並非好事。
這種觀點把對哈佛訴訟提出問題的討論變得更爲廣闊。問題變成了亞裔到底是不是平權行動的受益者?
名校只是人羣的一角,亞裔的孩子努力、用功、數學好、英語差、不融合、是中產階級的標準生、應試機器,這些評語到底有多少代表性?還是這種印象其實是思維定勢和刻板印象?甚至亞裔申請者在申請過程的“個性評分”項被打低分,多少是這種思維定勢的結果,也值得深究。
如果看一下統計數據,在舊金山就讀社區大學(大專)的亞裔學生比在所有藤校上學的亞裔還要多。象牙塔尖頂的博弈,會影響到底層的太多人。因爲已經有研究發現,如果在美國全社會廢止平權行動,最終受益的會是白人。
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亞裔,尤其是最近三十年來自中國大陸的美國新移民,大多數都是“優等生”,技術移民,也確保了下一代至少在教育的投入和教育的傳統上,都或多或少保留了亞裔虎爸虎媽的“優良傳統”。
不過,這樣一來,關於亞裔的思維定勢還會進一步被扭曲。在不在實施平權行爲的加州,隨着亞裔錄取比例逐年上升,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已經被戲稱爲在“亞洲移民中迷失的白人大學”,而UCI(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被稱之爲中國移民大學(University of Chinese Immigrants),都是新鮮的例子。
科舉與潛規則
哈佛的這個案子,讓我聯想起了中國的科舉。
同治二年,常熟翁家繼七年前翁同龢中狀元之後再次科榜奪魁,這次狀元是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叔侄兩人先後登上中國科舉金子塔的頂端,史上罕見。殿試之後,翁同龢日記中就寫道:“今邀先人餘蔭,得與廷試,從容揮灑而出,意若其有天佑乎!”等得到奪魁消息,這位後來的兩朝帝師更是“悲喜交集,涕淚滿衣。”
不過,翁曾源這個狀元的確是祖蔭得來的。
一年前,翁曾源的爺爺翁心存病死,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義特賜翁曾源舉人,而且免會試,直接參加殿試,所以翁曾源在科場上的兩個功名——舉人和貢士,都源自慈禧的賞賜,不是自己考的。直接參加殿試,也就是讓他接連跳過舉人的鄉試(各省舉辦的舉人資格考試)和貢士的會試(在京城禮部進行的考試),進入進士的排名考試。
殿試中除了極少數人之外,都能拿到進士的功名,因此殿試更多是走過場,主要看試卷的書法是否漂亮,評判的標準是所謂的“黑大光圓”。翁曾源書香世家,祖父叔兩代進士,書法更是頗有造詣,正常發揮,奪取殿試第一名的狀元並不意外。
不過翁曾源其實有隱疾,患有嚴重的羊角風,經常一天發作幾次,碰巧殿試那天精神抖擻,發揮正常。所以,翁曾源雖然一時風光,但是翁家的這個“小狀元”,並沒有像叔叔那樣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任何印記,只當了半年的翰林就辭官回鄉,二十年後病死;而他同科的探花(第三名)是張之洞,後來成爲了晚清的中流砥柱,是中國歷史上大書特書的人物。
一個患有嚴重疾病的人依靠祖蔭竟然能夠走到以精英選拔機制著稱的科舉的金字塔頂,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科舉的不幸,也是科舉作爲一種公平的選拔機制的淪陷。
科舉作爲精英選拔的體制,是否藏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貓膩?一直是帝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科舉既然承擔爲國家選拔人才,就必然要面對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科舉應該只是精英選拔,還是需要加入地區的均衡和全國代表性的考慮?
中國歷史上其實很早以前就有過類似的討論,探討選才的過程到底是要公平還是要更爲充分代表性。科舉之所以在明朝就開始分南榜和北榜(還有中榜),就是因爲科舉不僅僅是單純的精英選拔機制,還是一種讓來自龐大帝國各個地方的舉子能夠在科考的路上把帝國各地的信息帶到首都,也把首都的繁盛輻射到全國各地的一種上下溝通融合的過程。明朝規定的“南榜”“北榜”“中榜(安徽及西南諸省)”,分別佔每次進士錄取總額的55%、35%和10%,政府還明文規定各地的錄取名額,各州縣均有一定的配額,即使面積最小、人口最少的縣,也會有人才被錄取。
雖然在明代,中國經濟的重心已經移向江南。江南的經濟繁華也意味着江南有更多耕讀世家,江南的士子在科舉中就更可能中第,而中第的士子又更可能在中央形成自己地緣形成的小圈子,比如翁同龢翁曾源叔侄狀元所在的常熟縣,僅明清兩代就有366名進士。這個時候,用制度上保證接近一半比例的進士取自北方,對於南方的舉子而言的確是不公平,卻強化了統合帝國的紐帶。
從這一視角來看哈佛訴訟所折射出的美國精英教育的困局,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統合”因素主導着一種“潛規則”?只是在平權行動的“政治正確”下,這種統合是不能拿上臺面來討論個黑白分明的。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大家(ID:ipress),作者:吳晨(《經濟人·商論》執行總編輯,曾任職新華社等)。
*文章爲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網立場本文由 騰訊《大家》© 授權 虎嗅網 發表,並經虎嗅網編輯。轉載此文請於文首標明作者姓名,保持文章完整性(包括虎嗅注及其餘作者身份信息),並請附上出處(虎嗅網)及本頁鏈接。原文鏈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70961.html 未按照規範轉載者,虎嗅保留追究相應責任的權利
未來面前,你我還都是孩子,還不去下載 虎嗅App 猛嗅創新!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