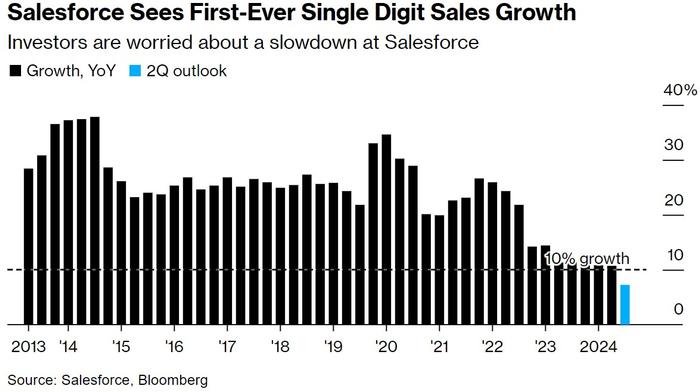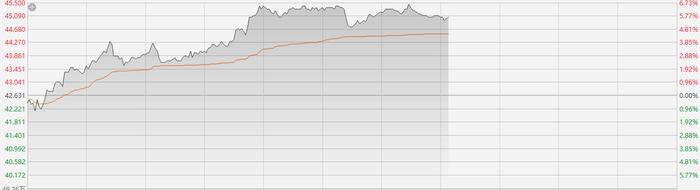反壟斷究竟是在反對什麼⑤:Google 再次因爲信息控制面對國會質詢,這些年它都被羅列了哪些罪狀?
摘要:但真正讓 Google 在有能力決定科技公司業務邊界甚至於去拆分一個公司的美國撞上反壟斷麻煩的,還是在於言論控制。Google 和 Facebook 在老家面對的大問題不是限制商業競爭、打壓小公司,而是它們對於言論和信息傳播的巨大影響力。
美國互聯網巨頭的高管們又將來到美國國會,接受新一輪拷問。
4 月 10 日,Google 和 Facebook 的發言人將接受美國衆議院司法委的聽證會質詢,解釋爲什麼新西蘭白人至上支持者殺人視頻通過它們的平臺得到如此廣泛的傳播。一天後,他們又要接受美國參議院的質詢,主題明確——“扼殺言論自由:技術審查和公共話語權。”
兩個主題充分說明,在反壟斷討論的大背景下,科技公司因爲控制信息流動所陷入的兩難境地。
在民主黨主導的美國衆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傑羅德·納德勒(Jerrold Nadler)指責科技巨頭放縱仇恨言論的傳播,稱“科技公司顯然已經成爲仇恨言論的導管”。美國民權律師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汀·克拉克(Kristen Clarke)向國會提交報告,認爲社交網絡仍然是許多暴力白人至上主義者組織和招募新成員的關鍵場所。
另一方面它們在參議院被指責爲過度審查言論、扼殺言論自由。主持參議院聽證會的共和黨黨魁特德·克魯茲(Ted Cruz)表示,“新的聽證會試圖討論科技公司普遍存在的言論偏見和內容審查,這是很多美國人心中的恐懼”。一年前,克魯茲指出過相同的問題,警告說“科技公司不能左右第一修正案賦予的言論自由”。
和歐盟給科技公司開出的一張張反壟斷罰單不同。Google 和 Facebook 在老家面對的大問題不是限制商業競爭、打壓小公司,而是它們對於言論和信息傳播的巨大影響力。
Facebook 的壞消息一直沒有停過,人們早就習以爲常。Google 的境遇則在過去一年多里有了巨大變化。自 2018 年 8 月首次質詢開始,Google 已經四次被要求去美國國會接受質詢。距離 Google CEO 皮蔡(Pichai)去年年底親自作證還不到 4 個月,新一輪更嚴重的討論再次開始。
外部批評不斷,Google 內部也出現風波。本意解決人工智能道德問題的倫理委員會只存活了一週,在大量員工對爭議成員的聲討中草草宣佈解散。而員工大規模抗議導致關停項目,過去半年在 Google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很少有公司能比 Google 更能反映過去 20 年裏科技公司的發展和爭議。
Google 誕生於一個模版樣的美國硅谷夢。6 年時間從車庫走到納斯達克,兩位年輕的創始人帶着不作惡信條上市的那一年,扎克伯格才只有 20 歲。整整一代科技公司從辦公室文化、到股權機制再到 OKR 考評都以它爲榜樣。
關於 Google 壟斷信息控制的擔憂很早就有過。2005 年, Google 和圖書出版商和解協議被紐約州地方法院叫停。主審法官丹尼·秦(Denny Chin)認爲 Google 控制在線書籍信息的能力將鞏固其在線搜索市場的壟斷地位。
歐盟反壟斷專員瑪格瑞特·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在 2014 年當時剛剛上任時說:“Google 控制的數據量會引發一系列社會挑戰,遠非經濟問題。”但當時執政者更關心的還是經濟問題,維斯塔格幫助促成了三張總計 82 億歐元的罰單。
現在,美國國會對 Google 更嚴肅更頻繁的指控來自對言論控制的擔憂,而非市場競爭。
2018 年 12 月,Google CEO 皮蔡(Sundar Pichai)首次站在國會山出席聽證會。衆議院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拋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的科技公司是自由的工具,還是控制的工具?”
短短 15 年時間,對 Google 的擔憂從搜索引擎競爭,一路升級到思想控制。這是整個社會和科技公司變化的一個體現。
2005 年,最流行的手機還是諾基亞,離 iPhone 發佈還有 2 年。互聯網基本等於點亮電腦屏幕才能存在的東西。人們奔着獲取信息的目的,來到這個只有 2 億多所謂網民的新生地帶。
2019 年,iPhone 和 Android 已經普及且完善到手機廠商都不知道怎麼才能勸人購買更多的手機。大半個地球超過 40 億人類通過手機實時在線上,每天花五小時已經不足爲奇。
科技公司的產品影響力也隨着增大。Google 搜索決定了 20 億人能看什麼。Android 用戶規模也超過 20 億。Facebook 用戶規模爲 23 億人,而單這一個應用的平均用戶使用時長就超過 60 分鐘。全球各地的聲音被集中到了幾個科技平臺上。
當互聯網從極少數人蔘與的社區,滲透入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它就不再可能是先驅們嚮往的理想世界。現實裏的一切好與壞都被映射到網上,加速發生。但每天影響所有這些事發生的,不再是政府,而是相對而言人數有限、存在時間也不長的科技公司。正如扎克伯格的最新公開信所說,這也是一個越來越難以完成的工作。
面對影響力已經令人恐懼、並且還在增加的科技巨頭。監管機構、政客、活動人士甚至公司內部員工們都給它們列出一個個罪狀。而它們呼籲的處理方案也逐漸從罰單與承諾,升級爲嚴格管制乃至拆分。
我們以 Google 爲例,梳理了自 2005 年至今,外界爲這家科技巨頭以及它所代表的整個科技業列出哪些罪狀。
當中不乏相互矛盾的立場,也不只一次因爲要解決問題卻衍生出新的問題。
Google 的第一次反壟斷麻煩從圖書版權開始,還是互聯網公司習慣的“先幹了再說”
Google 決定掃描世界上所有圖書的祕密計劃開始於 2002 年,公司內部代號爲“登月”。這個剛剛開始商業化的公司每年花費 5000 萬美元去做和自己業務完全無關的項目。當時,掃描密西根大學圖書館被認爲需要 1000 年,而 Google 認爲自研的算法 6 年就能掃描完,而且會越來越快。
麻煩在技術之外。擁有圖書版權的作家們和出版商迅速意識到 Google 在沒有任何許可的情況下就洗劫了圖書館。2005 年 9 月 23 日,只掃描了幾百萬本的 Google 第一次被作家協會和出版商協會起訴,但 Google 用新技術打開的市場說服了作家協議和出版商。“絕版圖書在圖書館裏落灰一文不值,開放搜索能帶來新的收入。”
但反對和解協議的抗議激烈。時任哈佛圖書館館長的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說:“難道我們想把最偉大的圖書館交給一個想向我們收多少錢就收多少錢的大公司嗎?”
司法部反壟斷部門開始介入。案件的性質從 Google 是否有權掃描變成了建立並壟斷一個線上圖書市場。
司法部堅持反對 Google 還有一層考慮。反壟斷部門在結案報告中認爲不應該鼓勵 Google 這種先故意侵犯版權,然後再通過訴訟解決的做法。和解協議被法院前後 3 次否決。最終歷時 8 年時間,2013 年 11 月, 紐約州立法院裁定 Google 掃描圖書並不侵權,宣告案件結束。
Google 圖書的出現還是因爲 Google 在爭取實現自己的最根本目標,“索引一切信息並允許所有人免費訪問”。在這個過程裏,它沒有等待版權方的許可或者推動,而是搶先執行,等有了規模再去談條件。
類似的做法貫穿於互聯網公司向現實問題滲透的每個方面,不管 Uber 滴滴拉普通乘用車車主當專職司機、Facebook 的隱私邊界、最初沒有正式僱傭關係的外賣、放鬆侵權以獲得低啓動成本的視頻網站……用 Facebook 後來寫在辦公室牆上的一句話來說,都是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快速行動,打破常規)。
類似的問題後來還出現在 Google 街景車隱私醜聞和廣告醜聞。
2010 年 5 月 9 日,德國漢堡數據保護局發現 Google 街景拍攝車一直在收集沿路住戶家中 Wi-Fi 數據。遭到約談的 Google 堅稱街景車只是收集 Wi-Fi 的 SSID、MAC 地址信息,沒有儲存其他任何敏感的數據。時任 Google CEO 施密特解釋稱這是一名員工的私下行爲。工程師將一段代碼插入街景軟件系統中,“明顯違反”操作程序。但隨着調查的深入,Google 不得不承認的確儲存了敏感信息。
2010 年 10 月 25 日,Google 在官方博客中承認過往 3 年裏,Google 街景車一直收集沿途周邊用戶通過未加密的 WiFi 無線網絡發送的信息,其中包括電子郵箱賬號密碼、網絡短信、手機號碼、病歷等隱私信息,共 600 G。而美國 FTC 的調查報告也指出,Google 的高層和工程師都審查過相關代碼,但並沒有修改其中的問題。
2009 年,通過網絡賣假藥的美國商人大衛·惠特克(David Whitaker),把純淨水貼上類固醇的標籤,通過 Google AdWords 打廣告,以每瓶 1000 美元的價格從墨西哥賣給美國顧客。
被捕入獄的惠特克爲了減刑,主動在司法部的監控下再一次和 Google 進行交易。在執法過程中,Google 廣告銷售人員在清楚其沒有合法賣藥資質的情況下,還主動提出給惠特克設計網站,幫助虛假藥品促銷。最終 Google 被判罰款 5 億美元。
這些問題發生之後,Google 都受到鉅額罰單,而後建立機制修正問題獲得諒解。這成了互聯網公司的通行做法。
不過隨着規模擴大、控制力增強,科技巨頭面對的新問題不再那麼容易解決。
之後延伸爲科技巨頭以壟斷優勢遏制競爭,歐盟已經爲此開出數十億歐元罰單
2010 年 2 月,歐盟認爲 Google 刻意在搜索結果中降低市場其他比價服務的內容。 8 個月後,歐盟正式啓動對 Google 壟斷的調查。當時 Google 改變搜索呈現方式,當消費者搜索商品時直接指向商品頁面而不是當時在歐洲流行的諸多比價網站。
歐盟委員會分析了 17 億 Google 搜索查詢的結果頁面,經過 7 年調查後最終得出結論認爲 Google 存在打壓競爭對手的情況。2017 年 6 月,Google 被處以 27 億歐元的罰款,承諾改變搜索處理方式。
類似的指控還存於餐廳搜索。Google 更願意將搜索結果指向自己爲餐廳所設置的信息頁面和預訂服務,而不是指向競爭對手 Yelp 的頁面。
Google 更明顯的壟斷行爲是利用 Android 捆綁服務。
2013 年 4 月 9 日,歐盟提出對 Android 操作系統有關的反壟斷訴訟。認爲 Google 通過 Android 系統捆綁預裝自家服務應用,包括瀏覽器、相冊、地圖、網盤等。歐盟委員會最終確認 Google 的確存在通過排他協議和補貼壟斷製造商和運營商預裝應用的行爲。2018 年 7 月,歐盟對 Google 罰款 43 億歐元,要求 Google 單獨提供應用商店和系統。
《新壟斷資本主義與毀滅的經濟學》一書的作者貝瑞·林恩(Barry Lynn)認爲, Google 的行爲與鐵路公司將乘客吸引到自己的店鋪差不多。通過控制基礎服務打壓競爭對手。
但幾次判罰的爭議也都存在。Android 強制性捆綁應用問題較明顯,但搜索商品、店鋪爲什麼不直接展示信息而是要指向比價網站或者點評類網站?如獨立分析師本·湯姆森所指出的,“消費者搜索一雙靴子,爲什麼搜索引擎不可以直接展示最便宜的那個鏈接,而必須是一系列比價服務?”
美國 FTC 公平貿易委員會在調查後得出與歐盟相反的結論,認爲 Google 壟斷行爲並沒有損傷消費者的利益。但歐盟的做法在美國有支持者。
民主黨參議員艾爾·弗蘭肯(Al Franken)2017 年也呼籲將政府要求運營商執行的中立原則也用在科技公司頭上。他在給《衛報》的一篇評論裏寫道:“像運營商所做的那樣,Google、Facebook 和亞馬遜在其平臺上處理合法信息和商業模式時應該始終保持中立。”
參加 2020 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伊麗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形容,掌握網絡入口和平臺的科技公司就如同鐵路時代控制交通命脈的鐵路公司,在物流業務上影響競爭者成本,藉機控制市場。她提出科技公司應拆分成基礎服務和產品,讓科技公司無法既當裁判又做運動員。
但真正讓 Google 在有能力決定科技公司業務邊界甚至於去拆分一個公司的美國撞上反壟斷麻煩的,還是在於言論控制。
個性化算法決定互聯網平臺上你能看到什麼,而它也被指責爲縱容極端主義和兒童色情內容傳播
2007 年,Google 開始測試個性化信息推薦。算法分析用戶搜索行爲和喜好的視頻,推薦更適合的結果。
規模發展很快。8 年前,Google 訪客數量首次超過十億。現在 Google 佔據了全球 86% 的搜索份額,這還是在離開中國市場的情況下。硅谷的車庫創業明星變成一個影響二十多億人的巨頭。2006 年被 Google 收購的 YouTube 也發展爲用戶量超過 20 億的龐大平臺,用戶日均觀看視頻時長超過 1 個小時。算法推薦內容讓人們從主動搜索信息變成被動消費信息,一次次被推薦內容吸引,不斷刷新。
無法阻止的是,大量虛假、極端、色情、血腥的內容也開始出現在平臺上。圍繞着審查,Google 開始成爲言論控制討論的焦點。
沒有太多人質疑兒童色情和 ISIS 屠殺視頻應該被平臺刪除。2014 年,戰地記者詹姆斯·佛利(James Foley)在敘利亞遭到殺害,斬首視頻被上傳到 YouTube 後被平臺迅速刪除。
《大西洋月刊》主編丹·吉摩爾(Dan Gillmor)在文章中認爲 YouTube 做了正確的事情,但他也同時提出疑問,刪除斬首視頻看上去沒有問題,但並不是所有內容都如此黑白分明,言論控制的邊界在哪裏?應該交給大公司制定嗎?
可以明確的是,Google 的算法並不會主動對極端視頻內容進行傳播。但個性化推薦很自然讓相似內容得到流量的傳播。
《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Jack Nicas 做過一個測試,當用戶通過他們選擇觀看的內容顯示出政治傾向性時,YouTube 通常會推薦呼應這種偏向性的視頻,而且往往具有更加極端的看法。
Jack Nicas 指出算法這樣做的原因,科技公司需要刺激的內容吸引着用戶不斷點擊,讓平臺獲取大量用戶使用時長。
在對於惡意內容的審查中,算法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最新的新西蘭殺人事件中,YouTube 聲稱將刪除所有和槍擊案相關的視頻內容,但該平臺始終有視頻畫面流傳。Facebook 更是殺手直播的平臺,警方提醒後才關閉直播間。
去年 Google CEO 皮蔡在國會山接受質詢。反壟斷委員會成員,民主黨議員 Jamie Raskin 認爲 Google 通信工具被用來宣傳暴力事件時,它成爲一個嚴重的公共問題。皮蔡隨後承認,Google 在制定和執行有關仇恨言論和其他攻擊性內容的政策方面,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如今社交平臺刪除仇恨言論的速度越來越快。2018 年,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刪除了 72% 的非法仇恨言論。在 24 小時裏審查 89% 的仇恨言論內容,2016 年只能做到 40%。但以互聯網巨頭們 2018 年的規模,11% 依然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等到這次澳大利亞槍擊案視頻傳播發生,新的質詢又將在本週開始。
對極端內容的審查又遇到了過度審查言論的指責
2008 年,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曾作爲戈爾副總統候選人與小布什競爭落敗的約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致信 Google,要求刪除 YouTube 上數百個基地組織支持者上傳的視頻,其中包括武器製作教育和煽動戰爭視頻內容。
利伯曼在信中讓 Google 果斷做正確的事情。“刪除伊斯蘭恐怖組織視頻是一項直接了當的任務。”最終 Google 並未遵從要求,而是選擇刪除了 80 個相關視頻,保留剩餘大部分。
成立於 1920 年,在美國種族隔離時代就爲種族歧視發聲的 ACLU(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組織)對利伯曼表示抗議。ACLU 認爲在美國本土審查恐怖主義內容可能成爲控制互聯網言論的前奏。
矛盾的大爆發發生在 2017 年。那年 8 月 12 日,極右翼示威者和反對人羣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隨後宣揚納粹主義的極右翼網站 The Daily Stormer 被 Godday 以及 Google 這兩家全球最大的域名註冊商撤銷。它成爲第一個沒有明確違法行爲卻被硅谷主流公司全面封殺的網站。
隨着社會矛盾加劇,人們越來越不能容忍相悖言論。硅谷科技公司向來持有的中立立場悄然發生改變。被刪除的內容逐漸從斬首視頻、色情內容發展爲不同價值觀的內容。
ACLU 和民權組織 EFF (電子前哨基金會,強調民權的重要性,認爲政府不應該權力過大)都發表博文對近日科技公司集體靜音新納粹分子/網站的行爲表示強烈譴責。認爲用來屏蔽仇恨言論的行爲,最終也將會反作用於爭取自由權利的民權組織。此事的具體情況,可以看我們早先的報道。
如果說納粹主義還屬於相對黑白分明的議題。那今年的反疫苗審查就不那麼清晰了。
反疫苗的爭議延續了 20 多年。支持者認爲接種疫苗會導致兒童自閉,但醫療公司爲了盈利而隱瞞了這些信息,並資助了那些“疫苗無害論”的研究。反對者則認爲該言論毫無醫學證據,反而會提高兒童死亡率。正反雙方的爭論越來越激烈,科技公司終於被波及。比較極端的如 Pinterest、Facebook 和亞馬遜採取了直接封殺反疫苗內容的方式。YouTube 沒有刪除視頻,但增加了爭議內容的警告。
這遭到了美國兒科學會(AMA)的擔憂,該機構致函給 5 家科技公司,稱科技巨頭應儘自己的一份力量,確保消費者能夠獲得有關疫苗接種的科學有效信息,而非一刀切式刪除內容。
2016 年大選之後,自由派指責科技平臺傳播的假新聞干預了選舉進程
2016 年 11 月,Google 搜索大選最終結果被指向一個特朗普投票結果超過希拉里的假新聞鏈接。Google 隨後承認沒有成功避免假新聞。
《紐約時報》採訪了這條假新聞的製作者,得到的理由是熱點的政治新聞可以換來更高的閱覽量。
假新聞最初被認爲是博取關注,依靠瀏覽量換取廣告收入的行爲。但隨着科技公司的服務影響力增加,假新聞和虛假廣告內容被發現用於干預 2016 年大選。
2017 年 9 月,Google 發現俄羅斯總參情報局(GRU)機構在早先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曾花費數萬美元,在該公司旗下的 YouTube、Google 搜索、Gmail 等產品上購買廣告來發布虛假信息。
一個月不到的時間,Google 和 Facebook 被要求出席三場聽證會。圍繞着是否主動接受外國勢力投放的政治廣告(該行爲在美國違法)和是否有能力阻止假新聞的傳播。
率先發起指責的自然是對特朗普當選憤怒不已的自由派力量。曾任羅德島州總檢察長,民主黨議員懷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認爲科技公司在假新聞上沒有盡力處理,促成特朗普上臺。
2018 年 3 月,Google 宣佈投資 3 億美元解決假新聞問題。計劃讓算法更新以顯示更具權威性的內容,而 Facebook 則宣佈要對媒體評級,增加大媒體內容的展示。
但這讓 Google 和 Facebook 陷入新的質疑。爲什麼由科技公司決定不同媒體的評級。《衛報》在社論中指出,提高大新聞網站的權重還會進一步減少小媒體的傳播。
與此同時,保守派則認爲 Google 在主動壓制自己的言論
到最後,無論是民主黨自由派還是特朗普代表的共和黨保守派,都在指責科技公司的內容傾向問題。美國保守派媒體《國民評論》在 Google 和 Facebook 出席假新聞聽證會後評論稱:自由派媒體和民主黨對於硅谷的態度取決於,硅谷是否能夠讓他們保持權力。只要能夠幫助到民主黨和自由派,那麼硅谷遇到問題也不會被指責。
而被認爲因假新聞收穫更多支持的特朗普,也在指責科技巨頭傳播偏見。
2018 年 12 月,共和黨國會議員佐·洛夫格倫(Zoe Lofgren)對面前的 Google CEO 皮蔡問了一個問題,“搜索白癡(idiot)一詞時,會出現特朗普總統的照片?”
皮蔡堅持認爲是算法導致,但議員對於 Google 打壓保守派的質疑並沒有平息。
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保守派衆議員拉姆·史密斯(Lamar Smith)認爲有不可否認的證據證明 Google 在壓制保守派的言論。他舉例 Google 搜索結果的首頁沒有一個保守派的網站鏈接,有關移民法的內容也被標記爲仇恨言論。
在線搜索營銷商 CanIRank.com 的一項研究也發現: 在 Google 上對政治詞彙進行的最近 50 次搜索中,顯示的自由派傾向網頁多於保守派網頁。
2016 年,獨立媒體流行文化新聞網站 SourceFed 發佈視頻,舉例指證 Google 搜索服務的聯想詞功能有偏向民主黨總統競選人希拉里的嫌疑。
2018 年 9 月 24 日,《華爾街日報》曝光內部郵件顯示 Google 員工進行了集體討論,試圖調整搜索功能以應對特朗普總統簽署的移民禁令。從而告知用戶如何爲支持移民的組織捐款以及聯繫律師和政府機構。事後,Google 堅持不會手動干預特定的搜索結果。
沒有證據證明 Google 和 Facebook 惡意控制着互聯網信息傳播,但在對它們在信息傳播當中所施展的巨大影響力,美國兩大政治派別已經從不同的出發點得出相同的擔憂。
搶走媒體廣告收入的 Google 被認爲是新聞業衰減的主因之一,影響了信息多元化
假新聞盛行的一個原因是傳統媒體式微以及互聯網平臺的展示方式讓判斷一個信息來源的權威程度變得困難。
2002 年,Google 推出新聞服務。新聞每個月有超過 40 億次的點擊:其中 10 億從 Google 新聞本身,而其餘的 30 億來自網絡搜索。
獲取新聞的方式變成了上 Google 搜索或者上社交網絡觀看。從 2013 年開始,從 Google 和 Facebook 引入的流量就超過媒體網站總流量的 50%。
直接的結果就是依靠瀏覽量增加廣告收入的美國媒體業開始大幅衰敗。2018 年 7 月,左派傾向的《衛報》撰寫文章,認爲 Google 正在扼殺新聞和民主自由。理由就是 Google 贏走了原本是新聞業的廣告收入。
2005 年開始,報紙的總收入從 500 億美元降到如今不到 200 億。美國新聞編輯室工作的人數從 2001 年的 40 多萬下降到今天的不到 18.5 萬人。
媒體的自由討論是美國第一修正案就開始保護的權利,對於電信和報業的反壟斷都在確保新聞的言論多元化。FTC 曾經出臺報業保護政策,要求報業可以在收入方面合併,但必須保留兩家不同報紙和編輯團隊。
科技巨頭的回應是自己重新資助媒體的發展。過去幾年中,Google 持續扶持本地媒體的發展。2018 年 3 月,Google 推出的新聞網站扶持項目 Google News Initiative(簡稱 GNI)。按照當時的計劃,Google 計劃通過 GNI 項目投資 3 億美元。
互聯網誕生之初對於信息自由流動的理想化願景逐漸被妥協和審查所取代,同時也沒有人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2018 年 8 月,Intercept 報道 Google 正在開發具有特殊審覈功能的搜索引擎 Dragon Fly。
此事引發全方位抗議。兩黨同時指責 Google,16 名兩黨議員組成的小組迅速成立調查此事的真相。與外界同等重要的壓力來自 Google 內部。一週之內,740 名工程師實名抗議。12 月 12 日,皮蔡參加聽證會,接受關於該計劃的質詢。皮蔡在質詢中反覆回答同一句話:“Google 目前沒有計劃推出(特別版搜索引擎)。”
這不是 Google 第一次做出類似選擇。2016 年,泰國軍政府表示 Google 接受要求並移除了侮辱泰國皇室的 YouTube 視頻。Google 雖然公開了透明度報告,對來自各國政府的刪除內容請求進行展示,但並沒有拒絕刪除內容的請求依然引發不小的質疑。
更早之前,2012 年,Google 還因一段反穆斯林視頻引起暴力活動,選擇屏蔽埃及和利比亞的訪問。民主和科技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的言論自由項目主管凱文(Kevin Bankston)形容 Google 走在一條危險的鋼絲上。一邊是屏蔽視頻對於自由言論的侵害,另一邊是平臺內容引發暴力行爲的社會影響。
這也是包括 Google 在內科技巨頭自己的疑問。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前主編傑森·龐廷(Jason Pontin)被 Google 委任研究一個問題——它能不能在保護自由言論的同時,監管有害內容?
互聯網誕生之初,它的推動者們曾希望帶來一個人人、處處可以表達信仰的新世界,如 EFF 創始人約翰·佩裏·巴婁(John Perry Barlow) 1996 年那封《賽博空間宣言》中所說的“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人人都可以進入這個世界,而不必考慮由種族、經濟力、武力、出生地而來的特權或偏見。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人人、處處可以表達他或她的信仰,無論這種信仰是多麼古怪,而不再害怕被強制沉默或強制一律。”
那封宣言允諾互聯網世界將讓傑斐遜、華盛頓、密爾、麥迪遜、托克維爾、布蘭代斯的夢想通過互聯網脫胎換骨,煥發生機。
而龐廷爲 Google 做的內部研究則得出另一個結論。Google 需要繼續做更多審覈,如果它希望取悅各國政府以維繫全球擴張。數據也顯示這麼做可以取悅廣告主——這也是免費商業互聯網的最大驅動力。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報告的結論也已經成爲互聯網巨頭的實際操作原則。
20 年間,科技巨頭從一個個新生的創業故事,變成滲入社會全部角落、控制着信息流動的開關,或主動或被動地影響着數十億人買什麼、看什麼、擁有何種程度的隱私、甚至如何工作。
現在關於這些開關的危害,被一個個擺了出來,但如何解決問題卻沒有顯然的結論。
一些政府已經行動起來。最近的比如新加坡立法管理網絡平臺假新聞,英國出臺《網絡危害白皮書》,明確對網絡公司的審覈行爲不力進行懲罰。更早的有多國各自不同版本但大多賦予政府極大干預權的互聯網安全法。
但即便只從 Google 一個公司所面對的指摘也不難看出,公權力的直接干預往往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題圖來源:W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