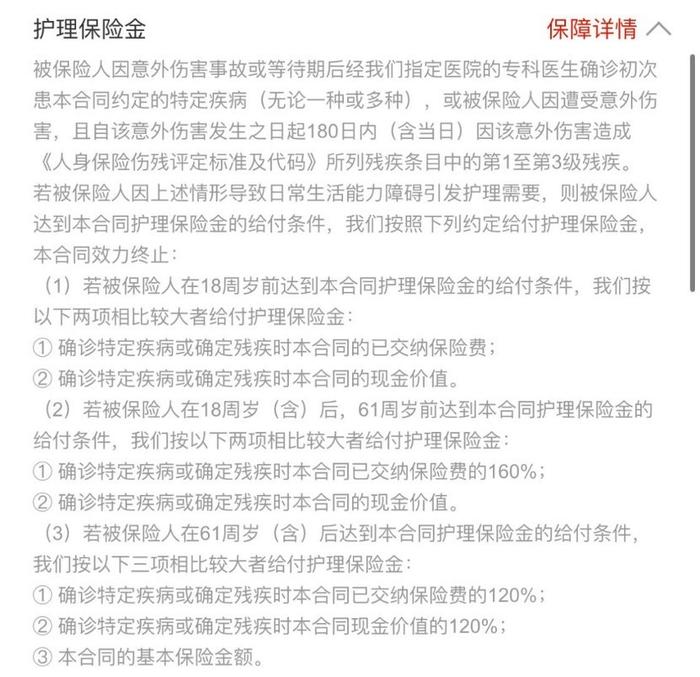個稅最高邊際稅率降至30% 免徵額提高到8000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18年6月29日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並開始爲期30天向公衆徵求意見的法定程序。
此次修正是自個人所得稅法1980年出臺以來的第七次修訂,也是最大的一次修訂。此次修訂的主要內容,首先是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四項勞動性所得首次實行綜合徵稅;其次是個稅綜合所得起徵點提到每月5000元(6萬元/年),再次是增加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專項附加扣除;最後是優化調整稅率結構,擴大較低檔稅率級距。與現行個人所得稅法相比,“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減輕居民稅收負擔。
但是通過深入討論和仔細研究,我們認爲,現有草案仍存在較大侷限,雖然是大修,但考慮不夠周全,如綜合徵收的範圍、最高稅率的調整、免徵額的確定、專項附加扣除的細則、政府部門授權等條款仍仍需進一步修改。
基於討論共識,我們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提出如下修正意見與建議:
(一)堅持依法治國,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嚴格遵守《立法法》有關規定,禁止將徵稅範圍、專項附加扣除的範圍與標準等稅收基本要素制定權授權給財政部
十九大以來,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黨中央批准《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意見》,要求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強調,“稅種的設立、稅款的徵收、收入的使用,直接關係納稅人的切身利益,關係人民的福祉,應由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立法機關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規範”。
依據稅收法定原則,稅收制定權力依法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第六款明確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
但本次草案第二條第十款規定“下列個人所得,應納個人所得稅:(十)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徵稅的其他所得”,第四條第十款、第五條第四款分別給與了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減稅、免稅範圍的權力,第六條最後一款規定“專項附加扣除的具體範圍、標準和實施步驟,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商有關部門確定”。
徵稅範圍、免稅與減稅的內容、專項附加扣除的基本內容和標準是稅種的基本要素,應當在《個人所得稅法》中直接明確。《草案》中多處出現將關鍵的稅收的基本內容的決定權授權給財政部的條款,明顯違背《立法法》第二款第六條關於稅收制度必須且只能制定法律的規定。
財政部擁有部分稅收制定權,存在“部門利益法律化”的空間,不利於切實保障公民的基本財產權益,不符合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時代基本方略。
我們建議,刪除上述第二條第十款、第四條第十款、第五條第四款三處違背《立法法》規定和稅收法定原則的條款,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確立徵稅範圍,不得授權給財政部。修改第六條最後一款,在法律中直接規定專項附加扣除的範圍、標準。修改第十一條第一款,在法律中規定預繳預扣的基本內容,稅務機關依此制定細則。
其次,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事關重大,應該審慎立法,不宜操之過急,不能只追求立法速度,忽視立法質量,應當以認真、嚴謹、求真、科學的態度對待此次《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正。財政部門、稅務機關應當向全國人大提供足夠的數據、事實,爲全國人大制定法律提供足夠的依據。
我們建議,在履行相應的審查程序以後,在2019年的兩會期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審查表決通過修正案,使廣大人民羣衆在2020年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性時期,享受到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帶來的可支配收入的持久提高,不斷提升人民羣衆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同時承上啓下,爲2035年實現共同富裕打下堅實的稅收制度保障。
(二)《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應當順應時代背景,鼓勵創新,提高競爭力以應對複雜國際環境
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財稅改革予以配套,《個人所得稅法》在大幅調整的時候,要明確個稅的功能與角色,要能回應時代的需求。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長期處於資本短缺、勞動力過剩,形成的稅制格局是勞動重稅、資本輕稅。但近年中國經濟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創新依賴於發揮勞動者的聰明才智,而勞動重稅和創新驅動型經濟相悖,個稅的改革方向應當是降低勞動者稅負、提升創新力,向勞動輕稅方向發展。
但中國個稅收入增速迅猛,2000年至2017年,個稅規模增長了27.9倍,遠快於一般公共財政和稅收的11.9倍和10.5倍,致使個稅佔稅收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3.29%上升至2017年的8.29%。即使到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2013年至2017年,個稅每年增速的平均值依然高達15.53%,遠遠高於同期全國GDP增速的平均值7.12%、全國稅收增速的平均值7.52%、城鎮非私營單位的平均工資增速的平均值9.71%。就在當前,2018年上半年的個稅收入8127億,比2014年全年多750億元,僅四年時間,個稅規模就翻了一番有餘。這顯然與勞動輕稅的方向是相悖的。
其次,近期中美貿易戰,美國對中興的芯片制裁,突顯了中國科技的短板,中央在多個方面出臺政策,鼓勵科研、創新,給科研人員減負,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國務院也特別要求“充分激發人才創新創業活力,改革分配機制,引進國際高層次人才,促進人才合理流動”。
我們認爲,要激勵人才創新,需要稅收制度配套,《草案》沒有回應時代的需求,工薪稅的最高稅率依然保持在45%,遠超資本紅利的20%,甚至高於美國現行的37%的稅率。稿酬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經營費所得三者併入綜合所得後,適用超額累進稅率,但不再適用現有法律減除20%的費用的規定,也沒有擴大較高檔稅率的級距,對於高智力羣體來說,這三種收入很可能大於工薪收入,實際增加了高智力羣體和創新活動的稅負,實際增加了嚴重抑制了中國人才創新的動力,也不利於企業的研發熱情。
針對境外人才,《草案》第二條,居民標準由原來的“滿一年”變爲“滿一百八十三天”,增加了境外人才的稅收負擔,與中國吸引國際人才來華工作的政策衝突,讓中國的人才政策在國際上處於劣勢,與當前中國自主研發、創新驅動的戰略背道而馳。
國際上來看,降低個人所得稅成爲主流趨勢。美國稅收改革大幅削減了個人所得稅,減輕人民的稅收負擔。在如此國際環境下,我國如果還保持較高的個人所得稅稅負,不利於鼓勵勞動致富,也會推動高收入者、高智力羣體流向境外,這兩類羣體所擁有的豐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也不能爲我國所用,喪失了人才競爭優勢。
我們認爲,《個人所得稅法》要算大賬,要服務中國經濟全局,要以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爲目標。稅收制度作爲基本經濟制度,不僅要能夠調節收入分配,增加人民羣衆的獲得感,還應服務於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促進國家發展。
當前最大的國家戰略就是增加勞動者的創新積極性,吸引和留住高素質人才,服務於我國的創新發展戰略,增強我國的綜合競爭力。
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應當順應國際稅改的趨勢,降低個稅的最高邊際稅率至30%(即資本紅利稅率的1.5倍),提高免徵額至8000元,擴大各檔稅率的級距,將勞務報酬等所得減除20%的費用後再納入綜合所得,全面降低稅負、簡化稅率,促進對高科技人才的吸引、鼓勵科研創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略,在制度提供足夠的競爭力,以保證中國可以贏得同美國等國的競爭優勢。
我們建議,爲了吸引境外人才增加在國內的停留時間,居民個人的認定應當保持“滿一年”等相關標準。
(三)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爲目標,將個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降至30%,減除勞動報酬、稿費等三項所得的20%的費用,擴大最高三檔稅率的級距
創新驅動型經濟有賴於人才優勢,而維持高稅率級距將對高等級人才產生擠出效應。以香港和內地的個稅比較,納稅人月收入3.5萬-7萬人民幣(4萬-8萬港元)區間,內地按30%和35%稅率分兩級徵稅,香港按7%的稅率徵稅。7萬-10.5萬人民幣(8萬-12萬港元)區間,內地按35%和45%分兩級徵稅,香港按12%的稅率徵稅。10.5萬元人民幣(12萬港元)以上,內地按45%的稅率增稅,香港按17%的稅率徵稅。即使和美國這樣財政收入極度依賴個稅的國家比,中國的個稅也沒有優勢。
從稅收徵管來看,高收入人羣可以採用公司化經營等方式合法籌劃稅收,當個稅稅率遠高於企業所得稅稅率的時候,會刺激高收入者採取避稅行爲,高稅率下會出現“收不上富人的稅”這一狀況,稅收的資金籌集和收入調節功能都無法實現。更有甚者,可能會出現高收入者爲了避稅而移民的現象,其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都流向境外,更是得不償失。
據統計,截止當前,可獲得數據的145個國家中,最高邊際稅率在35%及以上的有61個,在40%及以上的有37個,在45%及以上的有27個,大多數都是發達國家或者高福利國家。其中亞洲最高邊際稅率的平均水平27.61%,歐洲爲32.52%,全球爲31.36%,只有考慮到中國的社會福利水平,45%的邊際稅率,讓中國稅制在各類國際稅負排名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產生稅負重印象的關鍵因素之一。
然而,《草案》依然保持了45%的最高稅率,四項收入累加成爲綜合所得,較高檔稅率的級距也應該隨着收入多元化擴大,《草案》仍然維持最高三檔稅率的級距不變,這些收入多元的人羣可能就要按照比以往高一檔或幾檔的稅率,事實上增加了以智力、技術等個人能力爲收入主體人羣的稅負。
從中國現實來看,勞動收入能達到適用45%稅率的個人,必然也是各地方政府爭搶的人才,一方面政府要給各種補貼、優惠政策去吸引人才,另一方面,稅率還要保持在45%的高位,制度上有明顯的衝突。
我們認爲,降低稅率有利於減少避稅行爲,增加稅收遵從度,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從“避稅中介”流入財政口袋中,既增加了財政收入還有利於收入分配。有利於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低稅收一方面吸引境外人才,另一方面是避免本國的高收入羣體(比如企業家羣體)流向境外,也有利於鼓勵創新創造,減少勞動稅負,促進高智力羣體的創新活動。
我們建議,參考亞洲和歐洲最高邊際稅率的平均水平,取消35%和45%兩檔稅率,遵循國際稅改趨勢,簡併稅率檔次,按照3%、10%、20%、25%、30%共五檔稅率累進,適時取消25%。考慮到資本外流等因素,中國保持了20%的資本稅率,那麼只能降低勞動收入的最高稅率,以避免挫傷勞動者的創新熱情,將最高邊際稅率定在30%,低於美國的37%,略高於而資本所得和企業所得,既可以爲人才減負、切實的激勵他們的創新,又可以避免部分人羣以設立企業的形式籌劃個稅的現象。
我們建議,納入綜合所得的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等收入,先減除20%的費用之後,再與工薪所得一起綜合徵稅。現行法律中,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財產租賃所得,每次收入不超過4000元的,減除費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減除20%的費用,其餘額爲應納稅所得額。這個減除的費用實際是考慮了這些所得對應的經營性成本或費用。但此次的草案並沒有沿用原有的安排,顯得不是很妥當。這些收入的相關減除費用的規定應當平移到修正案中。
我們建議,適當增加較高檔稅率的級距,修正後稅法中,25%的稅率對應的應納稅額調整爲每年60萬-120萬,30%的稅率對應的應納稅額調整爲每年120萬以上。相比之下,美國最新通過的稅法中,單身個人的24%稅率對應的級距爲82501美元至157500美元(按最新匯率合人民幣55萬元至105萬元);32%稅率對應的級距爲157501美元至200000美元,35%稅率對應的級距爲20萬美元至50萬美元(合人民幣130萬至325萬)。
(四)切實增加居民收入的獲得感,將個稅免徵額提至8000元,保障居民基本消費支出,擴大最低檔稅率的級距至每年60000元以下。
收入,是百姓最爲關心的話題。降低居民的稅收負擔、增加居民收入,能讓人民羣衆最切實感受到黨和國家“一切爲了人民”的目標,感受到新時代的優越性,提高人民羣衆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因此,十九大報告要求“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在經濟增長放緩、做大蛋糕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個稅法的修訂,必須正視提高勞動者稅後收入這一時代需求。
免徵額體現的是納稅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我們建議免徵額的計算應當遵循三個原則:第一,免徵額的負擔水平應當與2011年一致;第二,免徵額的變動幅度,應當與職工收入水平、消費支出水平和通貨膨脹水平的變化一致;第三,勞務報酬所得、稿費等三種收入納入綜合所得,免徵額的變動應當考慮這一情況。
現行3500元的免徵額於2011年初開始實施。從2010年到2017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平均工資上升了103%,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長了110%。同期,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了81.5%,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水平增長了18.9%,這意味着居民的收入與支出水平在7年間都增長了100%左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還包括對老人的贍養費用,因此這部分贍養費用也應當扣除,隨着我國老齡人口的增加,就業者養老壓力增加,也會相應的增加個人的支出。
基於上述三點理由,我們建議,以2011年的3500元負擔水平爲基準,工資、薪金所得免徵額應至少提高到8000元,其負擔才大致相當,這樣纔可以回應公衆對長達7年沒有提高的免徵額的期待,同時,適當減少低收入者稅負,應納所得稅額不超過6萬時,統一適用3%的稅率,進一步降低中低收入人羣的稅收負擔,讓最廣大人民羣衆真切感受到黨和國家政策的溫暖。
我們認爲,免徵額對應的生活基本費用隨物價、消費結構的變化而逐年變化,法律很難達到一年一修,我們建議在增加“生活基本費用的動態調整機制”的條款,每年年初,由國務院根據物價水平、收入水平等,確定每一年的減除費用標準,在兩會期間,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審查和批准。
(五)專項附加採用標準扣除方式,精簡程序、提高效率
個人所得稅修正案增加了專項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的支出。教育、醫療、住房涉及最基本的民生問題,且一般是大額支出,將此納入專項附加扣除,體現了黨和政府“以人爲本”的執政理念。
專項附加抵扣將會影響居民的消費和支出行爲,因此要綜合考慮其他公共政策,細化專項附加抵扣,合理引導消費行爲。但是,《草案》沒有給出專項附件扣除的具體範圍、標準和實施步驟,僅提出“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商有關部門確定”。
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法》首先應明確規定專項附加扣除的具體範圍、標準,不應當將相關權力授權給財政部。專項附加扣除制度對稅率、實際稅負的影響很大,《草案》將其授權給財政、稅收主管部門,嚴重削弱了稅收法定的意義,也削弱了全國人大在稅收立法中的角色。
其次,我們建議,贍養老人應該納入到專項附加扣除範圍,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增加對老人贍養的抵扣,有利弘揚我國愛老敬老的傳統“孝文化”,增加對不斷攀升的老年人羣體的關注。
再次,專項附加扣除制度設計非常關鍵,如果程序複雜,納稅人申報成本過高,可能流於形式,納稅人享受不到實惠,也會使得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和稅務局之間的關係複雜化,可能會導致相關訴訟增多,把好事變成壞事。
如果根據實際支出票據報銷,可能會存在程序複雜、申報難、漏洞多、監管難的問題。憑票據報銷,可能會導致票據使用氾濫,票據的規範性和程序性也難以確定。報銷程序繁瑣,增加納稅人的報稅成本以及稅務機關的審覈成本。一方面,納稅人可能需要“報稅中介”提供服務,或者乾脆不申報,有違該條款減輕納稅人稅負的初衷,另一方面,複雜的程序爲納稅人虛假報稅提供了操作空間,增加了稅務機構監管、審覈成本。
我們建議,參考發達國家的經驗,子女教育、住房負擔、贍養老人等專項附加扣除採用標準扣除方法,而不能採用憑發票、按項扣除的機制。
標準扣除指的是以人口數(允許扣除的學齡子女、達到退休年齡的老人等)、住房(擁有按揭或租賃的住房)爲計算單位,針對每人次、房次確定一個標準扣除金額,多不補,少不退。
按照標準扣除,以人口數和住房數爲基準點,而非根據票據和麪積。低收入者家庭在子女教育的投入上往往小於高收入者家庭,低收入者住房面積更小、住房貸款和租金也相應更少。若憑票據報銷,會使高收入羣體獲得更多稅收專項扣除,而本來更需要費用減除的低收入者家庭無法充分享受該項稅收優惠。
因此,針對專項附加扣除,採取標準扣除方法,精簡納稅程序,提高申報效率。制定簡單明晰高效的專項附加扣住規則,提高納稅申報的可操作性,切實降低納稅人申報成本。稅務機關審查、監管也相對簡便,僅需覈對人頭、貸款情況,就能最大程度上避免繁瑣、防止作假。
繼續教育、大病醫療等項目,無法標準化扣除,可以採用憑發票、按“項”扣除的機制。
最後,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法》專項附加扣除標準應當地區差異化處理,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亦即在稅法中規定專項附加扣除的基本範圍、內容及標準的計算方式,將費用扣除標準(指數化、收入和消費水平)的確認權授權給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由地方政府提請地方人大決定。
考慮到專項附加扣除的複雜性,《個人所得稅法》在確立基本原則與內容之後,可以授權國務院決定細則,明確授權期限在兩年左右,授權期滿後,國務院應將成熟的條款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法律形式確定。
最後,希望此次最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能深入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不斷增加居民的收入獲得感,按照依法治國的要求,做到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保障民生,達到“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社會公平、服務經濟發展”的目的。
個稅法修正案討論小組成員包括: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杜莉、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施正文、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鍾瑞慶、長平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王長勇,以及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和聶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