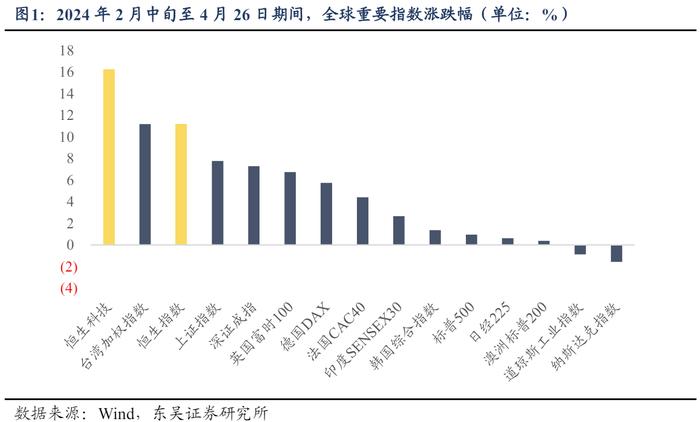投毒英雄谈毒倒众多日伪要员的南京毒酒案
摘要:”第二天,大后方的报纸报道了这件震惊中外的南京毒酒事件,参加宴会的日伪要员全部中毒,毒死了两个日本人,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我说:我们是领事馆的仆役,并给他们看了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日本兵没有下手。
本文摘自:《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 作者:田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申报》关于毒酒案的报道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们从抗战史专家口中知道了这件事。这起发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曾在大后方造成轰动,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之前中国军事上节节受挫(全国几无可战之军),政治上投降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鼓噪活跃,国际上孤立无援(英美奉行绥靖政策,苏联的军援实为坐视中日苦斗,以免除日人对其远东的威胁),抗战似乎走入了死角。
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往往需要一剂强心剂来抖擞精神,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当时社会心理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杀敌的功效。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2004年12月,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他说他是多年前听小区里的一位老人说起这件事的。 在南京一个肃杀的冬日里,我们随着街道干部在一个郁闷的小区里穿行。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楼。我们走进这位九十三岁老人的家,他向后退了几步,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能报道,日本领事馆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们要报复我的。”他的儿子说,老爷子现在有些老年病,有时神智不清。这就是一位刺杀行动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平静下来后,这位辛亥革命后两年出生的老人开始了回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1934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五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的指示。从此一生坎坷。
黄昏将至,屋里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长麟屋里的光线很差,到处摆放着上下铺的床,如同废弃的火车硬卧车厢。詹长麟的儿女两家人刚从青海回到南京不久,与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后,我们在下榻的宾馆对詹长麟进行了正式采访。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随老人一同来了,他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吃力,老人的记忆时常出现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总统府博物馆从事文史研究,对父亲经历如数家珍,经他提醒和补充,我们才完整地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采访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犹新:1、老人谈了两个小时,几乎没有喝水,当我让他喝口水时,文斌阻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投毒以后,从来不在外面喝水。”2、詹长麟曾谈到被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当时在场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血直往上涌。“诚心诚意地杀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詹长麟投毒后,全家亡命天涯,备尝离散之苦付出巨大代价。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而在抗战后所付出的代价,他肯定没有准备。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应对。詹长麟内向沉稳、信念坚定,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豁达,这也许是他历经磨难得以长寿的原因吧。 当我们离开南京时,他让二子文斌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关公。文斌解释,这是我父亲的守护神。
片子播出后,文斌打来电话,说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时候家里有人失声痛哭;当然不是为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东西。当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后前来关心了詹家,各种媒体也纷至沓来,我相信詹老会很泰然的,人生如戏,宽宽窄窄的舞台他走了那么多。“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他身上早已练就了适度、协调、温和的本领。
正文:
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饥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1934年,我二十一岁,我爸爸詹士良喜欢到南京鼓楼黄泥岗“何家茶馆”去喝茶。有一次,遇见一个叫王明和的织缎子的同行,喝茶间,王明和对我爸爸说,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
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作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 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日本领事馆对仆人的要求很高,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随后宫下又把我带到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办公室,须磨弥吉郎目测后,说了句日语:“要西(很好)”。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 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当时我们家住在南京黄泥岗下面的薛家巷十四号,这是一座四进的老南京民宅。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 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 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秘密组织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为名誉社长。
“蓝衣社”被视为复兴社中的“法西斯派”。“蓝衣社”初期主干由黄埔骨干构成,他们身着蓝制服,以区别普通党员,在戴笠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特务组织。——编者注)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我先后有过四个联系人: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
这四位联系人先后是我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戴笠——编者注)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讲,联系人对他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重复“信条”,其大意是: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伟大崇高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而为效忠党国,实现三民主义。 初做特务工作时,联系人黄泗清常谆教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后来,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 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旁白:戴笠非常鼓励下属特务介绍新人进组织,如某人长期不介绍新人,甚至会被认为是对工作的不积极。不仅如此,戴笠还特别鼓励成员介绍他们的家人进组织,家族式的组织一方面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便于管理,后来有人形容戴笠好像是一个大家长。
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6月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日本方面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要对中国动武。 藏本失踪的那几天,南京沸沸扬扬,有传言藏本在南京被暗杀了,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日本国的兵舰都开到了下关海面,战争一触即发。日本人历来是用假祸于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这次他们是不是想通过一个副领事的失踪,来挑起两国的战事呢? 6月6号晚11时,我正好在馆内值班,副领事藏本从总领事办公室出来,找到我,对我说,他现在要出去有事,让我找司机小刘(名字记不清了)把小轿车开出来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领事馆大门口,并拉开轿车门,让藏本上了车。我看到车直往北极阁方向驶去。我赶紧把藏本的去向写在一张纸上,告诉了组织。 事后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杀,企图制造他被中国人暗杀的假象。但是这个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自己家乡,不想死。他在那儿饿了两三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紫金山山上一个洞里面钻出来,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换吃的,结果被当地人发现了。因为得到我的情报,首都警察厅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寻藏本,村民发现他后告诉了首都警察厅的警察,大批警员上山去搜捕,在一个山洞里把他找到了。
首都警察厅就把藏本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领事馆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以后,跟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是这样解释的:“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过了几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国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物,我帮他装箱的。我为搜索藏本提供了这么一点依据,否则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发生了。
1937年,日本人在卢沟桥还是借口士兵失踪挑起了战争,战事很快发展到上海和南京。在日军占领南京前,为了避免战争伤害,日本总领事馆的全体官佐已经奉命撤离回国,日本领事馆停止办公。宫下出于对我和我哥哥的信任,吩咐我们俩在这段时间内继续留在领事馆,看管房子。
1937年12月13号南京沦陷后,我和我哥哥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不能离开南京,继续潜伏,了解搜集日军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尽管南京沦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日本领事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叫“日本领事馆使用人”。我们带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骑着自行车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地转,甚至郊区也去看,他看了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哪里发生大屠杀,哪里在杀人,哪里在放火,他都知道。并把看到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汇报。
南京沦陷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南京两个地方住过,一个是鼓楼二条巷,一个是广州路。二条巷是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靠近二条巷不远的大方巷曾经发生过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当时中国人老实,一个日本人用草绳把几十个被抓到的中国人拴起来,押着去屠杀,中国人都不知道挣脱草绳去反抗一下,老实到这种程度。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日本人太残忍了,你稍微动一点儿他就要打死你,实际上他把你拴住了,早晚还是用机枪扫,为什么不反抗呢,反正都是死。我永远不能忘掉的是:在广州路住的时候,日本兵到我们家来搜,找女人。我说:我们是领事馆的仆役,并给他们看了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日本兵没有下手。但在广州路,有个女人出来倒水,一个日本兵要强奸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反抗,日本兵就用刺刀把她捅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在上海路、在难民区,日本兵经常去那里抓女人强奸,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残暴罪行。在大屠杀之后,南京稍微恢复了平静,而占领南京的日军还经常晚上到金陵女子大学里强奸女学生。看到这些日军残忍的暴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对日军的暴行,真是一个字:恨。真是恨!我们讲这是民族恨,国家恨,还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万兴,他有个儿子,就是在日本轰炸的时候,死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从1937年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里,轰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飞机每丢一粒炸弹下来,只要是落到居民区,总是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的景象。
所以我要报这个仇,就是给中国人报仇。为什么要下毒呢?下毒就是为了替中国人争口气。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两个月的大屠杀之后,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又从日本国回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办公。我和我哥哥詹长炳又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当仆人为他们服务。
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听到这话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我时刻记着自己的任务。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什么叫忍辱负重,这就是忍辱负重。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三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
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系抗战初期在南京成立的汉奸傀儡政权。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京后,指使汉奸梁鸿志组织“治安维持会”。1938年3月取消维持会,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沦陷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维新政府宣告解散,并入汪伪政权。——编者注)汉奸要员。
我及时把这一重要情报向特务组织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名单中,囊括了当时驻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政府的骨干分子,包括梁鸿志。军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的特务情报组织——编者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反日寇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6月6日晚10时,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决定,在丹凤街二十二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
我哥哥去参加了会,会上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负责筹划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与我们兄弟俩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我们全家的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我负责在酒席上投毒。
为了保证投毒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让我投毒后,也喝上毒酒,与日军、汉奸同归于尽。这样子日本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好像就到此结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传达了。
我接受了最关键的任务——酒中投毒。但是,我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跟我哥哥这样讲,一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赔进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务后,尽量安全撤离。我还年轻,我不是不愿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能去死,我说我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个抗日力量嘛,还可以继续杀敌,继续为国家工作。
结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见又向上级反映,军统局后来认为还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须要做。”
军统局为了使我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还做了这样的安排,就是在1939年6月10日这天早上,请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父母,在南京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由军统局把家人全部送过江,到八挂洲隐蔽起来。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潘崇声姑父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USA三个字母。这个药是由军统局提供的。我手上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足有半斤重,领事馆里大大小小的柜子都归我管,所有吃的喝的也由我来管。酒是有专门的人采购来的。这次宴会的酒是从南京中华路老万泉酒店买的,这是一个老字号的酒店,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名酒都有。日本人最爱喝中国黄酒,黄酒称为老酒。喝黄酒的时候要温热。黄酒越热越好,人喝了不会醉,喝了以后不上头。我药拿到手以后,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就倒在一个温桶里,就是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晃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宴会开始以后,我佯装肚子疼,正好碰上一个叫刘玉山的仆人,我说我肚子疼,看一下医生拿点药就回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从后门溜走了。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当时历史的情况。
我哥哥一直在傅厚岗叫高原岭的巷子等我,我从后门遛出后,骑着自行车去和他会合。他还在傅厚岗买了两个枇杷。我们骑车穿过了玄武门,过城门时下车向日本兵鞠了个躬。江边有一只小船事先已经藏好等着我们。要上船时,我哥哥舍不得扔那两辆自行车,因为那两辆车非常好骑,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是日本货。燕子矶有个地方叫八斗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江面比较直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过江。当我正要上船的时候,日本前后两艘小火轮,架着枪,前后有一二百米吧,就开过来了,我和哥就把船划到江上的芦苇荡里。先避避风头,到了凌晨三四点才过了江,在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上了岸。
王高科一直在岸边等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说:“这么晚才到,你们再不来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气,说:“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气之下两个人吵了起来。我素来对他们俩人都没有好印象,因为两人平时有钱了,喜欢玩女人。
徐家洼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集镇,这个集镇有一个小茶馆。我们和接应人员早上钻到这个茶馆里面去。准备吃一点茶,好好休息一下。正在这个时候,日军一卡车,汉奸带着,就搜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他们该怎么办。王高科说后面有个空房子,于是我们几个人都钻进去了。一看有一张床,我哥就说他想躺躺,他说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话,房门如果关着,人家会起疑,我就把门打开,演了一个空城计。我们站在门后面,门开着,床上是空的,日军以及汉奸就从房子的这个门边一个一个走过去,没进那个房子。我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他们要是进来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据当时还在领事馆里工作的人讲,在我离开十多分钟以后,酒宴上就有人喊:“酒里有毒!”第二天,大后方的报纸报道了这件震惊中外的南京毒酒事件,参加宴会的日伪要员全部中毒,毒死了两个日本人,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官宫,是日本领事馆的会计,发钱的,这两个人吃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吃得少,没死掉。那个梁鸿志没死掉,日本人都中毒了,但听说,外头走廊上倒的倒,吐的吐。我听了心里很痛快,我一直等着这一天呢!我亲眼看见他们强奸过妇女再捅死,这个仇恨记在我心里,我为中国人报仇了!下毒就是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后来国民政府还奖给我一面刻有“忠勇杀敌 ”四个字的银盾。
得知领事馆的两个仆人不见后。日军开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据说是大小城门,外十三内十八,全部关掉了。结果他们都没搜着。他们抓了一千多中国人严刑拷打,还牵扯了我们很多亲戚。我有个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给日本鬼子打坏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给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口上烫。直到她去世,这个烫伤的伤口都没有愈合。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甚至连老万泉酒家的掌柜也遭遇了逼供。
徐家洼是军统局设在江北的一个据点。这是个秘密据点,主人叫毛蓝田。军统局是这样安排的。叫我们先潜伏下来,不要惊动,因为拖儿带女目标太大,一路上盘查也很多,半年以后再行动。大约过了半年,用毛驴驮着我们到上海去了,从扬州、泰州这一带慢慢去的。到上海以后就住在华北公寓。为了使无辜的人不至于生活得这么痛苦,上级就搞了一个假信,让别人写的,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国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誓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生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了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半年以后,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浙江现无此地——编者注)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戴笠——编者注)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因为没有钱,我们就落难了,那实在是受苦受难。我得了黄疸型肝炎,吃不下饭,病得很厉害。有一天走在街上,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突然拉住我,说:“你病得很重呀。”他说我眼睛看上去是黄的。此人是个中医。我们素不相识,他硬把我拉到店里开了几副药。吃下去一个月以后,病就好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人,他救了我一命。
在浙江,我本想靠卖稀饭、油条、烧饼、山芋维持全家继续逃亡,不过,只卖过一天,因为没有人吃。我们换换衣服又坐船到了福建莆田。好在家里人一直在一起。在莆田,我终于做起了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但全家的口粮仍难维持。我的大儿子腰上得小疖子,孩子们也瘦了。在浙江温州的时候,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小名叫圆兰子。因为营养不良,又得经常跑路,圆兰子最后死在莆田,埋在那里了。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从福建我们慢慢走,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
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抗战胜利以后,我带全家回到了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在励志社(创立于1929年左右,是蒋介石效仿日、美军队建立的一个军官俱乐部性质组织。——编者注)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我五万万元的奖金。其他的人都多少拿了一点,我拿得最多。
我提出,日本人打走了,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务,可不可以退出军统。上面同意了,但给我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安排了一个职务,是一份不用上班白拿薪水的工作。军衔是上尉,我每个月都要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钱。
1946年,我哥哥仍然留在军统局,主要是搞肃奸,把抗战时当汉奸的人揪出来。他当时红极一时啊。我拿奖金在中央门外的神策门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三层的旅馆。后来这附近的路也是我开发的,我还架上了电线杆。当时生意非常好,家里人口多,也就没有雇外人。旅馆里有电灯,有电话,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做生意很本分,该交的税都交,也时常接济附近的邻居。所以在后来我倒霉的时候,周围的人对我很好。唯一不顺心的是,我哥哥回来后,时常为财产的事在家里争吵。有一次,我老婆顶了他几句,他拔出枪架在我老婆头上,我在旁边吭都没吭一声。我老婆为这件事一直怨恨我。我们逃亡以后,原来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我哥哥列了一份财产清单(见附件)交给了国民政府。政府如数补偿给了我们。
1949年,解放前夕,我过去的上级赵世瑞找到我,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台湾,我当时很坚定不想去,因为旅馆的生意很好,我舍不得。
……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