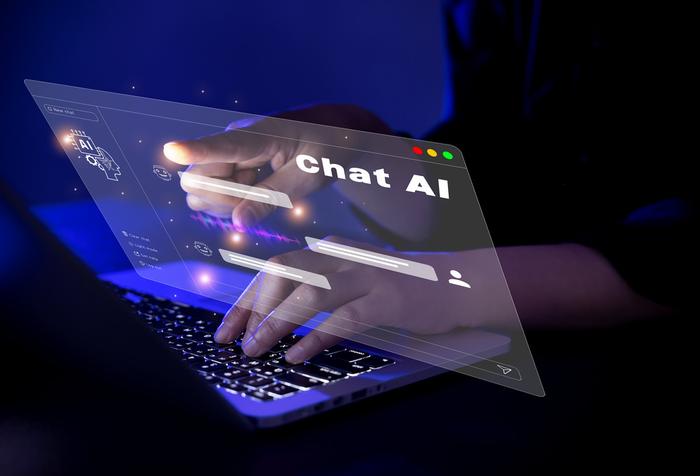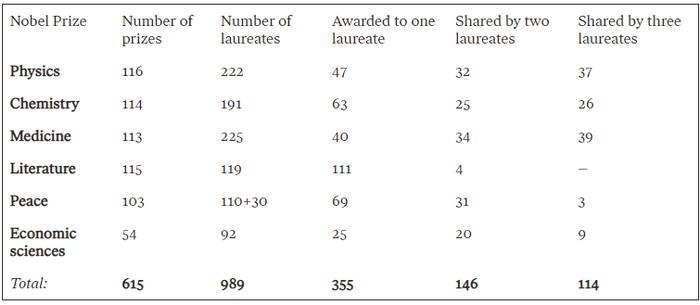小小說:湯輝的堅持
文/龔清楊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佈】
湯輝是我的哥們。我們有十多年的交情了。那時我才二十出頭,還是一個愣頭愣腦的文學青年。一次,我參加了市作協舉辦的一個文學活動。作協的活動跟別的活動差不多,都是領導們在主席臺上一本正經地講話,我們在下面一本正經地聽講話。輪到湯輝講話時,氣氛立馬活躍起來了。我記得當時是一個漂亮的女主持用聲情並茂地聲音說:“下面有請我市知名文學評論家、文學碩士湯輝老師講話,大家鼓掌歡迎!”
文學碩士?這四個字像鞭炮一樣把我們這幫文學青年震得一愣一愣的,要知道,我們這幫文學青年大多隻是中專或高中學歷啊!
湯輝那時候應該才三十歲左右吧,戴着眼鏡,白淨的臉膛上還閃現着些許的學生味道。最初,湯輝表現得有些慌場,有些羞澀,結結巴巴說不知道講什麼好,但一旦講開後,就顯得很有氣勢了。他像天女散花般講了一通朦朧詩熱潮、89年先鋒詩歌展、先鋒小說熱潮、尋根文學、新寫實文學等文學現象。講着講着,他忽然沒頭沒腦地說了句:“你們中間誰叫龍清楊?今天來了沒有?”
我當時愣住了,怎麼講得好好的忽然扯到我頭上了?這時旁邊的文友推了推我,我就糊里糊塗地站了起來,說:“我叫龍清楊。”
他衝着我笑了笑,又說:“請坐”。
我坐下後,他接着說:“我是前些天無意中在《鄂北文學》上看到了你的幾首詩。說實話,寫得相當好。我今天爲什麼要讓你站起來?是因爲我要主動地爲你的詩歌寫一篇評論。我還要申明一點,我讀研究生時,我的導師有一個特點,無論誰請他寫評論文章或者寫序都是請不動的。但他只要看上了哪一篇文章,就會主動地爲這篇文章寫評論。我老師說:‘漢字皆是神,紙張皆是神’。要對漢字和白紙有敬畏之心,絕對不能爲了人情世故寫一些溜鬚拍馬的垃圾評論文章……”
沒多久,這篇關於我的詩評文章就發表了。這篇文章使我在鄂北市文壇聲名雀起。最重要的是,這篇文章還解決了我的工作問題——市裏一家電視臺正缺一個編導,就把我招了進去。
一個人要有感恩之心,因此,我多次到他家去拜訪他。他跟我一樣,都有貪杯的惡習,我們時常聚在一起,點幾個家常菜,一瓶白酒,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我每次喊他湯老師時,他都有些不耐煩,就擺手說:“以後不要再喊什麼老師了,有學生跟老師經常在一起喝酒的嗎?我們是哥們,喝酒、寫詩的哥們。”
交往得多了,我就瞭解到湯輝的一些事情,他在一家國營工廠當工會主席,上班時沒什麼事幹,就把主要精力用在文學評論上和思想隨筆創作上。他的夢想是當一個尼采、培根、盧梭一樣的思想巨匠。
湯輝的日子風平浪靜地過了兩年多後,卻突然出事了——不過,這件事怎麼說呢,按照電影明星成龍的說法:“是男人都會犯的錯誤。”他是廠裏的工會主席,平常跟工廠裏的美女打交道的機會自然多。由於他沒有管好自己的褲襠,結果把公司的一個漂亮女孩子的肚子給弄大了。女孩子纏着要他離婚然後跟她結婚,但他卻壓根不敢跟老婆提離婚兩個字。這件事在公司裏鬧得沸沸揚揚,於是廠領導就撤銷了他的工會主席的職務。
湯輝原本就不大熱愛工會主席的這份工作,撤了正好,就開始找人活動,最後,調到市一家雜誌社裏當了主編。
一天晚上,我忽然接到湯輝的電話,說有急事找我。我問了地址,就連忙搭出租車趕去。到了一家酒店的包廂後,我看到湯輝和一個女人像兩件木雕一樣面無表情地對坐着。這個女人我認識,是我市一個小有名氣的女作家,筆名叫白玉蘭。人如其名,長得秀色可餐。我們以前在筆會上見過幾次面,也算是熟人。
誰料,白玉蘭見到我後卻是待理不理的,僅僅用鼻孔嗯了一聲,算是打了招呼。
而湯輝呢,卻低着頭猛勁地抽着煙。
問了好久,終於弄清楚了,原來,白玉蘭和湯輝相識後,就請他喫了幾次飯,一來二去,湯輝又犯了男人都會犯的錯誤,跟她上牀了。之後白玉蘭就纏着讓他給她寫篇評論文章。他固執地說:“我最怕的就是別人請我寫評論文章,這樣我會很被動的,找不到寫評論的感覺,屬於無病呻吟。”
白玉蘭說:“你當初答應過要給我寫評論文章的,所以我纔跟你上的牀。你一個大男人,難道說過的話像放屁嗎?”
湯輝說:“當初我是答應了,但當時的我是慾火焚身,是糊里糊塗答應的!所以說這種牀上的這種答應是不算數的。”
白玉蘭火了,恨恨地說:“我總不能白白地給你做愛吧?你一定要給我一個說法!”
萬般無奈下,湯輝就說:“我銀行卡里還有幾萬塊的私房錢,都給你吧。”
“幾萬塊錢就想打法掉我,你以爲我是叫花子嗎?門都沒有!”白玉蘭愈說愈氣,索性揪住他的領帶要跟他拼命。
一番討價還價後,終於談好了,湯輝給她十萬塊錢,兩人從此井水不犯河水。
可湯輝手頭上只有五萬,他想寫欠條,可白玉蘭不依,一定要當天做個了斷。他實在沒法了,就給我打了電話。
還好,我手頭攢了幾萬元,本來是打算買房首付的,看到湯輝有難,我二話沒說,就去銀行取了錢。
等白玉蘭揣着厚厚的十沓錢走了後,我不由得責怪湯輝起來:“你傻呀,你就硬着頭皮給她寫一篇兩三千字的捧場文章不就了事了嗎?”
湯輝揮着手說:“寫這種吹捧性質的文章,就像給婊子樹牌坊一樣,最沒意思了。”
我說:“哪你不寫,不就白白地給了她十萬塊錢嗎?老兄啊,十萬塊錢啊,厚厚的十沓,我真是服了你!”
湯輝卻哈哈大笑了起來:“值啊!不就是十萬塊錢嗎?十萬塊錢就把上牀的事情擺平了,多好啊!說實話,我寧願再多給她十萬塊錢,也不會寫那種亂七八糟的狗屁文章!”
我長時間地目瞪口待著,像看見了外星人似的。
(圖片來自於網絡)
顧問:朱鷹、鄒開歧
主編:姚小紅
編輯:洪與、鄒舟、楊玲、大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