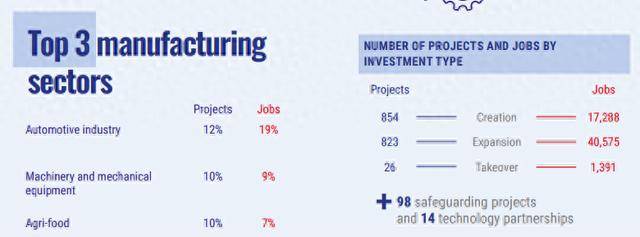基石資本張維:要命的從來不是宏觀經濟,而是跟風式投資
來源| 創業資本匯
熟悉基石資本董事長張維的知名投資案例的人不難發現,他是一個不追風口、不賭賽道、特立獨行的“另類投資人”:山河智能、山東六和、三六五網等等,都曾是別人“嫌棄”他“獨愛”的項目。
基石資本董事長 張維
但這些項目都有一個特徵:逆風翻盤,最終實現超高回報。
他是國內創投圈內最喜歡強調“投資與宏觀經濟無關”的PE(私募股權投資)大佬。從投行到PE的20多年工作經歷,讓他深知個人對於宏觀環境把握的“無能”,更加踏實掌握微觀企業個體的“全盤面貌”。
“要命的從來不是宏觀經濟,而是你跟風式投資、沒有獨立的思維和判斷,這是早期給我們帶來的一些重要的啓發。”在面對證券時報記者的專訪時,張維如是說。
投行經歷獲得兩個重要認知
大學畢業後的張維,進入安徽省政府機關工作。在外界看來,這個“鐵飯碗”可謂前途無量,但張維卻在體制內對自己的未來漸漸感到恐懼。
抱着學習經濟、瞭解經濟,也是爲了改變自己命運的想法,1992年,張維成爲了體制內下海大潮中的一員,轉戰深圳。來到深圳的兩年後,張維經常“混跡”於萬科、華爲等深圳知名企業的管理學課程,通過結識彭劍鋒與包政,也爲自己的管理學認知“啓了蒙”。
彭劍鋒與包政系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因協助華爲創始人、總裁任正非起草《華爲基本法》而聞名於商界。他們兩人都是管理學大師——德魯克管理學思想的推崇者,受他們的影響,張維開始閱讀德魯克的書,尤其是長達700多頁的《管理:使命、責任、實踐》,他前後反覆看了許多遍,讓他對管理學初步有了一個清晰的認知。時至今日,張維仍然強烈推薦身邊的同事看這本書。他說,德魯克用大白話,把管理學的道理講明白了,看完了這本書,你對管理的認知基本就開蒙了。
投行出身的PE投資人並不少見,張維也是其中之一。1999年,在納斯達克科網股估值高漲的示範下,中國開始醞釀推出創業板,一批本土創投機構應運而生。在這一背景下,原本在投行業做得風生水起的張維,逐步轉型進入PE行業。
經歷過IPO額度審批制的張維,在那段投行經歷中獲得了兩個重要的認知。第一是對企業的認知。張維說,在十幾年前,國內優秀企業數量很少,IPO發行的額度限制導致大量劣質企業上市,中國的經濟規模也沒起來。
第二是對資本市場的認知。在張維看來,中國的資本市場長期是政策市,而且政策是多變的。這就意味着,做股權投資,必須以和企業長期一起成長的心態,來幫助企業解決在成長中遇到的一些問題。
企業家精神是創造超高回報的核心要素
“投資與宏觀經濟無關,我們更看重的是微觀經濟個體。唯有企業家精神,纔是帶來百倍回報的根源。”這是張維的口頭禪。它的由來,跟張維第一個百倍回報的項目直接相關。
2004年,處於政府宏觀調控下的工程機械行業受影響較大,加上國內暫無退出渠道,當時沒人敢投山河智能這個項目。但在盡調過程中,張維及其團隊發現,項目創始人何清華教授是中南大學機械研究所所長,擁有非凡的企業家精神,公司“液壓靜力壓樁機項目”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不乏亮點,最終決定投資。
幸運的是,2005年,中小板的推出讓許多本土創投機構“起死回生”。而山河智能在2006年也成功於中小板IPO,並在2007年股票解禁時遇上A股前所未有的大牛市,這個項目獲得了120倍左右的回報。
“這個回報不是你規劃或者預期出來的,實際上剛投資的時候,我們覺得未來五年內能有兩三倍回報就可以了。”張維說,這個投資案例讓他意識到,投資能否成功,不來自於你對宏觀經濟的把握,因爲宏觀經濟是無法預測的。“在投資中,更重要的是看懂微觀企業個體,對於基石而言,我們認爲產業結構、財務報表這些只是第一層,相當於基本功。第二層不容易看懂的,是公司治理、企業家精神以及組織體系,這些東西決定了你不是靠短期的短跑取勝,而是靠體系取勝,同時也是基石資本的方法論。”
這當中,企業家精神被張維視爲是創造超高回報的核心要素。2003年,張維接觸到山東六和這個飼料領域裏的項目,又是一個“全世界都不認同”的項目,最終張維選擇了投資。
在張維看來,山東六和的三位創始人身上充滿了理想和抱負,體現在企業層面,早在20年前,這家公司就提出了服務營銷的概念。他們大規模對養殖戶進行免費的養殖培訓,並招收了大量農牧專業的大學生,下沉到養殖戶家裏,幫助他們進行更科學的養殖。
“這家企業跟他們的經銷商、養殖戶形成了很強的利益關係,股權分散,很多人可以享受到企業的紅利,甚至優秀片區經理在當時已經達到年薪百萬。而且在那個年代,他們創始人要求公司的所有中層幹部都要去讀MBA,學習管理學。一個公司,如果沒有抱負和理想,是不會這麼幹的。”張維說。
如果翻看基石資本的投資線路圖,大抵很難看到一些很熱門領域內的項目。從早期開始,張維及其團隊在投資風格上就已經開始形成不搶熱點、不跟風,堅持自身領投,不傾向於跟投的發展思路。
2006年,仍處於創業期的三六五網得到了張維的關注。當時,國內房地產網絡已經有搜房、新浪樂居、搜狐焦點等巨頭,很多人都覺得這個領域沒什麼投資機會了,因爲互聯網企業要做到前三名才能生存,但張維不這麼認爲。
在張維看來,中國市場的容量很大,互聯網企業的商業模式也在不斷轉型,時至今日房地產網絡仍未找到清晰的商業模式。因此,投資不能輕言有些領域已經被寡頭壟斷。2007年,張維團隊正式投資三六五網,將長三角地區內沒有被新浪樂居、搜房收購的互聯網企業找出來,促成了他們之間的兼併整合,最終將三六五網推上了國內的資本市場,也是唯一一家在國內上市的地產家居網。這一筆投資,他們獲得了150倍的回報。
投資案例失敗後深刻反思
截至目前,基石資本共管理基金規模逾500億,投資的企業數量超過110家。與管理規模相當的其他同行相比,這個投資數量僅爲他們的1/5到1/4。但與此同時,基石資本的項目退出比例超過40%,遠高於行業的平均水平。
在張維的投資經歷中鮮少有失敗案例,但張維認爲隨着投資經歷的持續豐富,失敗的案例遲早會有一些累積。
曾經,張維團隊投資過一家假髮企業,投資時企業的基本面相當不錯,但最終“死掉”了。後來張維反思,這個企業的“死亡”,某種程度上是被資本“撐死”了。
“獲得資金後,這個企業家有一個非常宏偉的擴張計劃,步子邁大了,讓自己消化不良而死。最初我們對企業家有過抱怨,後來發現問題出在自己身上。”張維說,他們發現,自己給了不恰當的錢,超出了企業的管控能力。“我們這些投資機構其實是有責任的,經常在企業順風順水的時候鼓勵他們接受更多的錢、做更大的盤子,然後到資本市場上去獲取更大的回報。我們的看法和企業家的看法一致產生了共振,把企業害死了。因此,在這個事情上,我理解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邊界,一定要很好理解才能做好企業。”
張維還談到了自己另一個“知名的失敗案例”。位於佛山市的鷹牌陶瓷曾經是中國陶瓷行業的第一名,1999年在新加坡上市,2005年,市場低迷,公司估值只是帳面淨資產的7折,而且公司沒有負債只有現金,從各種角度來講它都被低估了。張維及其團隊在新加坡市場收購了第二大股東的股權,收購成功後,他們做了美好的規劃:改善激勵機制,調動團隊積極性,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從新加坡退市迴歸國內上市。退一步,萬一沒做好,可以和當時一些沒上市但規模很大的陶瓷企業比如宏宇、馬可波羅重組,再回國上市。
但最終計劃落空,進入公司後張維和團隊發現,公司在治理和管理上仍然面臨困難,既無法簡單趕走原有管理團隊,也無法找到合適的團隊“接手”。而馬可波羅和宏宇儘管表示願意收購鷹牌控股,卻不願意把自己的企業拿出來上市,不願意公開財務。最後他們在新加坡市場把資產全部賣了,拿回了本金,“僅僅”獲得每年兩個點的微利。
“這次失敗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公司治理的複雜性,以及優秀管理團隊的重要性,優秀的管理層有能力創造價值,是企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張維說。
合夥人團隊堅如磐石
目前,基石資本共有10位合夥人,除了李小紅等3位是後來加入的合夥人外,張維、林凌、徐偉、陶濤、王啓文、陳延立、韓再武7人便是基石資本一直以來的創投團隊核心成員。
如此堅固而又“龐大”的核心團隊,至今仍堅如磐石,張維戲言,原因是最初就解決了合夥人的事業方向,以及定好了內部的“分贓規則”這些關鍵問題。
“在成立之初,我們就對公司的股權、利益分配方式都做了界定。爲了落到實處,真正控制投資風險,做到財聚人不散,基石資本設計了兩個制度予以保障。”張維說。
第一個制度是合夥人跟投制度。不同於其他PE慣用的合夥人在單個項目中跟投,基石資本要求合夥人只能以LP身份在基金中跟投。在實踐中,基石通常在發起每一支有限合夥基金時,都會預先確定10%-15%的總比例,由每個合夥人根據自身的情況認購份額。
是跟投基金而不是選擇性跟投項目,在張維看來,可以避免許多風險。首先,跟投項目容易產生道德風險,使得合夥人跟基金LP產生利益衝突。比如合夥人可以選擇優質項目大額跟投,對於一般的項目就回避。而在基金裏跟投,則能跟基金LP步調保持一致。其次,跟投基金也能夠提高內部合夥人的凝聚力,不容易形成合夥人之間不同人跟投了不同項目所導致的利益割裂,能夠調動公司的全部資源爲企業做增值服務。
第二個制度是投審會的一人一票制度。即便身爲董事長,張維也沒有一票否決權,他手上的票跟其他合夥人權重完全一樣。張維解釋說,這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絕因某個人喜好而帶來項目的投資風險,創造一種讓公司優秀的人才貢獻出最優秀想法的機制。
當下是加大投資好時機
在張維看來,國內本土創投機構數量的激增,除了最初的2000年前後的第一批之外,集中在2007年和2009年兩個時間節點。
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推出,允許創投機構採用有限合夥的方式成立公司,擺脫了此前有限責任公司和協議制度對管理人和出資人分別存在的弊端,清晰界定雙方權責,這個階段創投機構的數量得到了一定的增長。
2009年,創業板在深交所正式推出,國內的創投機構大批湧現。發展到今日,卻形成了魚龍混雜的局面,也讓行業的發展迎來了當下所謂的“至暗時刻”——許多中小型創投機構面臨“斷糧”,募資難幾乎成爲行業共識。
根據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數據統計,2018年上半年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共新募集1318支基金,已募集完成基金規模共計3800.22億元人民幣,上半年股權投資市場仍然呈現較明顯的募資難問題,尤其是對中小機構及新機構,募資總金額同比下滑55.8%。
募資難之外,行業的投資和退出也同步出現下滑。同一數據源顯示,2018年上半年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共發生投資案例數量5024起,涉及投資金額合計達到5795.02億元人民幣,同比下滑10.7%。與此同時,退出案例數量達到889筆,同比下降50.4%,受IPO審覈“嚴緊硬”趨勢的影響,IPO審覈過會率下降至49.2%,被投企業IPO上市數量同比下降35.3%,機構退出壓力增大。
在張維看來,斷定當下是“至暗時刻”仍爲時過早。他說,中國大部分創投機構還沒有形成自己清晰的風格,大多都在經歷“成長痛”的階段。所謂的“募資難”,對於真正已經形成品牌的機構而言,儘管也有影響,但沒有那麼難。
張維認爲,當下反而是受影響較小、老牌知名創投機構投資大發展的時刻。在他看來,當下二級市場的估值重心下移同步影響到一級市場,企業估值水平的下移,就是一個投資的好時機。
其次,張維觀察到,國內很多企業股權質押都觸及到平倉線,但這些企業本身沒有問題,因此很多地方政府有幫助企業釋放流動性的需求,這時候是創投機構的好機會。
“從投資角度來說,這是很有意思和價值的。因爲你反其道而行之,別人悲觀有很多宏觀因素的理由,但這些東西是你無法預測的。你要看到無論宏觀經濟增速下調到多少,總有一些新行業在崛起、一些優秀企業在成長,這纔是投資的本質,看微觀企業個體纔是最重要的。”張維說。
切忌妖魔化創投機構 政策對行業應適當寬鬆
證券時報記者:未來國家在扶持創投業發展方面有哪些可以進一步提升?
張維:第一,要公平稅賦。既然要鼓勵雙創,就應該不是徵高稅,而是一個相對公平的稅。我認爲20%左右的稅收是基本合理的,如果太高,創投機構會失去繼續投資小微企業、新興企業的活力,從而影響整個新經濟的成長。
第二,政策方面不應該給創投行業設置太多障礙。國家提出去槓桿,就是增加直接投資、權益類投資。對於監管部門而言,需要加強的是監管和信息披露,對刻意造假、虛假披露信息以及內幕信息的人嚴刑峻法。但對於創投機構而言,需要監管部門以平常心對待,尤其是對創投機構在減持、上市等環節設置太多條件,應該採取更加寬鬆積極的政策。
千萬不要把創投機構妖魔化,總覺得很多機構賺了太多錢。實際上行業內大量機構的投資項目是失敗的,基金層面是虧損的,因此需要一個公平中性的稅賦,也需要一個相對合理的減持期限、比例規定。
證券時報記者:創投行業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能夠發揮什麼作用?
張維:我不贊成自我誇大作用,我只能說我們是一支重要力量。國家要解決高質量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系統的過程。這個過程要求社會有一個寬鬆的創業環境,也就需要好的金融環境、資本市場相匹配去支持它。
當下,由於金融行業中出現了以P2P爲代表的一些“騙子公司”,監管部門因而設置了註冊的高門檻,這實際上是“因噎廢食”。總體上監管部門還是應該給創業者、創投機構創造一些寬鬆的條件,但對於打着新金融、科技金融幌子的非法集資必須強監管。
除了推動新經濟、新科技的發展,創投機構也可以參與收購兼併和資源整合來促進產業升級。現在中國大部分產業仍呈現出高度離散的狀態,意味着國內許多產業都存在規模效應和產業整合的內在需求。
此外,創投機構還可以參與國企改革,幫助國有資產通過產權變革來完成公司治理革命,抓大放小、退出競爭性的領域,必須通過民間的投資機構來發揮作用。因爲民營企業專注於效率和回報,如果靠另一個國有企業來控股,這個國企改革實際上是沒有作用的。
證券時報記者:您認爲創投業在哪些方面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紅利?
張維: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完成了從工業化社會到服務業社會的發展,催生了更多新興行業和具有成長性的領域,同時孕育出了一批高科技企業,讓創投機構從早期只能投一些製造業企業,到後來可以投服務業、高科技企業。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很多企業都處於模仿的階段,更多企業創新來源於營銷渠道的創新,極少數會在研發環節加大投入。事實上,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具備了相關條件,中國企業開始從仿製向自主創新轉型。在這當中,部分傑出的中國企業越發認識到要把核心資源投入到未來有意義的領域,這種投入不以企業是否盈利、宏觀經濟如何爲轉移。而這些傑出企業的背後,往往伴隨着創投機構。
證券時報記者:創投業對促進改革開放起到了什麼作用?
張維:能夠上市的中國公司代表了中國經濟中比較好的部分,根據清科數據顯示,當中VC/PE滲透率達到58.9%,背後都有不少創投機構的身影,對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上市公司是有支持的。
在一些新興行業,國有資金難以介入投資,主要還是靠民營資金。例如商湯、柔宇這類企業,在沒有實現規模化的營業收入之前,他們已經獲得了來自創投機構的大量資金支持。從這個角度看,創投機構對中國新經濟、高新技術的推動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同時也是推動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力量。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