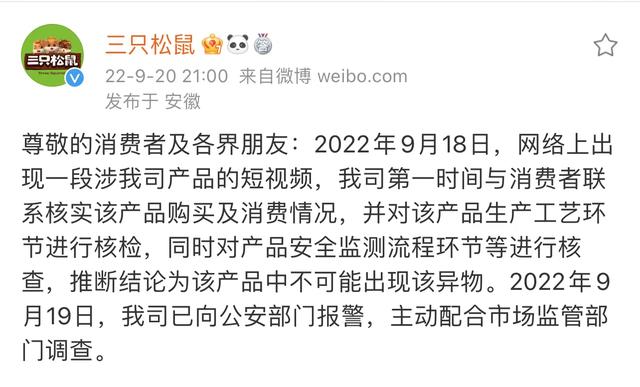中国人吃下水是因为穷吗?当然是因为好吃呀!
关于卤煮,有这么一种说法。乾隆四十五年,在下江南的途中,于扬州安澜园陈元龙家中吃到一道菜,非常喜欢,干脆就把做这道菜的厨师带回了京城。这位名叫张东官的厨师知道乾隆是重口味,就专门拿丁香、官桂、甘草、砂仁、桂皮、蔻仁、肉桂等香料炖五花肉。煮了肉的汤就叫苏造汤,煮出来的肉就叫苏造肉。造也作灶,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正经淮扬菜厨子做出来的菜是这种口味,不能细究。
上行下效,这种口味就逐渐成了北京城家里有铁杆庄稼的老少爷们的心头好,每天早上不来一碗就浑身不舒坦,感觉失了恩宠。到后来,这些位纷纷家道中落,北京城里做这道菜的口子都没了生意,怎么办?既然老主顾们都吃不起硬肋了,干脆就改做下水吧,于是有了卤煮。
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很多位老先生都写到过,不知真假,但苏造肉和卤煮的确都是搭配火烧。这段故事里透露出的信息值得注意,即便是由衷热爱卤煮这种下水大团建的食客,也默认吃下水是很穷气的一件事,只是吃得久了,成了传统罢了。
果然如此吗?似乎可以找出很多证据来。据说炒肝儿也是这么来的。上个世纪初,前门外鲜鱼口胡同路南有一家叫“会仙居”的小酒铺,报人杨曼青先生经常光顾。他吃了老板用猪下水模仿白水汤羊的汤菜后感觉不足,给老板出主意,用大料、口蘑汤等等调料把下水炖透了,添上酱,撒进蒜泥,熬稠一些,就成了炒肝儿。你看,这是用猪下水模仿的汤菜,有钱干嘛不直接去喝羊肉汤呢,对不对?
《清稗类钞》是清朝的饮食大全,饮食类洋洋洒洒写了九百多条,各地饮食皆备。但叙述到各地饮食时,极少提到内脏,写到苗人的饮食时,徐珂说他们养牛,牛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品,又无法储存,最常食用的是“枯脏”,也就是晒干的牛内脏。而在说到日常菜肴的时候,先是历数南北各色荤菜的价格,紧接着说到日常备荤菜,鸡鸭鱼肉之外,还有“猪、羊、鸡、鸭腹中之物,猪、羊头部之物尤便”。“尤便”二字,当然是指物贱,易得。
如果再往前翻,文人写的食谱中很少出现内脏。倒是元代的《饮膳正要》里不少,不仅有,还列出食性,显然羊肝、羊腰子、猪肚、猪腰子等物都是摆上餐桌的,不仅可食,还有讲究。再往前,《清异录》《山家清供》就没有,从中也可以看出元代食风。
但更多的证据指向反例。先来说《清稗类钞》,其中的下水做的家常菜就不少。闽人重视花生,常常做清汤花生猪肚,据说很补。猪肺清洗非常困难,要洗净肺管血水、剔去包衣,但和野鸡同煨滋味甚美。猪肝炒制,加入十几根大蒜叶炒香。这都是《清稗类钞》中的记载。袁枚是美食家,《随园食单》里也并不排斥内脏,羊肚羹加胡椒、醋,美味。
再往前说,烧尾宴是中晚唐时招待新科进士、皇帝宴请群臣的高规格宴席,其上也不是没有下水,通花软牛肠就是一例。要是追本溯源,周代天子的餐桌上,也少不了下水,如果记载属实,那么时人已经知晓网油的妙用了。
中国人讲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潜意识里是整体的自然观,所有动植物的所有部分,总要吃吃看,才好分辨滋味的好坏,绝不天然地排斥哪一种,认为它不可吃。《山海经》里写到各处山川,总要写写这里有没有蛇,有人就认为这怕不是用来吃的吧,蛇肉好吃,所以要特别多添一笔。就是在这样的寻寻觅觅中,食客们知晓了下水的美味,因为好吃——或许部分有便宜的因素把——而常常食用它,并为它开发出美味菜肴。尤金·N·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的一个观点常常被引用,中国人尤其注重肚子有没有吃饱这件事,其他的反而不太在意,除非把他们饿极了,不然他们是不会奋起而反抗生活的。这个观点其实还有下一句,那就是因为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所以他们很少真的饿到肚子,韧性很强。
我们几乎是毫无选择地接受了所有的食物。第一次吃火锅要涮黄喉、百叶、牛肚,也就涮了,往往是品尝过其美味才知道食材究竟来自牲畜的哪个部位。对当代英国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往往吃之前就先对它心存抵触。中国饮食研究者、英国人扶霞·邓洛普在《鱼翅与花椒》中写到自己刚到中国的饮食经历,犹如上刑。她排斥爬行类和变蛋之类的发酵食物,能点肉就绝不点内脏,一次吃火锅时,同伴给她夹了脑花,她不得不变身成一个精巧的、小心翼翼的手艺人,借丢弃鱼骨头的机会将脑花偷偷处理掉。但她吃过之后,却发现这种食物“口感像奶冻,柔软绵密,又有很丰富的层次,真是危险的诱惑。”
所以不是外国人不能理解食物的美味,而是他们“天然”地把一些中国人视为食物的原材料排斥在了食谱之外,这倒也无可厚非,人总是对结构之外的事物保持警惕,这里的结构首先是指认知结构。但如果硬将这种差异套上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未开化的区别,那就惹人讨厌了。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表现出对中国人食用蛇肉和狗肉的厌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历史学家杜赫德表达过惊异,“鹿鞭……熊掌……他们吃起猫啊、老鼠啊之类的动物,也是毫不犹豫。”至于下水、鸡爪鸭头、鹿鞭牛鞭,就更是至今仍能使友邦惊诧的。
这种惊异和鄙视实在是没有必要。我本来疑心外国人果然是从来不吃这些食物和部位的,但种种资料表明并非如此。往根上说,希腊人就不排斥下水。《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儿子去寻求老英雄涅斯托尔的帮助,当时后者正在参加百牲祭,“人们刚尝过腑脏”,“他们给客人一些祭牲的腑脏”。至少在希腊人看来,吃内脏并没有什么不对。
继承了希腊口味的罗马人,把种种饮食技巧和食材带到了欧洲各地,除了日耳曼部落之外,何以最后形成了这样的禁忌,恐怕和宗教有关系。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分析了这种宗教因素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她举了《圣经》中的《利未记》做例子。在《利未记》中,上帝宣布了一条饮食纪律,凡是不统一、不完整、无法归类的动物,都不应该食用,那么不是偶蹄的畜类就排除在外,在水中却无鳞的也排除在外,如此等等。这样的纪律是宗教化的,它使人们排斥某些事物,不是出于口味、习惯等因素,而是出于对犯忌的恐惧。
在宗教化的中世纪,出于对巫术和黑魔法的恐惧,有更多的食材被排除在外。但有时人们会出于自己诡秘的心理来偷偷使用他们,比如在某些部位涂抹公鸡脑来壮阳。这种饮食的自我净化背后,也有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的因素,因为很多食材的确是难以加工,也不太容易见到的,饮食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供应、挑剔的食客和频繁的日常消费,这些条件的缺乏足以把非常规石材剔除出日常餐桌,比如下水。
另外一大因素恐怕是与中产阶级崛起相伴的大工业化的食品供应。人们吃的食材高度一致,想要吃独特的食材反而要费一些力气,比如吃有机的、吃本地生产的、吃超市买不到的,野味或内脏。大工业化的食品供应救了野味们,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几乎吃光了他们能吃到的所有野味和鸟类,只因为他们能做到,并且热衷于这种炫耀式的消耗,这种传承自罗马的饕餮使得水桶状的笨伯身材居然成了一时潮流。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下水这类食材远离了大部分普通人的餐桌,而使他们无意或有意的忽视了一个事实——内脏从来就没有从餐桌上真的消失过。法国人吃牛脑、牛肝、胸腺、牛腰、牛肚、猪膀胱,西班牙人还要再加上牛鞭和牛肠,意大利人则本着不浪费和尊重生命的原则,力求把所有部位都吃干抹净。据丰子恺先生所写,吃猫也应该是一种法国习惯,广东的龙虎斗里或许有法国人的功劳。
外国人对中国人饮食习惯的惊异,常常是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在中国下个馆子,实在是太便宜了,不用看食评、选一个良辰吉日,着盛装出席。在中国,趿拉着拖鞋,穿着背心,晃着腮帮子上的二两肉,就能在街口巷尾吃到非常好吃的东西。中国人乐于吃、善于吃,食物是他们抵抗庸常现实的一座堡垒。说到这里,古今中外的饮食实在是并无本质差异。友邦惊诧,实在是因为没文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诗人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在中国旅行时,夸张地记录了难忘的经历:“没有什么东西具体地归类为能吃或者不能吃。你可能会嚼着一顶帽子,或者咬下一口墙;同样的,你也可以用午饭时吃的食材盖个小屋。”是的,没错,可谁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