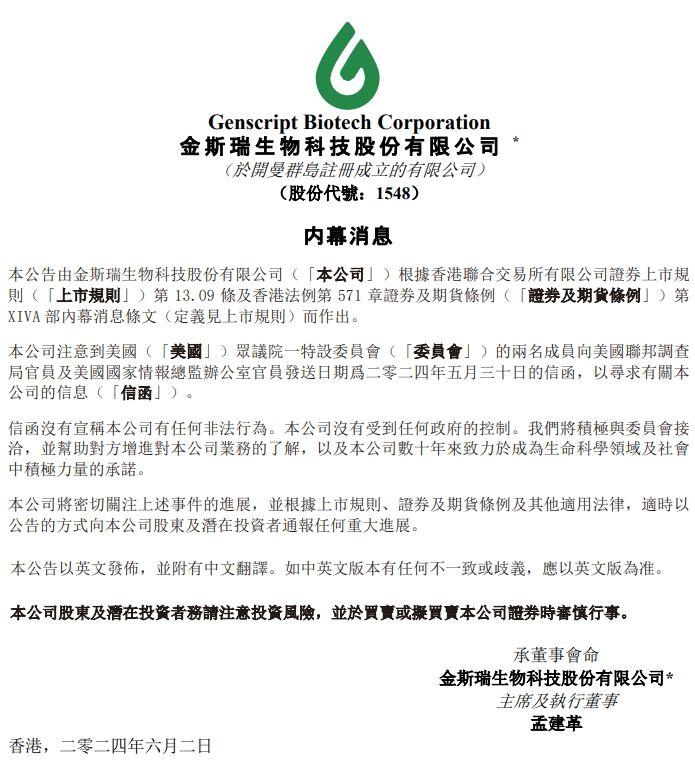【焦點議題】阿不力孜江·沙吾提 古力斯坦·亞生:當代伊斯蘭極端主義興起的原因及其影響
摘要:當代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作爲一種伊斯蘭教名義下的極端主義,它主張通過進行“聖戰”來實現全面徹底的“伊斯蘭化”,它是中東伊斯蘭國家多種內外因素在特定條件下迅速催化的結果。它不僅對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不良影響,而且對當今國際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對西方利益構成了嚴重挑戰,增加了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互不信任。伊斯蘭教主張和平、穆斯林世界反對極端主義、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互有需求,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不會發生全面的對抗和衝突。
關鍵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國際社會;西方;衝突;
自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突起,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1993 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發表後,把20 世紀80 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伊斯蘭威脅論”推向了高潮,伊斯蘭文明進一步被視爲對美國和西方安全與戰略利益的巨大威脅。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活動給予更多的關注。“1995 年3 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一項機密政令,它‘列明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機構必須向白宮提供重要情報’,其中包括‘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和恐怖主義活動’。這是冷戰結束後,白宮首次頒發的諜報政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前祕書長克拉斯也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冷戰結束後西方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之一’。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同樣重視‘中東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問題’,希望同西方大國共同遏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1]“9·11”事件以及一系列針對西方國家利益的極端事件的發生,標誌着敵視西方文明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極端行爲達到了高潮,“文明衝突論”在歐美贏得了更“廣闊的市場”。就連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也把新的反恐戰爭說成“十字軍東征”,雖然後來覺得用詞不當改了口,但是他心裏想的是一定要掃除與美國作對的異質文明———伊斯蘭文明,讓西方文明、西方的價值觀普照天下。2015 年11 月13 日在巴黎發生的恐怖事件重新引發關於伊斯蘭與基督教之間文明衝突的廣泛討論,讓人猜想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社會會不會出現敵對情緒的憂慮。那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真的那麼可怕嗎?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之間有什麼關係? 伊斯蘭極端主義爲什麼仇視和排斥西方文明等異質文明? 伊斯蘭世界會不會與西方打一場戰爭? 本文就此做一簡要的探討。
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
“原教旨主義”一詞源於西方基督教世界,特指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美國出現的基督教新教中的一種要求對《聖經》意義作字面解釋的基要派主張。在當時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只要談到基要主義,人們便會立即聯想到保守、僵化、復古倒退的極端主義思想傾向。因此,人們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與復古倒退、政治暴力聯繫在一起,給它打上了“恐怖主義”的烙印。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伊斯蘭教的歷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9 世紀的罕百里派,它成爲嗣後所有原教旨主義最重要的思想來源。在伊斯蘭曆史上,曾多次出現過以原教旨主義爲旗幟的宗教復興運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原意是復歸到伊斯蘭教初創時期的原始教義和本來精神,強調正本清源、返璞歸真。到18 世紀,阿拉伯世界內外交困,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伊斯蘭世界成爲掠奪和奴役的對象; 奧斯曼封建帝國極度腐敗,在對外戰爭中慘敗,人民愚昧、貧窮、落後,在伊斯蘭世界早年被視爲“異端”的“蘇非主義”盛行。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早期形態“瓦哈比”運動。它反映了當時廣大穆斯林羣衆反對外來侵略和干涉,維護伊斯蘭國家獨立的願望,希望藉助伊斯蘭教古老的教義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尋求新的出路和思想傾向。
但當前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又絕不是伊斯蘭發展史上的信仰淨化運動的簡單重複,當前的這一運動,無論在廣度或深度上都大大超過了過去歷史上的運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發展到當代,成爲與宗教現代改革主義和世俗民族主義相對立的一種思潮和派別組織。在中東伊斯蘭國家多種內外因素在特定條件下迅速惡化的情況下,主要以青年學生爲主的穆斯林民衆的宗教思想日趨保守、行爲極端,並且熱衷於全球化。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產生有着重要的思想根源,分別存在於遜尼派和什葉派之中,遜尼派穆斯林中極端組織數目衆多,極端主義思想的影響和危害更爲嚴重。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內部存在着不同的潮流和派別,但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還是極端派都主張不分邊界與民族,最終建立大一統的伊斯蘭神權統治。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宗教解釋上的共同點並不能化爲政治與社會立場上的共同點。主流的原教旨主義派別主張開展合法改革和鬥爭,希望參與國家的政治進程。激進派對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現政權持有對立的立場,而極端的原教旨主義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別組織中極端派的思想觀點、政治與社會主張的一種概括和界定。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主張、活動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它崇尚暴力,鼓吹一些人可以以“信仰”爲理由不擇手段地強制另一些人,直至鼓吹爲了“信仰”而殺人、放火、爆炸、投毒,實行不受任何道義約束的“超限”恐怖。“它是以伊斯蘭意識形態爲衡量一切的標準,反對一切非伊斯蘭的或反伊斯蘭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倫理規範”[2],主張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全面徹底地實現伊斯蘭化。實際上,“它已經脫離了伊斯蘭教原來的教義和精神,是對早年的那種寬容、開放、吸收、接納、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做法的否定”[2]。當代對國際政治影響最大的、最具破壞力的是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二、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產生的根源
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是伊斯蘭世界多種內外原因造成的。
第一,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的直接原因是近代伊斯蘭世界的衰弱和當代伊斯蘭世界面臨的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歷史上,西方殖民勢力爲了維護他們在中東的既得利益,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留下了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問題。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達到高峯,一批批民族國家紛紛獨立,他們或採納“西方化”的政治體制,或按照各自的民族主義理論治理國家,各種思潮在中東各國的政治生活中佔居了主導地位,伊斯蘭教的影響主要侷限在社會生活的範圍內。然而,這些思潮、模式並沒有解決什麼問題,反而帶來了一系列難以解決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特別是1967年阿拉伯國家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遭到慘敗,伊斯蘭教聖地耶路撒冷完全被以色列佔有,廣大穆斯林在深感恥辱之餘,認爲這完全是當政的世俗政權背離伊斯蘭教義造成的,因此,他們要求迴歸傳統,全面推行伊斯蘭化。伊斯蘭復興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開始蓬勃發展的。
第二,美國等西方國家干涉操縱中東事務,解決阿以衝突上採取雙重標準,推動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以色列猶太人國家的建立跟西方國家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建國後,它一直處於阿拉伯國家的包圍之中。幾十年來,雙方發生幾次戰爭,但結果以色列越來越強。阿拉伯世界和很多伊斯蘭國家的羣衆都認爲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的最大威脅,自己的共同敵人,雖然阿拉伯國家聯合起來了,但拿以色列沒什麼辦法。這主要是因爲美國在支持以色列,“50 多年來,美國從未拒絕過以色列的任何願望”[3]。如今一講到美國和阿拉伯人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無不強調以色列問題和石油問題。可是這兩個問題卻一直存在。冷戰後,雖然在美國的斡旋下,巴以和平協議終於簽署了,和平的曙光初見。但以政府出爾反爾,協議沒有兌現,成了空文。美國則背離公正中立的立場,長期推行壓阿親以的雙重標準,使廣大穆斯林倍感屈辱,心理嚴重失衡。他們對美以充滿敵意,對當局倍感失望,把解決民族危機的希望寄託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上。
第三,冷戰後兩極格局瓦解對中東國家造成衝擊,促進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迅速發展。蘇聯的解體,打破了冷戰時期在中東形成的地區均勢。原先受兩極格局抑制的各種地區矛盾重新激化,使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等問題迅速表象化。海灣戰爭爆發後,美國以此爲藉口在海灣大量駐軍( 被穆斯林羣衆視爲有悖伊斯蘭教義、褻瀆伊斯蘭教聖地) ,控制海灣地區、中東地區豐饒的石油資源,打壓伊拉克,威懾伊朗,嚴重干涉中東國家內政,通過推行“大中東計劃”,要改造整個伊斯蘭世界。通過促成“阿拉伯之春”,進一步分化阿拉伯國家。這些使得中東國家的民族意識和宗教感情進一步高漲,爲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創造了適宜的社會環境。
第四,民族主義思潮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爲主的殖民主義“宗主國”構建的全球性殖民主義體系開始瓦解。在民族自決和戰後聯合國推行的“非殖民化”運動中,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爲特徵的政治民族主義形成全球性浪潮。民族主義浪潮極大地刺激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穆斯林羣衆的民族主義覺悟。阿拉伯世界爭取本民族國家的政治自主、政治獨立,打破由於外力而被迫處於分裂的狀態、爭取統一和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要求與實際上處於外部勢力的控制之下的事實之間產生了摩擦。由於伊斯蘭世界許多國家的統治者專權、腐敗等問題而與廣大穆斯林羣衆處於相對對立的關係,穆斯林羣衆的這種強烈意願沒有實現,也沒有得到當局足夠的重視,並最終導致一些原教旨主義者採取了返回所謂的真實性、原本性文化傳統的政治戰略。
第五,是對文化全球化( 或者說西化) 的抵制、否定的結果。20 世紀80 年代後,隨着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網絡化、信息化以及文化的全球化趨勢不斷發展,對國家之間、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產生深刻影響。“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同質化、殖民化、高度互動化、相關化”。“文化全球化是以強勢文化( 西方文化) 壓制、排斥、甚至最終吞噬弱勢文化爲特徵的”。[4]文化的殖民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歷史上的殖民主義的延續,反映着霸權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隨着全球化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大力推銷西方的文化製品,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不斷衝擊傳統的伊斯蘭文化,威脅伊斯蘭國家的政治權威和社會穩定。“伊斯蘭教作爲一個完整的社會、經濟文化體系”[5]115,有其深厚的羣衆基礎。它本身具有強烈的政治社會特徵和輝煌的歷史成就。對於虔誠的穆斯林羣衆來說,伊斯蘭教法是他們的生活準則,不得隨意違反、更改,西方文明對伊斯蘭文明的最大威脅來自大衆文化。因此,西方文化的侵蝕,激起他們捍衛民族文化,反對西方滲透的民族運動。這樣原教旨主義的觀點被大衆吸納,其活動空間也相應擴大,不但廣大民衆抵制西方文化,而且引起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對西方文化的宣戰。
此外,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興起還與一些人對伊斯蘭教義的曲解有關。幾十年前巴基斯坦和埃及等一些國家反對西方思想的倡導者用充滿懷疑的眼光來曲解伊斯蘭教義。他們認爲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文化是邪惡和沒落的,現在阿拉伯世界或穆斯林國家的世俗政府是西方的傀儡,使伊斯蘭世界擺脫貧困、墮落、被西方控制的唯一方法,是伊斯蘭教成爲普遍的、絕對的制度,是用一切手段推翻一切非伊斯蘭政府,實現完全徹底的伊斯蘭化。在這些人的鼓吹下對“異教徒”所採取的一切暴力恐怖行爲被解釋成爲“聖戰”,爲“信仰”而殺人不是作惡而是行善,是合法正當的權利。IS極端暴力的特性,根源於他們極爲狹隘、排他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在IS的效忠者看來,是對《古蘭經》古典教義可貴的“虔誠”。IS的信徒們相信,如果穆斯林的信仰不夠虔誠,他們有權對其實施死刑。IS的教徒們認爲,他們殺人的權利是《古蘭經》賦予的。
三、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危害
伊斯蘭極端主義本質上是一場圍繞着政權歸屬問題展開鬥爭的政治運動。它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完整的政治理論,政治化的鬥爭方式。它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它的政治色彩遠遠超過了它的宗教色彩,深厚的羣衆基礎和社會基礎是它能夠發展壯大,擁有強大生命力和政治活力的社會物質基礎。伊斯蘭極端主義不分時間和空間,不顧特定的歷史文化和條件,不折不扣地貫徹伊斯蘭原初教義的文字性註釋,對國家的政治現實、社會現實持一種斷然否定的態度,具有一種政治激進主義的傾向,它對國家、民族、社會以及現存國際秩序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主要體現在:
第一,對國家主權的挑戰。根據伊斯蘭教的理論,真主主宰一切,國家的一切( 包括主權) 皆歸真主。在早期伊斯蘭教的實踐中,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權,這一時期被現代穆斯林羣衆視爲伊斯蘭的“黃金時期”。相當一部分穆斯林羣衆把現實生活中遇到的挫折與失敗全都歸咎於沒有依據伊斯蘭教法行事。穆斯林羣衆這種迴歸傳統的心態被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所利用,藉此極力提倡全面恢復和實行伊斯蘭法。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提倡“真主主權論”,認爲伊斯蘭國家的主權不在於民,而在於真主,真主擁有絕對的主權,宗教領袖的權力是真主賦予的合法權力,世俗化違背了伊斯蘭教法的普世觀念,屬於非法統治。這就意味着一切伊斯蘭政權只要違背伊斯蘭教義,便爲非法政權,全體穆斯林都有義務以各種手段推翻它。但回顧歷史,伊斯蘭國家歷史上根本找不到“真主主權”的影子。在漫長的中世紀曆史上,人們看到的是伊斯蘭封建王朝的君主以真主和伊斯蘭的名義實行統治。“真主主權論”是一種企圖通過曲解歷史來實現教權主義政治目的的價值觀。在此理論下,宗教的權威絕對,國家的主權有限,從而使伊斯蘭國家的有限主權和現行的國際法公認的國家主權不可侵犯原則發生矛盾。否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做法,對國家主權和現有的國際秩序提出了挑戰。
第二,對國家法律的挑戰。伊斯蘭國家的有限主權理論決定了國家只有司法權和行政管理權,沒有立法權。伊斯蘭法就是法律,任何政令、法規的產生都必須以伊斯蘭法爲基礎; 宗教和國家是一回事,宗教法律和世俗法律之間沒有界限。立法權在於真主,源於《古蘭經》和“聖訓”的伊斯蘭教法神聖不可侵犯,應當成爲國家立法的基礎與準繩,對於每個穆斯林和伊斯蘭政權都有約束力。真正的伊斯蘭國家應該以伊斯蘭法爲法律,真正的穆斯林( 包括統治者) 必須絕對地遵守該法律。如果伊斯蘭國家當政者實行的是不符合伊斯蘭法的世俗法律,穆斯林羣衆有義務推翻該政權,以恢復、維護伊斯蘭法的權威。在此理論下,幾乎所有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世俗政府是非法政府,成了他們推翻的對象。
第三,對國際秩序的挑戰。伊斯蘭極端主義對伊斯蘭教的解讀有很大的隨意性,而以政治性的解釋最爲突出。伊斯蘭教有“聖戰說”,每個穆斯林都有義務弘揚伊斯蘭教,也就是說要爲主道,爲傳播伊斯蘭教而盡心盡力。值得指出的是,《古蘭經》明確宣佈“對於宗教,絕無強迫”[6]60。伊斯蘭教主張穆斯林在遭到進攻或者受到傷害的時候可以採取武力。但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把“聖戰”的意思無限擴大,崇尚暴力,鼓吹人可以爲“信仰”而不擇手段地去推翻非伊斯蘭政權。實際上,它已經脫離了伊斯蘭教原來的教義和精神。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這種以暴力和恐怖手段作爲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是一股摧毀性的力量,是對現存秩序的破壞,“其結果是不斷深化目前正在發生的世界文化破碎性,引起社會動亂”[7]。由此可見,伊斯蘭極端主義不僅是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問題,它還具有世界性。
第四,對現代文化或文明的挑戰。伊斯蘭教“是一種文化體系以及一種生活方式”[5]115,有完整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倫理規範,並對穆斯林的影響很大,它嚴格管束着穆斯林的思想和行爲,不得隨意更改。伊斯蘭極端主義是以文化保守主義爲特徵的價值觀,它蔑視西方文化,排斥其他文化和文明,認爲伊斯蘭文明是全世界各種文明中最先進、最寬容、普世的文明。在相當一部分穆斯林羣衆看來,近代的歷史充滿了穆斯林大衆的血和淚,令人悲痛,這是大部分穆斯林國家偏離伊斯蘭正道的結果。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憑藉着野蠻的炮艦征服了穆斯林,精心培植和收買他們的代理人,迫使穆斯林民衆服從西方政府的保護,便以“新型穆斯林”的身份出現,抵制伊斯蘭精神,推崇西方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西方腐朽文化蔓延開來。西方文化的侵蝕嚴重衝擊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以伊斯蘭教爲基礎的文化傳統,西方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對阿拉伯世界的廣泛滲透和影響,嚴重影響了穆斯林的道德習俗和傳統價值觀念,特別是西方文化中許多腐朽的東西不斷侵蝕着伊斯蘭文化,廣大穆斯林倍感苦悶和迷惘,這激起了反對西方滲透的民族運動。穆斯林羣衆保護文化傳統的意願被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所利用。他們以自己的世界觀來看待其他的精神文化和思想意識形態,崇尚歷史上的神權專制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還傾向於以武力和暴力手段對付其他文明和文化,故極易導致出現獨裁、鎮壓、迫害、酷刑和強權政治等現象。
四、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不會發生全面的對抗和衝突
現代伊斯蘭極端主義作爲一種政治思潮、社會運動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宗教民族主義情緒。它敵視西方文明或異質文明,宣稱當今阿拉伯世界的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社會不公與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結果。唯有迴歸真正的伊斯蘭教教義,才能建成一個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諧的偉大社會。它崇尚暴力,嚴重影響和醜化了伊斯蘭教的聲譽,它的泛濫對世界和平與安全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增加了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互不信任。應該說伊斯蘭與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種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傾向。事實上,目前在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也沒有真的出現所謂“文明的衝突”,“9·11 事件”、巴黎恐襲案等,本質上來說並不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那麼,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會不會引起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全面衝突或戰爭呢? 筆者認爲,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不會發生全面的戰爭。
第一,伊斯蘭教本身是主張和平、勸善戒惡,鼓勵求知、反對愚昧,尊重寬厚、克己恕人,順應時代潮流的宗教。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派主張政教合一,崇尚武力,對西方現代文明極度的敵視和憎恨,有人說這是伊斯蘭教的本性使然,因爲伊斯蘭教本來就迫害異己,政教不分。西方某些政治家和媒體以偏概全,把伊斯蘭極端主義等同於伊斯蘭教,鼓吹伊斯蘭威脅,這導致相當一部分人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誤解和偏見。甚至在西方一提起“伊斯蘭”,人們或許想到的是進行“聖戰”、“武力傳教”,等等。這種情況正好迎合了某些西方政治家排斥其他文明和宗教的意願,爲其提供了話把。在阿拉伯語中“伊斯蘭”是“和平”、“順從”之意[6]3。按照伊斯蘭教義,伊斯蘭教的理想目標之一就是和平生活。雖然伊斯蘭教有崇尚武力的一面,但它倡導和平、主張與人爲善,武力只是實現和平的一種方式,而不是伊斯蘭教的目的。伊斯蘭教有“聖戰說”,但“聖戰”( 吉哈德) 的本意是“盡力”、“奮鬥”[8],也就是說,要爲主道,爲傳播伊斯蘭教而盡心盡力。但傳播伊斯蘭的途徑有各種各樣,主要有勸導、說服、感召等。《古蘭經》的主題之一就是勸善戒惡。因此,《古蘭經》明確宣佈“對於宗教,絕無強迫”。那些主張極端的、武力聖戰的原教旨主義的人,儘管有着伊斯蘭宗教信仰者的身份,但他們的主張不是伊斯蘭教的主張,他們不能代表伊斯蘭教,它背離和歪曲了伊斯蘭教義,綁架了伊斯蘭教。歷史上的穆斯林帝國也比今天的原教旨主義寬容得多。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是包容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幾種文明,經過消化、吸收、發展和創新,創造出了輝煌的伊斯蘭文明,伊斯蘭的生命力恰恰在於它能夠順應時代潮流。因此,不能把伊斯蘭極端主義等同於伊斯蘭教本身,不能看作伊斯蘭教的嫡傳正宗,它是一種宗教名義下的暴力。導致伊斯蘭與西方衝突的真正根源並非二者文化本身的差異,而是雙方共有觀念的敵對。
第二,多數穆斯林國家都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不僅不是宗教,而且它本身違背任何宗教精神,最終也損害任何真正的信仰。不僅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作爲一種人類之惡的極端主義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中也存在,是各宗教的一大禍害,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受害最大。雖然伊斯蘭教在伊斯蘭世界影響很深,滲透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得到部分羣衆的支持,但多數穆斯林國家是世俗政府,多數穆斯林是不會支持原教旨主義者極端行爲的。多數穆斯林並不認爲行兇事件的肇事者是伊斯蘭世界的代言人,而認爲他們是“醜化”伊斯蘭教的狂熱主義的傳播者。全面伊斯蘭化運動是一種要使伊斯蘭教成爲普遍、絕對和排他的唯一制度的運動,絕大多數穆斯林是反對和厭惡這一運動的。“9·11 事件”後不久,各伊斯蘭國家最高當局都譴責暴力行爲,因爲那些暴力行爲是違反伊斯蘭教基本原則的。伊朗是原教旨主義派最早贏得權力的國家。意味深長的是,在原教旨主義派掌權23 年後,伊朗變得溫和,尤其是伊朗的年青一代,明顯地表現出對正常的世俗生活的嚮往,對寬容與自由的嚮往。2014 年9 月,全世界超過100 名穆斯林學者和神職人員聯合起來向IS發佈了一封公開信,明確表明極端主義者的行徑與伊斯蘭教沒有關係。2015 年1 月《查理週刊》襲擊案發生後,伊朗總統魯哈尼如此表示。土耳其最高穆斯林神職人員戈梅茲也認爲,IS的恐怖行徑是對所有宗教的襲擊。但他同時表示,與伊斯蘭傳統無關[9]。
第三,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交流已經穩定化。一部分持“伊斯蘭威脅論”者片面強調了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衝突的一面,將其視爲一把挑戰西方文明的“毒辣的弓”,把擴張主義視爲伊斯蘭的本質,而忽略了兩者之間的相融和互動。實際上伊斯蘭文明參照了羅馬文化,伊斯蘭文化在今天的西方文明的繁榮中起到了很大的橋樑作用,可以說,如果沒有伊斯蘭文化就不可能有西方的“文藝復興”。雖然有過一些“血腥的”交往史,但兩者之間存有諸多交叉、重合和兼容之處。通過幾次的“碰撞”,當今兩者之間的交流已經穩定化。1965 年雙方發表聲明表示,不但要尋求對話,而且要共同促進社會公正、道德準則、和平和自由。這一聲明已經得到落實。在梵蒂岡與國際上的主要伊斯蘭教組織之間,基督教領導人和穆斯林領導人已經建立了經常性的情況交流機制。1984 年以來,雙方會晤不斷增加。旨在建立新秩序的真正合作已經取代彼此的長期對立。已故教皇保羅二世曾於2001 年5 月前往伍麥葉王朝清真寺,消除了兩大宗教之間長達15 個世紀的誤會和互不理解。“9·11 事件”也沒能阻止這種合作。“9 ·11”後教皇訪問一個穆斯林國家———哈薩克斯坦。此後,2006 年底現任教皇本篤十六世訪問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藍頂清真大寺,並與伊斯坦布爾大伊瑪目肩並肩面向麥加禱告,此舉被看作是增加雙方互解、友誼,消除歷史積怨、隔閡、緩解雙方矛盾的重要舉措,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通過承認伊斯蘭世界和西方的共同道德準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交流正式確立並穩定下來。穆斯林中少數人的極端行爲絕不會破壞這種共同的願望。多數穆斯林都表示支持共處和相互尊重。而西方大多數人也認爲,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緊張關係、衝突是由偏執的少數人引起的,伊斯蘭世界與西方“可以找到共同基礎”。
第四,伊斯蘭世界和西方經濟上相互依存。隨着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發展,各國、各地區或具有不同經濟傳統的經濟實體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正在不斷加強,促使着伊斯蘭世界的經濟緩慢地融入以世界經濟新秩序爲基礎的整體。伊斯蘭經濟制度的中正性,政治上的平衡以及人道主義,都有可能被西方看成是一種能促進交流和新秩序的文明。
人類社會雖然已跨入了“知識經濟”時代的門檻,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擺脫對能源的依賴,能源供應的穩定是世界經濟穩步發展的重要保障。伊斯蘭世界是世界主要的能源供應區,而西方是主要的消費方,這一事實決定了雙方經濟上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趨勢必然會促進雙方的經濟合作,經濟上的聯合對雙方都有利。
目前,歐洲—地中海地區以及黑海或中亞國家經濟區已經把伊斯蘭國家融入一種相互合作的混合機制,這就否定了所謂伊斯蘭世界和四方不相容的說法。1992 年6 月成立的黑海經濟組織就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和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在經濟上相互接近的典範。經濟具有使人們彼此接近的力量,因爲它已能使人們共同滿足自己所需,使意識形態的分歧降爲第二位,這是相互依賴性形成的和平努力。
此外,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現在都在經歷一個嚴重的危機時期: 這個時期對西方來說是價值危機時期,對伊斯蘭世界來說是地位危機時期。雙方如果團結起來,就都能找到挽救危局的辦法。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現在是兩個受到傷害的世界,彼此都需要對方,雙方不會爆發戰爭。
參考文獻
[1]金宜久.伊斯蘭教與國際政治[J].世界知識,1996(22).
[2]金宜久,等.講述阿拉伯人[J].世界知識,2002(16).
[3]田文林.對中東民族主義的多維思考[J].世界民族,2003(3).
[4]蔡拓.文化全球化對國際關係的影響[J].國際政治,2002(1).
[5]肖憲.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6]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研究室.伊斯蘭文化面面觀[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維吾爾文).
[7]王建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全球化[J].阿拉伯世界,2002(2).
[8]李建維.伊斯蘭教:三詰三辯[J].世界知識,2001(23).
[9]如何打贏一場與IS的“持久戰”?[N].新京報,2015-11-15.
來源:寧夏社會科學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