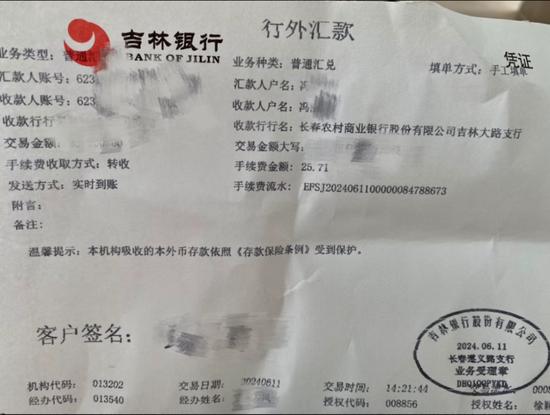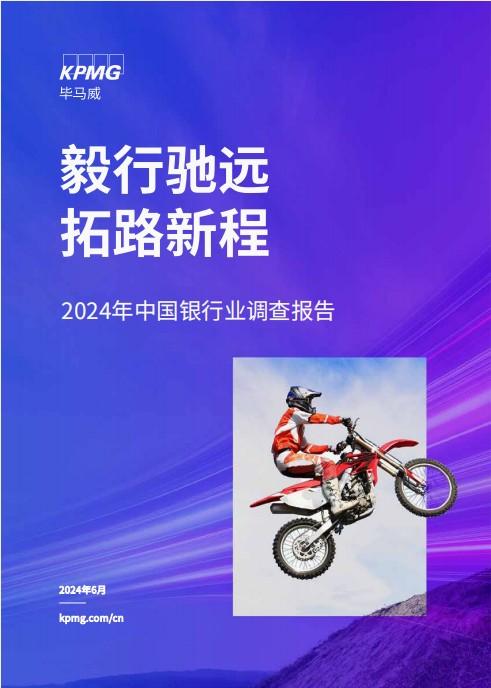王绍光:内参如何直达“天庭”影响政策议程 | 文化纵横
摘要:从1984年起,研究组被一分为三,人员分别进入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以及社科院农发所。从当年5月24日到11月,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先后六次召开由相关部委参加的座谈会,研究是否有必要制定破产法,曹思源在会上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及理由。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订阅《文化纵横》2019年4月刊。
✪ 王绍光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导读】内参是中国高层领导人重要的信息文件,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作者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经济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因而不能仅靠提高决策者自身能力来解决。这就要求对决策机制加以改造。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经济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因而不能仅靠提高决策者自身能力来解决。这就要求对决策机制加以改造。例如,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知识互补的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从“农发组”的一枝独秀到各类智库的涌现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开始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活动能量很大、具备“通天”关系的中高级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的支持下,该研究组成员四处开展调研,其调研报告可以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成立。随着研究组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成员开始转入其他机构。从1984年起,研究组被一分为三,人员分别进入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以及社科院农发所。
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
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如国情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如财贸经济研究所、金融中心等)、各部委办(如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各个国有商业银行都设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国务院参事室、各民主党派也表现踊跃,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
除公开发行的报刊外,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送到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室。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在正规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
▍内参影响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典型案例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案例看出来:
案例一:1983年6月,中国加入《南极条约》,但因中国尚未在南极建立考察站,其身份是缔约国,而不是协商国,在南极事务中享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和决策权。有鉴于此,1984年2月7日,王富葆、孙鸿烈等32位刚刚获得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的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到南极洲建站,进行科学考察。对这封联名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方毅、胡启立、乔石、李鹏、赵紫阳等相继作了批示。当时中国实力不强,国内四化建设处处急需资金,而南极考察站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现实作用。面对科学家开出的十年1.1亿元的预算,中央领导着眼于长远目标,反复斟酌必要性及相关经费问题,最后同意在南极洲建站,进行科学考察。1985年2月14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
案例二:1984年5月17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曹思源说服人大代表温元凯向全国人大递交由他起草的《关于制定“企业破产整顿法”的提案》及两个附件。人大很快将提案转到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厅又转到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当年5月24日到11月,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先后六次召开由相关部委参加的座谈会,研究是否有必要制定破产法,曹思源在会上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及理由。同年10月底,国务院领导同意着手研究如何起草企业破产法。次年1月底,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正式成立,曹思源参与其中。1986年夏天。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第一次审议国务院提交的企业破产法草案时,50位发言者中就有41人持反对意见。为了防止企业破产法胎死腹中,曹思源将自己写的《谈谈企业破产法》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手一册,并以该书作者身份给所有常委会委员打电话。修改后的企业破产法最后于1986年12月2日在人大常委会付诸表决,结果是101票赞成、0票反对、9票弃权。1988年12月,《企业破产法》开始正式实施。
案例三:经济改革全面展开后,价格体系,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扭曲,是当时最头疼的问题。在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成为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即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一方面,接近决策层的田源、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主张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以减少价格改革可能引起的震动;另一方面,张维迎等人提出,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后来,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则提出了“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在为会议纪要写的单独报告《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中,华生建议,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入手,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和完成整个价格体系的调整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便是“双轨制”概念的来源。会后,华生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代表,向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做了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很快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年即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标志着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正式被中央政府采纳。1986年,三十出头的华生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称号。
案例四:1986年3月3日,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等4位中科院院士联名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加速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亲自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200多位专家,研究部署高技术发展的战略,经过三轮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纲要。近20年来,“863”计划在促进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案例五:1987年,通过新华社内参,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的报告,提出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构想。这份报告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1988年1月,邓小平指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2月6日,中央政治局上确定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3月4日,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的口号;3月18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在原有基础上,把140个市、县(杭州、南京、沈阳等省会城市)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人口增加到1.6亿。为此,王建被评选为“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案例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从1985年起开始从事国情研究。1993年6月中旬,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随后出台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报告内容所提出的7项建议有6项先后被采纳。1994年,胡鞍钢提出“特区不特”的主张,建议逐步取消针对特区的优惠政策,实行国民待遇,为缩小地区差距创造条件。此建议虽然受到深圳市委和《深圳特区报》的连续批判,但中央领导最终采纳了他的大部分建议。另外,胡鞍钢与合作者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开发西部、正税养军等建议也在90年代后期变为中央的政策。为此,他还多次应邀出席国家最高领导人召集的问策会、国家部委召开的长远规划咨询会,成为高层决策圈的著名智囊。
—— 新书推荐 ——
《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
▍内容简介
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是大势所趋,还是短时间的概念泡沫?相较于人类社会过去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引发的革命性变化具有哪些特征?在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可能向哪些方向发展?具有千年传统的人文主义,能否依然能控制住拥有强大算法、海量数据且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世纪轮转,今天的中国,需要再次直面“赛先生”的挑战,重新理解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本书由《文化纵横》编辑部策划、出品,东方出版社出版,收入了金观涛、朱嘉明、王飞跃、胡泳、段永朝、吴军等学者的二十篇讲义,内容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现代医学”等前沿科技领域。虽然以新技术革命为讲述对象,但作者普遍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他们不是单纯地向大众普及新兴技术的原理及其应用,还从法学、哲学、历史学等多个角度,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新技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
▍本书目录
序言 重建真实性哲学(金观涛)
第一讲 后工业时代:意义互联网的兴起(胡泳、王俊秀、段永朝)
第二讲 互联网文明与中国制度转型(朱嘉明)
第三讲 “互联网+”时代的大国竞合(胡泳 王俊秀)
第四讲 大数据、机器智能与未来社会图景(吴军)
第五讲 “零隐私世界”:信息时代隐私保护的困局(利求同)
第六讲 大数据革命的商业与法律起源(胡凌)
第七讲 人工智能:第三轴心时代的来临(王飞跃)
第八讲 反思“人工智能革命”(金观涛)
第九讲 机器崛起:人机群体共生的新形态(王晓)
第十讲 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伦理(吕超)
第十一讲 比特币:预示未来货币形态和体系的实验(朱嘉明)
第十二讲 区块链重塑世界(段永朝)
第十三讲 智能机器社会的崛起:小法律、实验法、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余盛峰)
第十四讲 破解现代医学的观念困境(金观涛 凌锋)
第十五讲 现代医学的兴起、挫折与出路(李尚仁)
第十六讲 从“设计生命”到理解生命:对生命科学的哲学思考(金帆)
第十七讲 技术科学的风险与伦理重建(李尚仁)
第十八讲 警惕科学: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临界点上(田松)
第十九讲 “数码时代”科技与人文的契机(许煜)
第二十讲 AI时代的宗教:对世俗化命题的反思(李睿骞)
附录 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的对话(徐英瑾)
跋 抑制文人情结,走向“后人类时代”(朱嘉明)
编后记
本文摘自王绍光《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打赏不设上限, 支持文化重建
长按下方二维码打赏
转载须知
后台回复“转载”获取授权
进入微店
点击“阅读原文-进店”进入
投稿邮箱
本文已参与“最佳评论计划”,入选留言者,有机会获得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