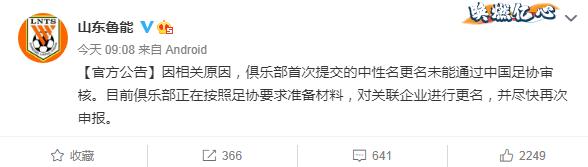小說:老宅子(全文)
作者:子 非
來源:樂亭文聯《潮音》雜誌/樂亭故鄉人網站專版
題圖爲配圖,和本文無關
一 、老宅子是活的
一座老宅子塌了。
就這麼莫名其妙地塌了,沒颳大風,沒下暴雨,也沒地震。
這座老宅子應該有五六百年了吧,聽長輩人說,是元朝時一個色目僧人建的。
宅子是典型的中國風格,沒摻雜一丁點兒西域特色。
文革時,紅小將們想一把火把它燒了,結果,當場就有一人發了瘋,其餘的人作鳥獸散。
後來,就那個發瘋的人活了下來,其餘的人皆死於各種事故。
我小時候,也經常去這座老宅子附近玩,老宅子就在我們鎮西,周圍林木蔥蘢,十分幽靜。
縣裏一直對這座建築不聞不問,也沒申請文物保護,聽任它在歲月斑駁中蒼老,死去。
老宅子塌掉的同一天,鎮子裏熱鬧非凡,不是紀念“雷峯塔的倒掉”,而是有一家人在辦喜事。
這家人搬來不到半年,據說是甘肅酒泉人氏,打工來此落戶。
在我們當地人的傳統印象裏,甘肅應該是永遠黃沙蔽日,不見藍天。
所以,他們來我們這兒,不啻於中國人不遠重洋來到了北美大陸,這樣理解便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這家人姓米,一共三口,父親,米建國,母親,米文月,女兒,米珊珊,一家人掉進了米缸裏。
無巧不成書,來米家入贅的倒插門姑爺也姓米,喚做米興邦,跟他老丈人的名字正好湊成一副對子。
因爲他們在當地舉目無親,所以花大錢請了一個歌舞團,連演三天,好能夠多聚些人熱鬧熱鬧。
當地人都說,別看甘肅人手裏不寬綽,辦喜事可是不含糊,捨得花錢。
歌舞團的節目很精彩,有武術,有雜技,還有魔術。
他們團裏的成員也是操着米家人一樣的口音,但他們自稱是寧夏人。
歌舞團當然有歌舞,不過是在晚上,跳傳統舞蹈和現代舞蹈,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和青年人。
第一天,我和一個朋友看完那座老宅子的廢墟後,便跟着人流來到了米家。一看,節目確實十分精彩。
第二天,我晨練,當跑過那座廢墟時,感覺有些不對,但也找不出哪裏不對,便又去看節目。
第三天,廢墟邊死了一個人,是那個瘋子,當年的那個倖存者,死因是心臟病突發。
人們發現他時,他用剩下的一口氣,拼力擠出了幾個字:“肉喫人……”
肉喫人?人們都哈哈一笑,說:這個瘋子,死了還說顛倒的瘋話。
三天過去了,歌舞團沒有要走的跡象。歌舞還在繼續,人們紛紛猜測:是不是這些寧夏人不想走了……
白天,都是一些男演員表演節目,女演員很少;到了晚上,卻是女演員唱主角,男演員都去睡覺了。
老宅子塌掉的第七天,我晨練,經過那堆廢墟時,發現有些彆扭的地方。
可到底是什麼地方彆扭,又無從說起,總之,給我的感覺是怪怪的。
我心一橫,決定走近廢墟去看看。周圍還有幾個早起的人,算是給我壯壯膽吧。
“肉喫人!”一聲大喊,嚇得我汗毛直豎。回頭一看,是解毅,我的老同學。
我打趣說:“老同學,你也信這瘋話?”
解毅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盯着我,一字一頓地說:“你-也-看-出-來-了。”
二、肉喫人
我臉上堆着笑,漫不經心地說:“我看出來了?看出啥來了?”
解毅仍舊板着臉,顯然在他心裏壓着一樁很重大的事。
他隨意朝四處望望,周圍稀稀拉拉有幾個晨練的老人。
突然,他“哎呦”一聲摔倒在地,我急忙去扶他。扶起他後,我看見他的眼睛閃着興奮的光。
他輕聲對我說:“你想辦法把耳朵貼在地上。”
我假裝做了幾個仰臥起坐,當我的頭一接觸到地面時,馬上就有一種“嗡嗡”的聲音刺入我的耳膜。
我驚訝地對他說:“地底下有一臺機器。”
他搖了搖頭,凝視着不遠處的那堆廢墟,自言自語說:“你是活的嗎?”
活的?猛地,我的腦海裏靈光一閃,困擾我幾天的謎題終於有了答案!
這堆廢墟在一點一點地復原!
三天前,當它神祕倒塌時,碎磚碎瓦撒了一地,現在,碎片的範圍在縮小!
解毅苦笑了一聲,說:“那堵斷牆,前天還沒這麼高,照這個速度,最多十一二天,這座宅子就會完好如初。”
我不禁打了一個冷戰,彷彿面前有一個古老的怪物正在慢慢甦醒。
我馬上又笑了,說:“別神經兮兮的了,房子有活的嗎?那我們還敢在屋子裏睡覺嗎?”
解毅轉身盯着我,好像我就是一個突然從洪荒闖到現代的怪物。
他又一字一頓地說:“它-就-是-活-的。”
我懷疑他最近沒休息好,他的眼睛裏佈滿了血絲,顯然這幾天在熬夜。
我說:“也許是我們神經過敏了,走,看歌舞去。”
他搖搖頭,說:“那幫甘肅人,來的真是時候,早不來,晚不來……”
我糾正了一下他的話:“那些人是寧夏人,跟老米一家不遠,但不是一個省的。”
他顯得有些不耐煩,說:“你還看不出來?他們都是一路的。”
他停了一下,又幽幽地對我說:“你知道歌舞團的成員都姓什麼嗎?”
我哈哈一笑,說:“不會是都姓米吧?”
他神情凝重地看着我,說:“對,他們都姓米。”
我想了想,反問他:“你是怎麼知道的?”
解毅笑了笑,說:“是他們裏邊的一個小夥子無意中說漏的。”
他說,有一天,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夥子去他的超市買電池,買得很多,幾乎就把他多年的存貨一掃而空。
他問,買這些電池幹什麼?小夥子支支吾吾地說,晚上使……
他又問,你們甘肅人都姓米啊?小夥子隨口說,就我們米家堡的人姓米……
馬上,小夥子又改口否認剛纔說的話,說,我說錯了,我們不姓米,我們也不是甘肅人,我們是寧夏人。
解毅暗暗好笑,覺得這個小夥子涉世未深,屬於那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
小夥子付完錢,用編織袋裝好電池,頭也不回地就走了。望着他的背影,解毅的眉毛擰成了兩個大疙瘩。
三 、一張撕掉的縣誌
我不禁皺了一下眉頭,問:“他們晚上使那麼多電池幹什麼?”
解毅搖了搖頭,說:“這我哪兒知道?走,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很快,我們就駕車來到了縣檔案館,解毅拉着我直奔二樓。
二樓存放着縣誌,一般是不允許隨便翻閱的,可解毅例外,因爲他跟館長是老同學。
解毅挑出一本厚厚的縣誌,擺在我的面前,說:“我給你看一段記載。”
只見他熟練地翻着頁,當翻到其中一頁時,他停住了,然後,他把縣誌正面轉向我,推了過來。
我一看,是一段關於元朝的記載:“有番僧自西域來,建屋而居,時本縣苦於水患,僧獻策,無不大妙……”
“僧不喜交遊,少鄰處,每值滿月,有異光聚於屋頂……”下頁是:“長毛之亂,始於廣西……”
我抬頭望了望解毅,他正悠然自得地閉目養神。
我問:“這元代的西域番僧怎麼又跟清末的太平天國扯上了?”解毅慢慢睜開眼睛,好像早就在等着我問他。
他說:“你這麼聰明的人難道還看不出來嗎?”
我猛地醒悟,細細看了看書縫,果然隱隱有撕過的痕跡。
我不滿地說:“你到底讓我來幹什麼?就讓我看這書少了一頁?”
解毅沒有回答,只是把手伸進夾克的內兜,等他的手抽出來時,手裏多了一張紙。
一張和縣誌一般顏色、一般字體的紙!
我伸手接過那張紙,紙折着。我小心地把它打開。
“每有樑上君子來,僧俱先知,皆饋金散之,若遇強梁,僧宣法號,則諸兇無不癲狂。”
“縣知事嘗微服造訪,僧泡奇茶敬之,知事歸邸,猶記茶香,而其它一概忘之。”
“某日,一牧童討水進屋,僧不知去向,牧童遍尋而未得水,出言僧屋有怪石閃動。”
“僧終不復歸,屋遂廢棄,後有三人避雨而入,言屋甚怪,不久,三人皆瘋,俱呼‘見鬼’。”
“由是無人敢入其屋,明永樂八年,屋倒,翌日,屋復完好如初,時人不知借神力抑或鬼力。”
“明正德五年,屋又倒,三日後,屋復完好如初……明萬曆三十八年,屋又倒,六日後,屋復完好如初。”
“康熙七十九年,屋又倒,九日後,屋復完好如初……嘉慶十五年,屋又倒,十二日後屋復完好如初。”
“宣統二年,屋又倒,十五日後屋復完好如初……”
縣誌是清末編撰的,關於此屋的記載到此爲止。
解毅看我讀完,問:“你看出什麼來了沒有?”我回答說:“原來這屋子鬧鬼,倒了又好,好了又倒。”
解毅調皮地揚着眉毛,說:“都二十世紀了,你還信鬼神之說?”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問:“那你用什麼解釋這件事?”
這回,解毅變得嚴肅起來,一字一頓地說:“用-科-學。”
我剛想反駁,他又問道:“你知道這張紙是誰撕下來的嗎?”
我反問他:“不是你?”他有點生氣,說:“這是文物!你把我看成什麼人啦?”
隨後,他壓低聲音,湊近我說:“撕這張紙的人,就是四天前死的那個瘋子,當年的紅衛兵!”
四、一個埋了多年的祕密
我不禁脫口問道:“是那個瘋子?”
解毅的回答更是教我大喫一驚:“你錯了,他根本就沒瘋!”
我又問道:“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裝瘋嘍?”
解毅笑着說:“你又錯了,他也沒有裝瘋。”
我沒好氣地說:“你在開什麼玩笑?”
解毅一本正經地說:“我沒開玩笑,我說的都是大實話。”
我問:“那你怎麼解釋那個瘋子的非正常行爲?”
解毅嘆了口氣,說:“因爲他在擺脫那些‘鬼’。”
我不解地問:“什麼‘鬼’?”
解毅沒有回答我,自顧自地說:“三十多年前,有四個紅衛兵,他們血氣方剛,天不怕,地不怕……
“有一天,他們抄縣檔案館,有個叫毛明的,隨手翻縣誌時,發現了關於那個宅子的記載……
“於是,他撕下那頁紙,還對其他三個人講了他的推測,他很聰明,推測得也很有道理……
“他推測:當年的那個番僧是位科學奇才,因爲某種原因隱居於此,他建的宅子很可能就是一臺機器……
“因爲凡有小偷來他都事先知道,可能宅子裏安有監控警報系統,至於盜賊癲狂,可能是由某種儀器所致……
“番僧不知去向,很可能是躲避仇家,宅子後來屢次倒塌,又屢次復原,極可能跟牧童看到的怪石有關……
“說完,他們就開始付諸行動了,他們大搖大擺地闖進那座數百年來令人談之色變的宅子……”
我脫口問道:“在那座宅子裏,究竟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
解毅接着說:“那座宅子極其簡陋,分裏外兩間,裏面空蕩蕩的,人一進去,馬上就有一種壓抑的感覺。
“毛明敲了敲牆壁,竟發出中空的聲音,他用拿來的大錘使勁掄了上去,沒想到,牆壁輕而易舉就破了。
“他發現牆壁窟窿裏面一團漆黑,隱隱約約像是有些亮點,他便湊近那個窟窿,想看個明白。
“其餘三個人,受不了裏面的壓抑,都在宅子門口等候毛明,他們覈計,要一把火燒了這個宅子。
“突然,那座宅子動了一下,他們以爲是地震了,隨之,便傳來了毛明的慘叫聲。
“毛明跌跌撞撞地跑出來,說‘我看見銀河系了,很多很多星星。’‘鬼!鬼!走開!’
“就這樣,毛明一會兒說看見了銀河系,一會兒又說看見了鬼,三個人害怕了,扔下他就跑了。”
我問道:“這個瘋子毛明,那天他究竟看到了什麼呢?”
解毅回答:“兩樣東西,他都看到了,他沒瘋,只是別人不相信他說的話罷了。”
我搖了搖頭:“我打小就看見這個瘋子大喊大叫,正常人怎麼會這樣,你怎麼解釋?”
解毅回答:“那是因爲他要擺脫‘鬼’對他的恐嚇,他一大喊大叫,‘鬼’就會消失。
“我猜測,那座宅子是有生命的,當那三個紅衛兵商議要燒掉它時,它發怒了……
“毛明正好在宅子裏,所以首當其害,那些‘鬼’不過是些幻像罷了,也許是人們心中的‘鬼’。
“凡是做過虧心事的人,心中就有鬼,那座宅子只不過把人內心的‘鬼’激發出來罷了。”
我問道:“那你是怎麼知道這一切的?”解毅回答:“毛明清醒時親口對我說的,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
五、一個神祕消失的民族
突然,有一個疑問浮出我的腦海:“毛明臨死前說的‘肉喫人’是怎麼回事?”我開始不再稱他“瘋子”了。
解毅站起身,說:“走,我們再去一個地方。”
解毅帶我來的地方是縣圖書館,這裏藏書很豐富,在遠近的幾個縣都很有名。
我們找好一個靠裏的座位,解毅從書架上拿下來一本書,書很厚,我一看,是一本辭典。
解毅開始翻找,找到那一頁後,把它推給我,然後,用手指在一個詞條上點了幾下。
這個詞條是“月氏”,其中,“月”有兩種讀法:一種讀“yue”,另一種則讀“rou”。氏讀“zhi”。
我有些不解,茫然地看着解毅。他笑着問我:“認識這兩個字嗎?”
我結結巴巴地說:“‘yuezhi’、‘rouzhi’,讀哪個好?”
解毅長出了一口氣,說:“中國的文明太燦爛了,燦爛得都有些麻煩了。我看你還是讀‘rouzhi’吧。”
我反問他:“你帶我來這裏就是給我普及燦爛的中國文明的?”
解毅笑着搖搖頭,說:“當然不是,你不是問我‘肉喫人’是怎麼回事嘛。”
忽然,我的腦海裏閃過一個想法,我終於明白“月氏”和“肉喫人”的關係了!
毛明在臨死前想要說的是“月氏人”!
我把我的想法說了出來,解毅衝我點了點頭,表示我的想法完全正確。
我又問:“難道是古代月氏人穿越到現代,用某種隱祕的方式殺死了毛明?”
解毅顯得有些傷感,說:“不是古代的月氏人,是現代的月氏人。”
我追問道:“現代的月氏人?我沒聽說過現代還有月氏人啊?”
解毅拿過那本辭典,匆匆翻了一會兒,找到後推給了我,同時說道:“你難道沒聽說過‘昭武九姓國’嗎?”
我剛纔對月氏有了粗略的瞭解,知道這個民族以遊牧爲生,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一世紀。
後來被匈奴攻擊,一分爲二:西遷至伊犁的,被稱爲大月氏;南遷至甘肅及青海一帶的,被稱爲小月氏。
我找到“昭武九姓國”的詞條,發現也跟月氏有着很深的淵源。
昭武九姓國,分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初居中亞,南北朝時期,散落中國新疆、甘肅等地……
一直默不作聲的解毅突然問我:“發現什麼了嗎?”
我剛想搖頭,但馬上眼前一亮:米姓……中國甘肅……我驚喜地說:“你是說米……”
沒等我說完,解毅一揮手製止了我,並用眼睛飛快地瞥了一下右邊。
我假裝掃視了一下閱覽室,在我們的右後方,坐着一個面目生冷的中年絡腮鬍男子。
他彷彿在看一本宗教方面的書籍,並時不時用犀利的眼神盯着我們。
解毅小聲說:“兩天前他就盯上了我,也許他看見了毛明跟我談話。”
我問:“他是歌舞團裏的人?”解毅微微點了一下頭,說:“他就是歌舞團的團長,平時並不出來。”
我又問:“那天毛明跟你說什麼啦?”
解毅回答:“毛明說有一個自稱月氏人的男子找過他,還問他是不是月氏後裔。”
解毅偷偷從內衣兜裏掏出一塊刻滿條紋的四方金屬牌,說:“因爲毛明脖子上掛着這件東西。”
六、處男和處女
不一會兒,我們已經走在縣城的大街上了,那個歌舞團團長也並沒有跟出來。
我突然發問:“那塊金屬牌兒是做什麼的?”解毅沒有回答,只是自言自語:“那個西域番僧是做什麼的?”
我笑了笑,說:“和尚還能是做什麼的?傳經佈道,超度世人……”
解毅朝周圍看了看,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塊金屬牌,金屬牌呈方形,很古樸,銀白色,上面刻滿彎彎曲曲的符號。
驀地,一隻蒼白的手變魔術般出現在解毅眼前,沒等他反應過來,金屬牌已經不見了。
我急忙回身,一個穿風衣的瘦高男子在朝跟我們相反的方向疾走。金屬牌,顯然是他奪走的。
“追!”我和解毅幾乎異口同聲地喊了出來,那人只是疾走,所以,追上他應該不成問題。
可事實遠沒有我們想的那麼樂觀,我們用盡全力奔跑,和那人卻始終保持一段距離。
追到一條偏僻的衚衕,我們看到那人拐進了一個帶門樓的院子。
這一帶住的大都是外地人,現在是白天,人們都在外面奔波,這裏顯得很冷清。
我們追進院子,發現這個院子髒亂不堪,只有一座陳舊的平房,紙糊的窗戶滿是破洞,像一張張飢餓的嘴。
解毅推開房門,走了進去,我警惕地掃視了一下四周,也跟了進去。
房子裏只有兩個板凳,一個板凳上各坐着一個人,一個是穿風衣的瘦高男子,另一個是面容姣好的紅衣女子。
“米珊珊!”我不禁驚叫起來。這個紅衣女子,正是剛剛成爲新娘的米珊珊!
“是你?”解毅也很意外,對穿風衣的瘦高男子說,“你不是那天買電池的那個小夥子嗎?”
瘦高男子緩緩站起身,從懷中掏出金屬牌,鄭重地交到解毅手裏。
我想活躍一下氣氛,便衝米珊珊開玩笑說:“新娘子不見了,不怕新郎官着急嗎?”
米珊珊一臉凝重,美麗的大眼睛冷冷地盯着我,說:“我不是新娘子,我還是處女,我是聖處女。”
我有些尷尬,想找個臺階下,便故作隨意地說:“你是聖處女,那他就是聖處男囉?”
米珊珊沒做聲,那個瘦高男子用一種平緩的口氣說:“你說得很對,她是聖處女,我是聖處男。”
我們呆呆地站在房子裏,想笑,卻笑不出來,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還是解毅打破了僵局,他問道:“你們引我們到這裏來,有什麼要我們幫助的嗎?”
米珊珊瞥瞥瘦高男子,冷冰冰地說:“天一,你告訴他們吧。”
米天一望着我們,慢慢地說:“救救我們,我們不想死,我的族人們是一羣瘋子。”
米天一突然問我:“你看過一本書嗎?是一位姓金的漢人寫的,名字叫做《天龍八部》。”
我笑着說:“當然看過了,凡有井水處,便有金大俠的書……”
米天一打斷我說:“你知道書裏面有一個人嗎?他一心想要光復大燕。”
雖然他問得有些無關痛癢,但我還是回答他說:“知道,不就是那個不愛美人愛江山,最後瘋掉的慕容復嗎?”
米天一盯着我,幽幽地說:“米建業就是慕容復,他想要光復大月氏,統治全世界。”
我有些啼笑皆非,問米天一:“米建業是誰?是哪家精神病院的病人?”
米天一有些驚慌失措,說:“你怎麼敢這麼說他?你不想活啦?米建業是米建國的哥哥,歌舞團的團長。”
這時,門外響起了一個洪鐘一般震耳的聲音:“不錯!你們馬上就會成爲精神病院的病人了。”
七 雞蛋的妙用
一聽這聲音,米珊珊花容失色,米天一癱倒在了地上。
我和解毅在圖書館見到的那個歌舞團團長面無表情地走了進來。
他身後,跟着米建國,米興邦,還有三個我不認識的人。
米建國一揮手,米興邦把門死死地關上了,那三個人則掏出了鋥亮的手槍,槍口齊齊地對着我和解毅。
米建業惡狠狠地盯着渾身顫抖的米珊珊和癱在地上的死人一般的米天一,寬闊的胸膛劇烈地起伏着。
整座房子彷彿瞬間掉進了深海里,很長一陣子,只聽得見米建業粗重渾濁的呼吸聲。
突然,他的面容溫和了下來,他用手輕撫着米珊珊蒼白的臉龐,親切地說:“珊珊,你忘了你的承諾嗎?”
米珊珊抽泣了起來,說不清是因爲害怕還是因爲悔恨,米天一像蛇口旁的青蛙,依然癱軟在地上。
米珊珊抬頭望着一臉慈愛的米建業,輕聲問道:“伯伯,我們必須要死嗎?”
米建業身子一震,痛苦地閉上了眼睛,房子裏又恢復了剛纔的死寂。
良久,米建業顫聲說:“我的孩子,祖宗的遺訓是這麼說的,我們就必須這麼做。”
我不禁問道:“他們都是花一樣的年齡,爲什麼要去死?你們這樣做是爲了什麼?”
米建業縮回輕撫米珊珊的手,用食指指着我說:“愚蠢的漢人,你永遠不會明白!”
解毅開口說:“我明白了,他們無意中得知了你們要殺死他們,所以想尋求我們的保護。”
米建業大踏步走近解毅,很快便從他身上搜出了那塊金屬牌,吻了一下,便收入囊中。
解毅看着三個黑洞洞的槍口,絲毫沒有抵抗。他明白:米天一說得沒錯,這真的是一羣瘋子。
米建業冷冷地喊了一聲:“興邦!”米興邦靠過來,畢恭畢敬地回道:“父親,興邦在。”
我不禁又喫了一驚,這米興邦明明是米建國的上門女婿,怎麼又成了米建業的兒子?
米建業望着破破爛爛的窗戶,問道:“今天晚上可以從地道去那裏嗎?”
米興邦回道:“可以,今天晚上可以行動了。機器也安裝好了,就差……就差……”
米建業接了過來:“就差那塊聖石了,是嗎?那塊聖石會在哪裏呢?”
解毅突然問道:“你們買那麼多電池就是爲了晚上挖地道嗎?爲什麼我們鎮上所有的人都毫無察覺?”
米建業望着解毅,譏諷地說:“你們看我們的表演,還顧得上地底下嗎?”
他又說:“今天早上,在那堆廢墟旁,你把耳朵貼在地上,難道什麼也沒聽出來嗎?”
我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這些人,難不成早就在監視我們?
解毅哈哈大笑,說:“原來那聲音是你們在挖地道,我倒真的沒往這上面想!”
米建業盯着解毅,說:“你們不知道的還多着呢,你們也用不着知道了,因爲你們馬上就要變成瘋子了。”
米建業緩緩踱到房子的中間,就像一位出征前躊躇滿志的帝王。
我看看解毅,希望他能想辦法擺脫眼前的困境,當我和他的目光相碰時,我看到的是無奈。
米建業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問米建國:“雞蛋準備好了嗎?”
米建國連忙回道:“四十一個雞蛋,不多不少正好。”
米建業不滿地說:“多準備十個,我不想把一個瘋子帶到兩千年前。”
八、真相大白
天漸漸黑了,月亮爬了上來。院子外,不知什麼時候停了一輛卡車,三個持槍人把我們押進了車廂裏。
車廂裏,擺放着一些演出用品,米建業,米珊珊,米天一和三個持槍人坐在我們對面。
米興邦和米建國沒跟上來,估計鑽進了駕駛艙裏。很快,車啓動了,車廂裏開始搖晃。
米建業微閉着雙眼,雙手牢牢抓住一個籃子,我猜測:裏面可能就是米建國說的那四十一個雞蛋。
解毅打破了沉默,問米建業:“您可以在我瘋掉之前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嗎?”
米建業慢慢睜開雙眼,說:“好吧,我可以告訴你這一切,反正明天早上你就跟你的朋友毛明一樣了。
“兩千多年前,有一個偉大的民族,這個民族就叫做大月氏。在她輝煌的時候,整個西域都是她的!
“後來,她消失了,消失在雪山下,消失在大漠中,消失在綠洲裏,消失了……消失了……
“不!她並沒有完全消失,她還留下了一條血脈,就是我們——米氏。
“蒙古人掃蕩西域時,我們米氏部族也遭到了屠殺,有一個僧人,帶着聖石輾轉來到了你們這裏。
“聖石是我們大月氏的鎮族之寶,每逢滿月,它就會發出五色神光,部族的人都在遠處膜拜。
“聖石可以使人發瘋,但它對處男處女卻造不成什麼傷害,如果不是處男處女,就必須在口裏含着一枚雞蛋。
“那個僧人到了這裏,安頓好之後,開始研究那塊聖石,他發現,那塊聖石居然是活的!
“他造了一座屋子,把聖石藏在屋子的地板下,沒多久,他又發現,整座屋子也居然是活的了。
“凡是有人走近那座屋子,他都會聽見屋子發出一種聲音,那聲音,就像是一個人在說話。
“他是處男,當然不怕聖石,可那些不是處男的人,卻會發瘋發狂。
“他精通天文,最後他發現,那塊聖石其實不是石頭,而是一個極小極小的宇宙。
“他造的屋子,實際上已經被這個宇宙佔領,他隨便砸開一堵牆,都會看見星星,他嚇呆了。
“天下很快就太平了,他思鄉心切,準備回到河西,可那塊聖石卻再也帶不出那座屋子了。
“他終於回到了故鄉,他把聖石的事情告訴了他的族人,他的族人卻認爲是他弄丟了聖石而編造的荒唐故事。
“他被族長下令處死了,族中有一個跟他極要好的人相信他說的是真的,決定來這裏一探究竟。
“那個人發現僧人說的是對的,便寫了一封信,吩咐同來的人帶回部族,而他則住在附近,暗中守護着聖石。
“他娶了一個當地女子,準備世世代代守護聖石。他的後代,發現了屋子一百年毀一次。
“他的後代,一直同部族保持着聯繫,但明朝亡後,他的後代也消失不見了,很可能是在戰亂中都死光了。
“我們米家堡的人是當年米氏部族的唯一直系傳人,我們堡的歷代族長,都會背誦祖先的遺訓。
“我們祖先的遺訓中,有這麼一條:‘興復月氏,子孫永記!’我米建業,就是現任的族長。
“我是我們堡裏唯一的大學生,我最感興趣的科目就是物理和歷史。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興復大月氏!
“我反覆研究了關於那座屋子的資料,我終於明白了,那快聖石就是一個微型宇宙,一百年是它的生命週期。
“我製造了一臺機器,工作原理參照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如果能量足夠大,就能把人送回到過去。
“按照我的推算,今年那座屋子會倒,這時,是聖石能量最弱的時候,再過十五天,它就會恢復如初。
“我決定,把聖石跟屋子分離,直接放到我的機器上,我再用高能粒子激活它,讓它快速復原。
“聖石一旦跟我的機器合爲一體,那我們就可以拿着現代武器穿越時空去征服兩千年前的世界了!”
九、愛情可以使人變成魔鬼
米建業說完了,卡車也開始減慢速度,顯然是接近目的地了。
我和解毅一言不發,米珊珊和米天一也沉默不語,他們也許明白:他們的生命快走到盡頭了。
米建業嘆了一口氣,說:“一會兒,你們在廢墟中找到聖石,然後就割腕自殺。”
米珊珊劇烈地抖了一下。問道:“爲什麼我們非死不可?”
米建業無奈地說:“祖宗遺訓中說,要用處子的血祭聖石,我不能違背祖訓。”
我插言說:“祖宗的話也不見得都是對的,再說,即使你回到了過去,征服天下又豈是那麼容易?”
米建業用手捋了捋絡腮鬍,冷冷地說:“她不喜歡我,說我是可憐的瘋子,那我就偏要做出一番事業給她看!”
解毅望了望我,眼睛裏掠過了一絲希望的光芒。
他嘆了口氣,自言自語說:“她真蠢!居然看不出來你是一個偉大的天才!”
米建業突然像獅子一樣揪住解毅,大聲咆哮起來:“我不許你侮辱她!誰都不配侮辱她!她是神!”
風暴過後,他又恢復了平靜,呵呵一笑,說:“這世上居然還有人說我偉大!”
我言之鑿鑿地說:“你當然偉大,要不你的族人怎麼會推舉你當族長,你應該是最優秀的!”
米建業苦笑了一聲,說:“那是因爲我是我們堡裏唯一的大學生。”
他又接着說:“上大一時,我就喜歡上了她,可她嫌我是窮鄉僻壤來的,而她的父母都是北京的高幹。
“畢業後,我找了一份工作,意外地發了一筆大財,當我去找她時,她已經跟一個有錢人出國定居了。
“我兒時的夢想又燃燒起來,我要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好讓她看看!我是最優秀的!”
解毅笑着說:“你口口聲聲要讓她看看,你回到了兩千年前,而她在兩千年後,她看得見嗎?”
車停了,米建業冷笑着對我們說:“你們不要心存僥倖了,我會回來再帶她到兩千年前看看的。”
我們下車後,發現已經到了一個大院子,院子裏站着三四十個人,都全副武裝,一臉殺氣。
米建業用洪亮的聲音說:“大月氏的英雄們!再過半個小時,我們就可以和我們的祖先在一起了。”
我發現,我們又回到了鎮子裏,這個院子是歌舞團表演歌舞的地方。
我想大喊幾聲,但解毅用目光制止了我,因爲那三隻槍始終對着我們。
鎮子裏可真安靜啊!喧鬧了六七天的歌舞表演看來已經結束了。原來,這些人一直在借歌舞作掩護挖地道!
解毅突然問道:“毛明是怎麼死的?”米興邦冷冷地說:“是我用心臟共振儀幫他擺脫了痛苦。”
解毅憤怒地說:“你有什麼資格幫他擺脫痛苦?你這是不折不扣的謀殺!”
米興邦一邊看着那些人進入地道,一邊說:“幫忙也好,謀殺也好,總之,他應該去死。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脖子上掛着我們月氏人的銀牌時,我還以爲他是當年那僧人朋友的後代呢。”
很快,四十多人都進入了地道,院子裏只剩下米建業,米珊珊,米天一,解毅和我。
米珊珊在米建業威嚴的目光下,轉身走進了地道,地道口大約兩米高,一米寬,像一個地下車庫的入口。
我不由得讚歎:“你們真厲害!神不知鬼不覺,挖了這麼大一個地道!”
米建業幽幽地說:“所有的機器都是我設計的,如果她看到了,一定會對我刮目相看。你們不知道,當二十年前她對我不屑一顧、跟着那個該死的有錢人出國的時候,你們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十 、聖石
地道里一團漆黑,不時有一些轉彎,因爲彎度不大,倒不至於撞在土壁上。
解毅在我前面走着,米建業在我後面大約四五米處跟着,也許,他手裏有一把致命的手槍。
這段時間彷彿有一個世紀那麼漫長,沒有人說話,只聽得見細微的腳步聲。
忽然,米建業用一種嘲弄的口氣說:“如果你們不那麼聰明,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有時候聰明不是一件好事。”
他又彷彿在安慰我們,說:“聖石在滿月時威力最大,今天晚上不是滿月,你們也許不會瘋得有多厲害。”
我心裏百感交集,沒想到那座不起眼的老宅子竟隱藏了這麼大的祕密。
解毅在前面問道:“你說過聖石是有生命的,我們不去傷害它,它怎麼會讓我們瘋掉呢?”
這時,隊伍停住了,隨之,四面燈光齊亮,我發現我們走到了一間擺滿機器的大房間裏。
米興邦把兩把鐵鍬塞到我和解毅手裏,衝米珊珊和米天一說:“你們帶他倆上去找聖石。”
原來,我們就在那座倒塌的老宅子下面!
米建業開始和十來個人組裝那些機器。機器上佈滿透明的玻璃管道,模樣很怪異。
米興邦不耐煩地踢了我和解毅一腳,喝道:“快上去找聖石,不然就打死你們!”
解毅開口問道:“雞蛋呢?”
米建國冷笑了一聲:“沒你們兩個人的雞蛋,你們不發瘋,我們怎麼會找到聖石?”
我欲言又止,看看解毅,又看看周圍的這羣瘋子,無可奈何地沿着一個梯道往上走。
這時,米建業一揮手,除了我們四個,其餘的人都含上了雞蛋。
到了上面,我才發現,那三個持槍人也跟了上來,看來,我們今天是在劫難逃了!
我用鐵鍬撥弄着碎磚亂瓦,心撲通撲通跳得厲害,呼吸也困難起來。
米珊珊和米天一各執一柄雪亮的尖刀,麻木地看着我們。他們準備要用鮮血祭那塊聖石了。
突然,解毅的鐵鍬碰到了一團東西,藉着微弱的月光,可以看清是一塊橢圓形的石頭!
這難道就是聖石?可……可……可解毅並沒有發瘋。
解毅拿起那塊石頭,掂了掂輕重,自言自語道:“難道是我早上喝的那杯茶?”
我心念一動,對了,縣誌上說,當年番僧曾給縣知事泡奇茶,那我們早上在檔案館喝的茶莫非就是那奇茶?
三個持槍人見我們沒有異狀,催促說:“不是那塊石頭,扔掉!接着找!”
突然,那塊石頭動了一下,解毅手一抖,那塊石頭便飄到了地上。
只見它先是飄到米珊珊面前,彷彿在端詳她,隨即又飄到米天一面前,米天一用手去摸它,它卻靈巧地躲開了。
它像長了眼睛一般,徑直飄向了三個持槍人,馬上,它從我們出來的地方飄了進去。
三個持槍人的臉上滿是驚訝和恐怖的表情,忽然,他們發瘋般地大喊大叫起來。
幾乎在同時,廢墟下面也傳來了紛亂的驚叫聲和撞擊聲,還有幾下悶悶的槍聲。
米珊珊和米天一扔掉了尖刀,像兩尊塑像般站在那裏一動不動。
我詫異地問:“難道雞蛋不管用嗎?”米珊珊冷冷地說:“只有生雞蛋管用。”
米天一問道:“珊姐,是你把生雞蛋都換成熟雞蛋了?”米珊珊一言未發,只是深吸了一口氣。
後記
當夜,縣公安局接到我的報警電話,把那些瘋子都送進了附近的瘋人院,米建業在瘋狂中開槍自殺。
米珊珊和米天一當時就走了,我和解毅問他們去哪兒?他們就說了兩個字:“回家。”
我發現米珊珊懷裏捧着一塊石頭,看來,那塊聖石也要跟着他們回家了。
第二天,那堆廢墟復原好的地方重又坍塌,而且,一直都那樣,再沒復原過。
我和解毅抽空拜訪了一下他的老同學,縣檔案館劉館長。
劉館長很熱情,泡了一大壺那種味道怪怪的茶,並說,這茶的配方是他家世代相傳的,能辟邪氣。
解毅問他祖籍何處,劉館長笑着說:“老同學,你恐怕不知道吧,我祖先好像不是漢族人呢。”
我和解毅對視一笑,解毅打趣說:“你的祖先恐怕姓米吧。”劉館長很驚詫:“我就姓米。”
現在輪到解毅一臉驚詫了,劉館長解釋說:“從我祖父那輩起隨了姥姥家姓,就一直姓劉了。”
別說在舊社會,即使在現代,隨母親姓的也不新鮮。解毅點了點頭,表示明白了。
劉館長突然問道:“解毅,聽說你們鎮上出事了,是嗎?那羣人怎麼會都瘋了呢?”
解毅反問他:“大劉,你說宇宙有生命嗎?”
劉館長笑着說:“怎麼會沒有呢?就說地球吧,別看它不聲不響,它就有生命。你看,它嚴格地自轉,還繞着太陽轉,而且億萬年裏,它一次又一次躲過了小行星的撞擊。如果把地球當成一個動物的話,我們只不過是附着在它身上的真菌或細菌罷了。……對了解毅,你不要打岔,你們鎮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些人究竟是怎麼瘋的?”
解毅笑了笑,說:“你再回答我一個問題。你說宇宙有生命嗎?”
劉館長捶瞭解毅一下,說:“還是那老毛病,喜歡賣關子。宇宙當然也有了。我們是地球的細菌,地球是宇宙的細菌,宇宙……呵呵,我也賣一個關子。宇宙是我們的細菌,世界就是這樣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反覆不斷地循環的。”
從縣檔案館出來,我問解毅:“你爲什麼沒告訴劉館長全部真相呢?”因爲在剛纔,解毅說那些人是寧夏人,想找寶貝,結果中了老宅子的毒氣而發瘋。
解毅回答:“你說米建業活得累嗎?他僅僅是爲了現代的一次受挫折的愛情。你說米珊珊和米天一活得累嗎?爲了部族一個古代遺訓差點送命。所以,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THE END
附錄:替網友尋人:
我叫張凱,河北省唐山市灤縣古馬鎮包麻子村人。我想尋找我繼奶奶,以及和我父親張志遠同父異母的叔叔。繼奶奶大約是1940年和爺爺張丙周結婚的,只知道她是樂亭縣人汀流河一帶的,姓張,那時大約三十歲上下。爺爺是四二年區小隊在灤縣前常峪村開會時,因漢奸告密被鬼子包圍,在掩護戰友突圍時犧牲的,同時犧牲的還有顧順田、黃作周丶董振邦等,當時的區長叫澤文剛。爺爺犧牲後,奶奶就走了,走時懷着孕。大約是四九年時村裏支前的擔架隊曾有人見過她,還有當年才六、七歲的叔叔。那時她是解放軍東北軍(四野),入關來解放平津路過灤縣。算來奶奶應年近百歲,叔叔應在七十多歲。盼幫助尋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