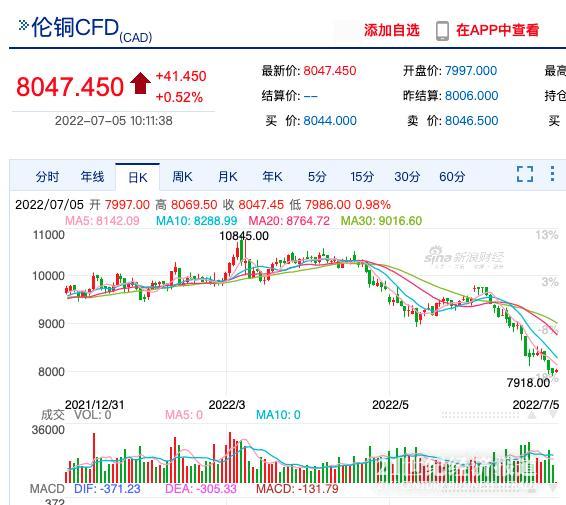三个月内两人死亡,中国学员质疑美国航校种族歧视、飞机老化
摘要:2011年12月,还是USAG,还是丹顿校区,一架搭载两名中国学员、一名外籍教员的飞机,在进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坠机事件发生后,邱裕所在的南航发表声明称,USAG已暂停中国学员全部飞行训练,并对学员进行心理疏导。
航校飞机老化坠毁 中国学员当场身亡
文章摘要:美国航空学院是经中国民航局认证的国外航校,培养了大约2000名中国飞行员。4月16日,中国飞行学员颜洋在宿舍自缢。三个月后,还是这家航校,一架飞机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机上一名中国飞行员与航校教员不幸罹难。接连发生的两起事故,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这所航校的黑匣子。
有种情绪正在教室里蔓延。
一位学员班长站了起来,“我已经向公司申请,自愿停飞,回中国。请现在就让我走。”话音未落,他摘下领口班长特有的星星领章,朝地上一摔,转身离开了教室。
这一天是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航空学院丹顿校区召开了一场全校会议,讨论头一天该校发生的那起事故。
7月28日下午5时,一架从丹顿起飞的训练飞机,本应在这个时间,降落在盖恩斯维尔市立机场宽阔的18号跑道。但在机场跑道以东四分之一英里外,飞机以倾斜的姿势砸向地面,旋即起火,爆炸,碎成一堆破铜烂铁。机上搭载的两位年轻人——22岁的中国学员邱裕、意大利女教员Francesca皆不幸身亡。
中国学员后来发现,失事前一周,该飞机至少三次被报告存在机械故障。这成为会议上大家质疑的焦点。
王宇也在会场。听着校方不停推卸责任,大家陷入沉默。那位学员班长起身质疑后,教室里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挺佩服他的”,王宇感慨。学长邱裕坠机后,他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晚,头一沾枕头,噩梦就在脑袋里盘旋。梦里,因为各种原因,他遭到枪杀,然后从梦里惊醒。
这已经是他目睹的第二起中国学员非正常死亡。三个月前。4月16日凌晨6点,另一个学长颜洋,在卫生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遗书。中国学员普遍认为,航校一直存在的“歧视”“压迫”“刁难”,推着颜洋走上绝路。
“已经没有人相信它能安全地飞下去”,王宇说。这所老牌航校,培养中国飞行员已超10年,送出了大约2000名中国毕业生。但眼下,它被质疑在飞行安全与管理上存在诸多疏漏。“短短三个月内,连续发生了两桩命案,大家已经失去信心了。”王宇想起颜洋葬礼上,中国学员悼念时使用的一个词——无尽的深渊。
这些年轻人本应身穿笔挺制服,坐在驾驶舱,操控飞机向天空深处爬升。而现在,USAG就像一架失控的飞机,连同被困在机舱里的中国学员,朝深渊俯冲。
两个中国学员之死
邱裕出事那天的傍晚,王宇正在回学生公寓的路上,一位同学告诉他,两小时前,邱裕坠机了。
王宇愣了一下。头天晚上,欢送一位顺利完成学业的师兄,王宇还与邱裕碰了面。当时,他一把握住邱裕的手,说了句,“师兄啊,加油啊,挺住。”王宇知道,那段时间,邱裕飞得不太顺,吃了一张罚单。没想到,“第二天,他人就不在了。”
在他的记忆里,邱裕成熟,话不多,但也开朗。他来自广州,是家中独子,父亲是一名木工,母亲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发廊,父母均为聋哑人士。王宇事后才听说,邱裕有女朋友,谈了八年,他打算拿到飞行执照,再回国与女友完婚。
坠机消息传回学校时,张林拒绝相信。邱裕比他早来几个月,算是他学长。一次,张林飞模拟机遇到故障,向邱裕请教,邱裕不厌其烦地为他讲解。当时,邱裕乘坐的校车即将发车,错过这趟,需要再等一小时。张林提醒他,邱裕反而宽慰,“没关系,我可以教完你再回去。”
“特别谦和,也很认真,学习上刻苦。”张林评价邱裕。现在,他失去了“热心”的学长,也失去了“温柔”的老师——同机坠亡的女教员。坠机前两天,她还鼓励他,“我觉得你可以,你足够好,我相信你,因为你是我的学生。”
冷静下来后,张林与几位同学聚在公寓,打开电脑,开始查询事发时的天气、交通状况,飞机维护记录、故障报修记录,试图找到坠机原因。五六个小时后,结果慢慢浮现。
学校官网里的故障报修记录显示:
7月20日,飞机被报告为,左边发动机转速不稳定。
7月24日,飞机又被报告,左边发动机在着陆后失效。
7月25日,再次被报告为,起飞后,起落架收不上去,左发动机着陆后失效。此次报告,由后来坠机的女教员提交。
但在官网上,几次故障报告都被关闭了,“意思是,有人来检修了,确认了故障,并且修好。”张林解释。
28日,再次分到这架飞机,女教员还专门找签派员反映,“这架飞机左发和起落架有故障,能不能换一架”。张林的一位同学当时刚好在场,他听到签派回答,“不行”。
14时40分,飞机发动。只是这次,她已经没有机会在降落后,再次报告故障。
USAG的飞机“带病飞行”,已不是第一次。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飞行时通讯出现故障,失去与地面联系;飞着飞着机舱门自动打开,学员再伸手把它关上——“习以为常了已经”,张林说。USAG的飞机平均机龄接近50年,而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机的平均机龄不超过二十年。“机龄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机龄越高,越需要高水准的维护和保养,学校显然没有做到。”张林说。
8月8日,邱裕父母出发前往USAG,启程前,他们录制了一支三分钟视频。视频里,他们坐在床前,杨母双手捧着邱裕遗照,杨父用手语讲述家里概况。王宇在公寓区远远看见了他们的身影,但没有上前打招呼。几天前,坠机教员的葬礼在当地举行,他也没去。三个月前,他刚刚参加了一场葬礼,怕自己承受不了。
4月16日凌晨6点,中国学员颜洋悄悄挪进卫生间,将门反锁,在两三平米的狭小空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遗书。他才22岁,来自江苏淮安,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技术专业2015级学生。一年前,他与深圳航空公司签约,由公司提供学费,到USAG进行飞行训练。
王宇比颜洋晚到一个月,很早便耳闻颜洋在学校的遭遇——多次遭受航校歧视、刁难。但颜洋很少抱怨,同学记忆里的他,总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看《家有儿女》《非诚勿扰》,笑着和大家分享零食。王宇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校区回宿舍的大巴上,颜洋正与同学打闹,脸上挂着笑。
葬礼在达拉斯举行。去往殡仪馆的大巴上,王宇靠在座椅上,闭着眼,他很愧疚,“感觉在学校没能多帮帮他”。窗外,乌云堆积,天空压得很低,他心里更堵得慌了。
颜洋的室友则陷入了更深的自责。葬礼上,他责怪自己,“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鼓励你走下去,你赶紧回去算了,退学回去得了,转专业不行吗?”王宇坐在后排,眼泪顶不住夺眶而出。他记得颜洋室友抽泣着说,“你今天应该在中国,至少还活着,我还能再见你一面。”
校方代表也到场,作了简短发言,没有道歉,没有追责。“特别官腔”,王宇听得很气愤,双手不自觉攥在一起,那会儿,他便意识到,航校管理层若不做出改变,意外不可避免。
三个月后,他又失去了另一个朋友。

No Chinese
一年前,王宇带着期待,坐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他与同批次的十几位同学,飞行十几小时,抵达芝加哥,又转机来到达拉斯,这是美国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距离USAG60公里。航班延误,他们等了近五小时,落地时,已近凌晨。
来美国前,他们经历了体检、心理测试、政审、英语考试等多轮严苛的选拔。现在,陌生的世界徐徐打开,顾不得疲惫,他们吃了当地汉堡,逛了沃尔玛,回到公寓已凌晨两点多。王宇穿过一扇铁门,目光越过草坪,视线终点那幢二层建筑便是他们的住所。棕色外墙、灰色尖顶,浸在红、白色夜灯里,乍一看,像美国当地的“旅馆”。
邱裕比他早几个月入住这片公寓。没课的时候,男生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做饭,吃火锅。
王宇喜欢在地图上搜索附近好玩的地方。为看一场电影,39度的高温,男生们顶着烈日,沿高速公路旁的草地走了四十分钟。他们还会去周边大学参观,走累了,坐食堂里喝杯咖啡。节庆日,还随当地人去观赏烟花。出于安全考虑,学校不许他们打车,于是,每两周,乘学校班车去三十公里外的亚洲超市购物,成了男生们放松的方式之一。
学业安排也很紧凑。前五周,早六点至下午四点半,王宇都得去学校进行语言培训。回到公寓,完成作业,一般就晚上七八点了。之后分配教员,学习飞行,飞行时间、时数全听教员安排。
新鲜感没能维持太久,王宇就发现了学校的一些异样。
入学两个月后,他在官网查询考试安排,发现考试名单将在校学生分为了三类:Domestic 、international、Chinese。王宇一愣,为什么把中国学员单列一栏?
USAG丹顿校区共有200多名学员,中国学生占大多数。中国学员几乎都是公费培养,由航空公司或航校垫付学费和生活费,拿到执照后,再进入公司工作。他们听从航司安排,无权选择航校、教员。
每家航空公司都有一定比例的“停飞率”,淘汰权掌握在航校手里,在USAG,王宇说,吃到三张罚单,便会面临停飞,无法拿到执照,还要面临航空公司的索赔。而本土学生、国际生大多自费,拥有更高的自主权、优先权。
也是如此,本土生、国际生可以任意“插队”。USAG考试日期通过邮件发送,一般提前两天,中国学生头一天收到考试安排,第二天再登陆邮箱,里面可能又躺了一封“取消考试”的邮件,一查,替换成了某位本土生或国际生。“大家多多少少都遇到过被插队的现象”,王宇说,最长的一次,他等了一周,才重新安排上考试。
尽管中国学生占多数,但航校不许说中文,不少角落都贴着“NO Chinese”的警告牌。
有一回,学员刘靖坐在教室,拿着IPAD看飞行视频。一位教员径直走到身边,罚他做了几十个俯卧撑,做完起身,教员告诉他原因:坐在他身旁的两位同学一直用中文交流,刘靖没有制止,负连带责任。
在刘靖一年的USAG经验里,说中文,意味着罚款、写检讨、做俯卧撑。惩处方式甚至包括,中国学员手持一张A4纸,靠墙而站,像嫌犯一样拍照,照片还要贴在教学楼的一面展板上。A4 纸上写着:I don’t speak English like I am supposed to。
“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柬埔寨人,欧洲人,他们讲母语没有任何惩罚”,刘靖在规定里感受到了“歧视”。尽管,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大家练习英文。但学员们认为,可以接受全员“Speak English ”,但不能是“NO Chinese”。

怨气在积累,但没人敢说什么,毕竟学校握有飞行“生杀”的大权。直至4月16日凌晨,颜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头一晚,他还做了值日,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调上闹钟。他在凌晨六点醒来,悄悄走进了卫生间。
刘靖不敢相信。两天前,他还与颜洋吃了饭,颜洋跟以往一样,话不多,但爱笑。
颜洋离世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打破了USAG的宁静。
几天后,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工作人员召集中国学员开了一次会,了解大家在USAG的生活状态。会上,一位同学自述,他因飞行时犯了错,航校一位经理叫他去办公室,勒令他“像狗一样地趴在门口”,教工和学生出入,从他背上跨过。另一些被惩罚的学员,航校为他们安排了“daily schedule”,要求他们“清晨擦洗飞机”“夜间打扫厕所”。刘靖身边不止一位同学经历了这些事。
中国学员的控诉还包括,训练进度严重滞后。颜洋在USAG待了一年,中间只有两三个月正常飞行,仍处于私照阶段——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便能考完的初级训练阶段。
在USAG,收到三张惩罚单,便会面临停飞,意味着飞行生涯结束。
刘靖的一位同学,因生病收到了惩罚单。“难道民航局规定飞行员不能生病?”学员们不解。
颜洋也多次收到惩罚单。离世当天,私照经理本来安排了一次会面,“一般见这个人的话,就是发停飞警告单”,王宇猜测,颜洋可能提前听到了风声,会面前几个小时,用另一种方式选择了回避。
“那个时候,第一次有了强烈的退飞的感觉。”刘靖在社交媒体写道,他偷偷哭过好几次,睡不好,闭上眼就是颜洋的笑脸。最后一次见面,他还问过颜洋,“最近飞得怎么样?”
“就那样呗,你也不是不知道。”颜洋说,飞得好,就可以正常训练,解脱了。
“飞得不好呢?”刘靖记不清自己是否问出了这句话,但颜洋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脑海里都漂浮着一个回答。
“飞不好那就死呗”。

一种商品
USAG隶属于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声称是“全美十大航空学院之一”,“致力为全球客户提供世界级的专业飞行训练”。2008年,USAG获得国家民航总局认证,开始招收中国学员,至今培养了大约2000名中国毕业生。
但它不是第一次出事了。2011年12月,还是USAG,还是丹顿校区,一架搭载两名中国学员、一名外籍教员的飞机,在进行飞行训练时坠毁。中国学员一死一伤。USAG发表声明称,“校方和FAA会配合调查事故原因”。
发生事故的也不止USAG航校一家。2018年5月,美国圣地亚哥某航校一架教练飞机失事,机上两名飞行员与一名教练遇难,三人均为中国公民。
中国学员海外遇难事件频发,但国内航司并未放缓每年大批量输出飞行学员的速度。“公共运输航空每年大约需要6000名飞行员,由于缺乏培训设备、设施,国内每年仅能培训3000左右飞行员,剩下的飞行员只能送出国。”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负责人葛志斌早年接受采访时说。
在航空业发达的美国,大大小小的航校共1000多所,但能够接收中国学员的航校并不多,“必须是中国民航局认可的141部航校”,美国一所航校的高管罗放介绍,目前,具有民航局CCAR-141部合格证的飞行学校仅69家,国内34家,境外35家,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USAG就是其中之一。
在指定的这几十所航校里,能分配到什么样的教员,全凭运气。
在美国,航校教员多是兼职,时薪仅二十多美元。“为什么教员工资这么低,还有人干呢?因为他要积累小时数,美国民航局规定,要满足1500个飞行小时,才能去航空公司工作。”罗放解释。
他运营的航校,曾有一位教员,一到夏天,就开着皮卡来学校。皮卡后座拉着除草工具,教完飞行,他就回地里,推着机器给人割草去。“因为教开飞机,一个小时25块钱,割草不论小时,论片,一小时给五家割了,他能挣二百美金。”
罗放见过一所航校,四位教员,两位是非法移民,学生多的时候,一位教员能带九个学生,但民航局规定的教员学生比例为1:6。而在加州,一所航校教官与助理曾合谋绑架一名中国学生,试图将他遣返回国。原因是不满中国学生英语差劲。
“说白了,我们在那里根本没有人权”,贺小将公费培养的中国学员比喻为商品,“公司、学校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而已。”
2018年5月,贺小在网络发布《国外航校乱象丛生》一文,分享了他在美国的经历。
一年前,贺小以国内某航空公司委培生的身份来到美国猎鹰航校培训,不出意外,十五六个月后,他将拿到执照,回国,成为一名飞行员。但第十四个月,航校没给学生续签,在移民局的抽查中,贺小被抽中了。
2018年1月31日,上午九点前后,贺小在宿舍为飞行做准备,四位警察推门而入。
“出示一下护照”,警察要求。
贺小拿不出来。刚到美国,公司要求他们同批35名中国学员上缴护照,由航校统一保管,理由是“不想让我们在美国乱跑”,贺小回忆。
他们办理的是M1学生签证,于2017年11月到期。临近超期,学员多次找到航校、公司反应,希望航校尽快续签,得到的答复皆是“这是航校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
警察以“非法滞留”的罪名将贺小铐走。他被投入了当地的移民监。监室很小,一张洗手台,一个马桶,上下铺各睡一人,唯一的窗户悬在上方,很高很高,带着铁栅栏,关着来自非洲、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
贺小有些害怕。他哭了,一直在抖。一位来自非洲人的陌生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他们告诉他,“最好能有一位律师,他会协助你,尽快离开。”
关押七十天后,贺小在父母聘请的律师帮助下,申请自愿离境。“这样有一个好处,不会受到再次入境的限制,但还是产生了一个黑记录。” 2018年4月,回到国内,他准备与父母一道,去上海向公司解释。启程前,父亲接到了公司电话,贺小被单方面停飞了。
按照民航局规定,停飞后,贺小不能再继续完成后续训练,他降了两级,转了专业,能否再做飞行员,还是一个未知数。

陷入迷茫
坠机事件发生后,邱裕所在的南航发表声明称,USAG已暂停中国学员全部飞行训练,并对学员进行心理疏导。但次日,航校召开全校会议,领导发表讲话,“今天一天是为了悼念我们已逝的两位朋友,从明天早晨六点,希望大家开始正常飞行”。
质疑声此起彼伏,领导不得已松口,“那么,明天我们从中午十二点再开始恢复训练。”王宇回忆。
大多学员选择拒飞,一位中国学员班长直接申请停飞。王宇也考虑过停飞,“如果航校连安全都无法保障,我还是情愿换个地方,继续生活。没必要在这边赌上自己的一条性命。”但他也纠结,停飞回国,意味着毁约,面临高额赔偿,还得转专业,从头学起。他已在飞行上花费四五年,回到原点,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承担得起。
恐慌也落在国内待飞学员身上。一位中国学员即将迎来USAG面试,“真的让我很慌啊”,他在社交平台抱怨。一位家长,孩子已通过体检,现在陷入纠结,“看看这个,我都想让他放弃。”更多的声音呼吁中国民用航空局加强监管,尽早调查。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你没有实时监管它。”这几年,罗放见过不少监管漏洞下的乱象。一家航校,民航局要求配备十架飞机,十五位教员,他只有五架飞机,六名教员。检查当天,航校从外面租来五架,检查完又恢复原样。另一家,库存飞机坏了,仅一架能正常飞行,上百学生排队等那一架学飞。
“民航局通常做法是一年过来一两次检查,那么你知道,领导过来了,检查一天两天,这一天两天我做好就可以了呗。”罗放见识过最快的检查是,“两天检查三家”。
“那是门生意,生意就有利润。利润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能多赚一分,没有人少赚一分。”罗放感慨,“在几千万美金的生意面前,一条生命真的很脆弱。”
王宇也体会到了这份脆弱。颜洋离世的第六天,航校司机领队在司机与所有学员班长的群聊里,发了一条信息。大意是说,为感谢班长对事件调查的配合,航校为他们提供一次去游乐园免费游玩的机会。群里一片沉默。
“颜洋才出事,学校就组织活动,让我们去玩,大家都没法接受。”王宇说。
“说实话,很迷茫。”王宇喜欢飞行。他享受飞机穿云而过,靠在座椅上,欣赏云朵与蓝天分明的界线。他喜欢看夕阳,训练安排在傍晚,他就驾驶飞机,一直往西边飞,俯瞰太阳从天空落到地平线下,见证白日与夜晚交接。
他的朋友圈,还保留着一条状态。那是去年夏天,丹顿的地面温度高达43度,胳膊肘碰到被太阳暴晒的安全带扣,都能烫出水泡。但王宇很兴奋,他顾不上热,一头钻进飞机,坐在驾驶舱,看舱外的飞机起落,天空变幻。那是他第一次摸到“真机”。那时候,他的愿望很简单,完成训练,回国,做一名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