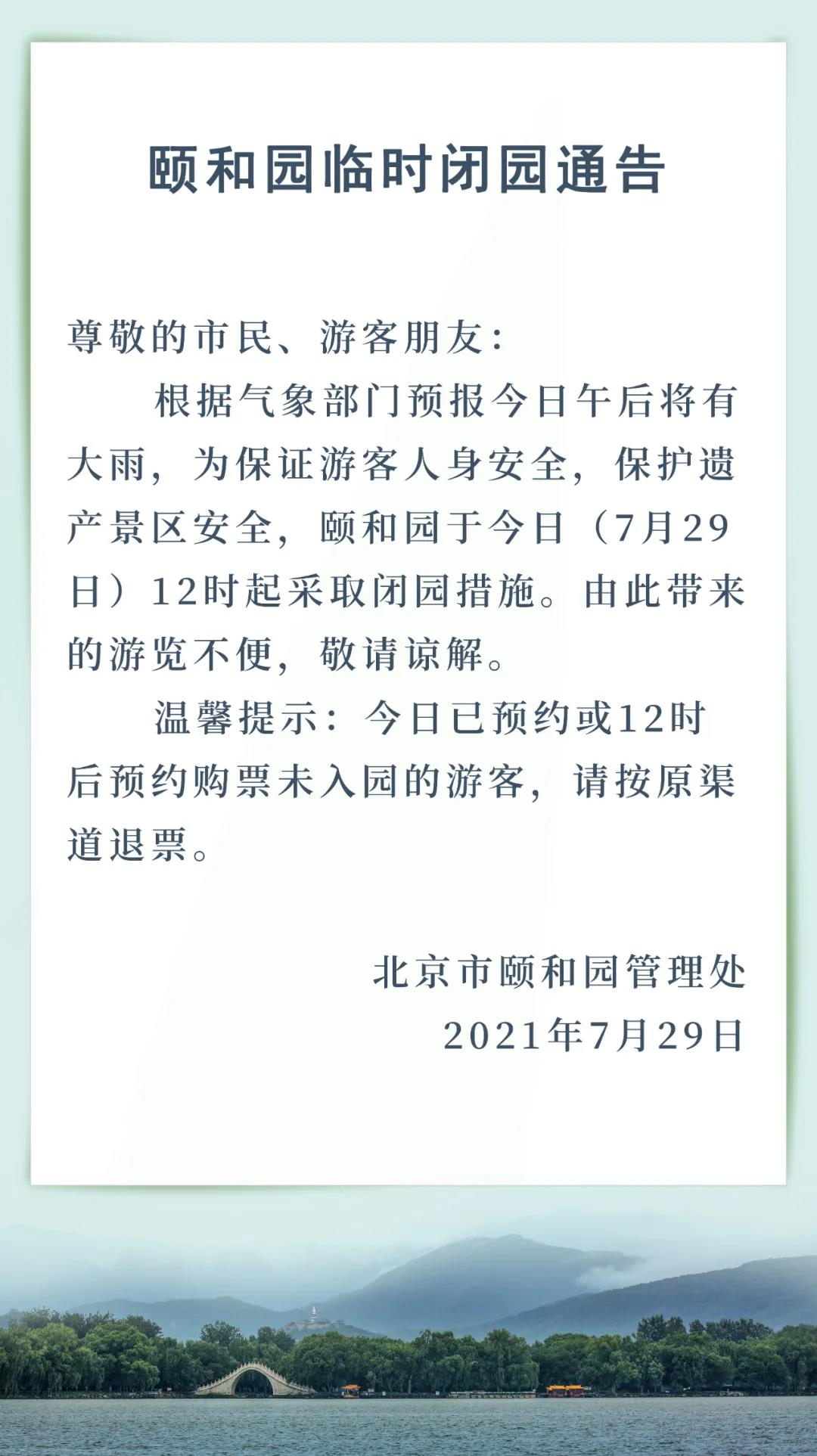93年前的今天,“一介書生”王國維投湖自殺
摘要:有人說在王國維之死中看到自由,沒有人可以再侮辱他,有人說在王國維的自殺中看到奴役,附着在自殺之上的任何宏大意義都顯得荒誕。有人在王國維之死中看到自由,死亡之後,沒有人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再奴役他再侮辱他。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
“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這是阿爾貝·加繆說過的一句話,在他看來,判斷生活是否值得過本身,便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
死亡是那樣容易,但生命的思慮卻常常很沉重。
“口鼻塞滿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跡,世界寂靜悠遠,沒有任何聲息。”研究王國維的學者周寧是這樣來形容他離開時的畫面。王國維本人連自殺的原因都不屑於解釋,只是檢驗官在他衣袋裏發現一份簡單的遺書,開頭有16個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那是怎樣的“時變”?怎樣的“義”?
93年了。回顧如今存在於各種文獻中的王國維,那一天,他以一種頗顯淒涼卻又可能是最嚴肅的方式,在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死去,而此後被各個時代記起。有人說在王國維之死中看到自由,沒有人可以再侮辱他,有人說在王國維的自殺中看到奴役,附着在自殺之上的任何宏大意義都顯得荒誕。只是在他自己的理解和認同中,彼時彼刻的死亡或許是與其心中秉承的道義最相契的結果。
以下內容經商務印書館授權,整合自《人間草木》第四章。
《人間草木》,周寧著,商務印書館,2009年10月。
原文作者|周寧
他的死是一個謎:“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陳丹青油畫“(清華)國學研究院”局部,左起第三爲王國維。
1927年6月2日上午,還有兩天就是那年的端午節。頤和園的園丁聽到幾丈外一聲水響,剛纔還在魚藻軒獨自抽菸的老者,轉眼間跳入湖中。園丁急忙趕來將人救起,僅幾分鐘,竟去了一條命。湖水很淺,王國維被水下的淤泥堵塞了口鼻,瞬間窒息身亡。
死亡是如此容易。車伕還在頤和園門口等他出來,家人還在家中等他回去,可他作爲陌生人,已經全無知覺地匍匐在昆明湖邊,口鼻塞滿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跡,世界寂靜悠遠,沒有任何聲息。檢驗官在他衣袋裏發現一份簡單的遺書,開頭16個字似乎說明死因: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僅此而已。
名人用死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並不鮮見,但王國維不一樣,他死得很輕鬆,甚至不屑說明自殺的原因。
死亡可能是沒有意義的,這是死者的立場。生者卻不同,他們無法忍受這種空曠的真實。王國維溘然長逝,他究竟爲何選擇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至今仍然是一個衆說紛紜的謎題。
孤立在夢境邊緣的鳥:寧靜的美好總是不堪一擊
1925年,王國維接受了清華學校的禮聘,此時,他名義上仍是溥儀的“南書房行走”,伴遜位天子讀古書。可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出走天津,“流亡”的那天,王國維隨駕出宮,“未敢稍離左右”。仁義深厚,也到此爲止。
離此人海,躲入書齋,天荒地老處與二三素心人商量學術,原本是閒適從容的。清華研究院待遇優渥,每月400大洋。奉旨入京之時風光無限,但他雖食朝廷俸祿,卻領不到實際的薪水,常常舉債度日。
在清華,王國維教授經學、小學、上古史,每週三個課時,其餘時間潛心於自己的研究,日子平靜而悠長。每天早晨起來,太太幫他梳理發辨,這是一天開始的沉靜莊重的儀式。有一次太太勸他剪去髮辮,他竟表現出少有的惱怒。那條纖細的發辨,是他身份、情感、理想的象徵。
王先生故去之後,學生們回憶當年課上,印象最深的細節是他每轉過身去,垂在腦後細長的髮辮在眼前輕輕掃過,與黑板上的殷墟文字一般悠遠而夢幻。
對於真正的學者,學術就是生活。除了從事研究、上課之外,在辦公室或家中接待來訪的學生,還有遠道而來的友人,一年後陳寅恪搬來清華園作鄰居,王國維有時去他那裏坐坐,隔一段時間總要進一次城,逛逛琉璃廠,淘古玩,訪舊書。
然而,這一切都是短暫脆弱的,幾乎讓人來不及品味,人像孤立在夢境邊緣的鳥,若有所思,片刻之後便驚飛了,劃破凝固的空氣。
這個世界的寧靜美好總是那麼脆弱、虛幻,不堪一擊。1926年中秋剛過,長子潛明在上海病逝,王國維痛惜萬分,短暫的好時光從此結束了。20年前莫氏夫人逝世,王國維悲痛難解,寫下許多悼亡詩,如今老年喪子,更是悲痛欲絕。一切遠未結束,半年之間,禍不單行。王國維準備“哀死寧生”,卻與多年至交、親家羅振玉失和,最終導致絕交。生命不僅是痛苦,還讓人受盡屈辱。
《王國維家事》,王長明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王國維長女王東明的百年追憶。
有所懼大於死
國維在歲末的沉鬱哀痛中度過50壽辰,陰鬱的1927年新年在北伐戰爭的鼓角聲中到來,哀痛中又加上了恐怖。北伐軍攻陷北京,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他們這些前清遺老,恐怕性命難保。
陳寅恪來訪,與王國維談起“中國人之殘酷”。一週之內,軍閥張作霖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釗
(1927年4月6日)
,革命黨處決了湖南大儒葉德輝(1927年4月11日)
。都是不祥的預兆,連梁啓超這樣的新派人物,也準備再次流亡日本。王國維絕望了,生的恐懼大於死的恐懼。
世界殘暴瘋狂,已經難以理喻。梁啓超邀請王國維同去日本避難,王國維拒絕。18年前曾與羅振玉一家流寓東瀛,他不想重複那種生活;陳寅恪勸他到城裏躲躲,他的回答簡單到“我不能走”;學生邀請他去山西避亂,他問:“沒有書,怎麼辦?”王國維謝絕了所有的好意,不是因爲他不能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走。此時,他感到恐懼與厭倦的,不是北京這一個地方,而是整個現世。
有所懼大於死者。王國維生路已絕,死意已決。清華園裏人心惶惶,1927年春季學期草草結束,計劃提前於6月1日正午開師生敘別會,然後放假,大家各奔東西。敘別會前一天,遺老朋友金梁來訪,“平居簡默”的王先生,那天竟“憂憤異常”。他們談話中說起頤和園,王國維感慨:“今日干淨土,惟此一灣水耳。”
塵世的最後一夜在平靜中睡過,早晨起來,一如既往。他坐到那裏,由太太梳理髮辮,似乎也沒有想過,這是在爲另一個世界束裝。八點鐘到研究院,商量下學期招生的事,然後便僱車去了頤和園。師友門生家人,沒有人在他身上看出任何異常。人生原本這樣,每一天都可以生,每一天都可以死。
最後的陽光下,王國維抽了一支菸,呼吸之間,煙火明滅,像他那脆弱敏感的生命。萬古恆常,短暫的一生不過像是這支紙菸。
隨即便是一聲水響,在寧靜安詳中,永遠消失。
不過是一介書生
王國維投湖那天是那年端午節前兩天,人們紛紛將他的死於屈原聯繫到一起。輕生死者重道義,這是中國的傳統,不過王國維倒從未表白自己的死與這位文化先賢有什麼因緣。
如果王國維之死若真與屈原之死有某種關聯或承繼,那麼,這個關聯點或承繼點,一定隱蔽在王國維精神深處。
三十歲前後,王國維經歷了人生的雙重轉型:一是學術上的,從西學轉入國學;二是生活上,從獨學轉入用世。朦朧中,他或許已意識到某種奇異的“宿命”,隱約暗示在他所著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中。
《王國維:一個人的書房》,王國維著,中國華僑出版社,2016年1月。
王國維說屈原一方面潔身自好,有所不爲,這是南人的超脫,另一方面又輾轉激憤,爲所不能爲,這是北人的執著。集南人北人品性於一身,無法既超脫又執著,糾纏不清,執拗不開,總是死路一條。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這是否也是他的“宿命”?
1908年,而立之年的王國維屑眷北上,開始了“南人作北人”之旅。本無心政治的他卻在因緣際會中與政治糾纏不清。
他經羅振玉舉薦入宮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實質至多是一名圖書管理員。辛亥革命後清室覆亡,王國維入了遺老行列。四年後從日本回來,王國維在上海憑自己的學問謀生,不料羅振玉又幫他謀得個“南書房行走”,再次入宮。
王國維既無明確的政治理想,更無自如的政治能力,無辜讓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種政治敗局中。王國維生平得羅振玉提攜,感恩常使他“失去自我”;尷尬的政治人生,多與羅振玉的“挾持”有關。馮玉祥逼宮,廢帝避難天津,王國維產生了莫名的“道義感”,竟與羅振玉等遺老相約投神武門御河殉清求死,後來被家人看住了,沒能成就“君辱臣死”的大節,卻入了遺老行列。他想象自己是個有操守、念舊情的人,君辱臣死,從此成爲他無法擺脫的噩夢。
說到頭來王國維不過是一介書生,書生本性註定的政治人生,一定是失敗而痛苦的。他是一個只有道德理想而沒有政治抱負的人,執着於理想,不肯苟合於社會。政治的污濁最終吞食了他的熱情,起初厭倦,終於絕望,溥儀出走天津,王國維並未隨行,多少算是解脫,但也並不輕鬆。
王國維當年看出屈子文學精神的內在分裂,卻看不出這種分裂必然導致一種文化以及一種“文化所化之人”精神分裂的悲劇結局。
王國維自沉之故,在個人人格的分裂,也在塑造這種人格的文化傳統的斷裂。在王國維身上,有屈子文學精神的宿命,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屈原與孔子,都生在一個敗落的時代,都代表一種理想化的道德立場,都以“生死抗爭”的方式試圖匡扶政治拯救世道,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儒家思想是烏托邦式的,這種烏托邦思想在歷史中被政治權利僞裝成意識形態,成爲似是而非的肯定現存秩序的思想。帝王政治與儒家理想之間本質上的對立被小心翼翼地掩蓋了,形成一種千年文化幻覺。在這種幻覺中,儒者自以爲可以通過爲帝王謀家國,實現個人的道德理想。可實際的下場是,或爲帝王豢養驅使的走狗,或爲帝王逼困拋棄的喪家犬。
只有人的道德,沒有非人的道德
王國維的死是完全的被動之死,死亡是一種逃避。
有人在王國維之死中看到自由,死亡之後,沒有人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再奴役他再侮辱他。
有人在王國維的自殺中看到奴役,自殺不是勇敢,而是懦弱,附着在自殺之上的任何宏大意義都顯得荒誕。
蘇格拉底臨終時說:“此刻,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處更好,只有神知道。”哲學家的態度似乎較爲開明,柏拉圖認爲不可責備那些因命運坎坷、受盡屈辱艱辛而自殺的人。休謨也是有條件地爲自殺辯護,人有權處置自己的生命。
但是,在尊重人、人性、自由精神的啓蒙哲學中,自殺是一種軟弱的犯罪。康德將倫理學的基礎建立在自由前提上,明確譴責自殺輕蔑存於人性中的人道。
在尊重人、人性、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前提下,理性的確很難爲自殺辯護。自殺可以以情感感動人心,卻不能以道理說服人腦。一個民族精神強大,不在心,而在腦。終日靠感動過日子的民族,心智上不成熟、意志上不堅定。
《王國維遺書》,王國維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8月。
王國維在一個失敗的時代死去,在無聊的時代又被記起。淺薄短暫的感動之後,人們沉不下心去深入思考他們實驗過的生死的意義。
當年梁啓超反對“以歐洲人的眼光去苛評亂解”王國維之死,“若以中國古代道德觀念去觀察,王先生的自殺是有意義的……”可是,所謂中國古代道德的意義是什麼?人生於危亂,憂民憂君,又無能爲力,“與其苟活,不如殉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氣節是有了,但真可以“以死救末俗”嗎?
自殺對個體生命是不負責任的,對社會道德與政治生活,未必也真負責任。真誠純正的君子們都殉了死節,最終的結局只是“地下太平”了,天下危亂依舊。這個世界會好嗎?
王國維的自殺,其意義可能是審美的,但未必是道德的,絕對不是政治的。人可能爲死亡之美所感動,但未必能從中獲得道德的振奮;即使能感到短暫的道德振奮,也未必能作用於政治實踐,進而改造社會創造歷史。
就此而言,加繆的立場或許更加值得讚賞,生活中孤獨、苦難、墮落、危險無處不在,死亡也隨時隨地發生,但我們始終要充滿開朗的激情,睜着眼看死亡與光明,讓激情中有熱愛、感激、信念、歡喜……
個人高尚勇敢的生存境界在“苦難與陽光”之間。
人,只有人的道德,沒有非人的道德;只有活的道德,沒有死的道德。思想是痛苦的,但思想是唯一的途徑,引領我們走出心靈之夜。
原文作者|周寧
整合|萬齋 西西
編輯|羅東
導語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