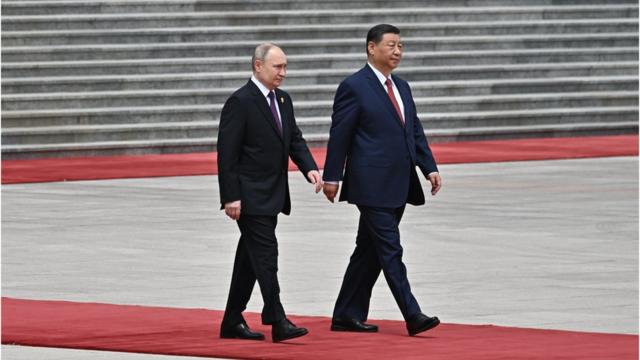假如納粹獲勝 世界版圖會變怎樣?
(原標題:假如納粹獲勝 世界版圖會怎樣?)
轉載自宏塵娛樂
[摘要]戴高樂的政治顧問科耶夫譏諷說,希特勒試圖在一切方面模仿拿破崙,卻忘記了時間已經過去了130年。在20世紀40年代追逐一種19世紀式的帝國藍圖,不過是那位奧地利畫匠的惡趣味罷了。
“一億日耳曼主宰民族將分佈在整個歐洲,確保他們統治地位的是(德國)對科學和技術的壟斷……充當奴隸勞工的其他民族將在體質和心智上加以人工的弱化,變成孱弱的文盲和半白癡。這樣,他們(德國人)就可以安然地享用帝國的建設成就——高速公路、‘通過快樂獲得力量’連鎖飯店、各地的黨總部大廈,以及巨大的軍事博物館和天文館……這將是一個屬於德意志的千年時代,甚至連人的想象力也將被鉗制在其中,無從逃脫。”
以上是英語世界最著名的德國史專家之一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筆下的“未曾發生的歷史”——納粹德國獲勝以後的歐洲。日後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曾以這一設定爲基礎,寫出了暢銷300萬冊的歷史架空小說《祖國》(Fatherland)。特雷弗-羅珀和哈里斯的立論大多是基於對《我的奮鬥》、《二十世紀的神話》等納粹理論著作及戰時德國文件的研讀,他們描繪的“勝利之後”德國的版圖也毫無二致:一個延伸到波羅的海、東歐與高加索的“更大的德意志帝國”,由一系列附庸國所環繞,滿足於將統治範圍侷限在歐洲。
哈里斯政治驚悚小說《祖國》中描繪的納粹獲勝之後的歐洲版圖。這一設定與“二戰”爆發前流行的地理政治學觀點極爲吻合。
弔詭的是,早在“二戰”爆發之前20年,就有兩個人預言了德國的擴張模式及其界限。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提出了“心臟地帶”這一概念,他把東歐這個擁有可觀勞動力、耕地及工礦資源的板塊視爲“心臟地帶”的核心,認定“誰統治了東歐,誰便能支配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能支配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便能支配整個世界”。德國坐擁雄厚的工業力量與軍事基礎,正是併吞東歐的有力競爭者。這一學說影響了一位退役德國陸軍少將,此人將麥金德的理論與19世紀末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基本設定結合起來,重新提出了“生存空間”這個僞達爾文主義概念以及基於種族劃分的“泛區域”。希特勒正是在這位將軍的教誨下,於《我的奮鬥》中申明瞭德國的擴張目標、種族政策與國際政治藍圖,並在1941年以“歐洲新秩序”的名義付諸實施。
換言之,納粹德國的空間擴張不僅是一種結果,甚至也出自必然:同時代的一切歐洲戰略家都認定,基於地理和技術原因,“東進”是使德國權勢在短期內最大化的最優路線;德國僅憑這一路線,便足以攫取世界性權勢(Weltmacht)。而德國的失敗,恰恰是由於他的對手在資源規模上遠遠超出了第三帝國的上限——兩個洲級國家,一個在外線提供工業產能和海上通道,另一個在內線提供海量人口和緩衝空間,這種結合足以使任何中等強國相形見絀。在歐洲控制全球的努力失敗之後,世界進入了美蘇兩極的時代。
德國控制下的歐洲版圖(1942年)。
“心臟地帶”與“生存空間”
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 Mackinder)的一生都在和主流意見“較勁”:1904年,當馬漢的“海權論”系列著作正在全世界受到追捧時,他卻發表了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直言位於歐亞大陸“樞紐地帶”的陸上強國正在剝奪海權國家的既有優勢。1919年,當凱恩斯在巴黎和會上勸說英法政治家承認德國的經濟重要性、並以復興德國作爲重建歐洲的關鍵時,麥金德卻把《歷史的地理樞紐》擴充成了小冊子《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極力渲染遏制德國的必要性。麥氏的論文和小冊子奠定了地理政治學(Geopolitics)的一般分析路徑和基礎性概念,由於他深信陸上強國在工業時代具備更大的權勢稟賦,從而和馬漢的“海權論”相對立,所以也被稱爲“陸權論”。
麥金德(1861-1947)的“陸權論”在20世紀產生了重大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他並不是一位刻板的地理決定論者。
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麥金德把位於歐亞大陸中心位置的那個由草原和沙漠構成的板塊——涵蓋了俄國的絕大部分疆域、蒙古、中亞及波斯——稱爲“樞紐地帶”(The Pivot Region)。在他看來,這裏三面爲山系所環繞,河流都流入內陸湖或北冰洋,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天然要塞,而爲海上武力無法企及。16世紀以前,這片廣袤而人煙稀少的地區一直爲各路遊牧民族所控制,他們憑藉馬和駱駝的機動性,對外圍的農耕地區做反覆的襲擾。只是在航海技術的發展開啓了“哥倫布時代”之後,西歐各國才得以憑藉強大的海上力量,迂迴到樞紐地帶邊緣的瀕海陸地建立起橋頭堡,將這股破壞性力量封禁起來達三百年之久。
不過到了20世紀初,伴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成果的擴散,樞紐地帶迎來了復興:那裏的巨量人口和戰略資源可能被某種集權體制組織起來,以創造出驚人的生產力。蓬勃發展的鐵路網不僅爲樞紐地帶強國提供了動員資源的工具,而且就像過去的馬和駱駝一樣,可以成爲進攻性的機動載具。當樞紐地帶完全控制了歐亞大陸、並開始建設遠洋艦隊時,“一個世界帝國就在望了”。
歸根到底,第二次工業革命改變了海洋和大陸之間的力量對比:當技術取代貿易成爲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強動力之後,那些在資源和人口方面具備突出優勢的陸上強國,自然也就比依賴貿易的海上強國能積累起更多的財富;鐵路網的擴張則在顛覆海洋交通的便利性的同時,爲陸上強國準備了對外侵略的通道。如果說當麥金德在1904年提出“樞紐地帶論”時,他所擔憂的還是俄國可能破壞歐亞大陸的均勢;那麼在經歷了四年殘酷的大戰之後,事情已經很清楚了:真正具備雄厚的技術基礎、且不滿足於既有國際地位的乃是德國。
於是,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對他十五年前的觀點作了修正,將“樞紐地帶”的範圍進一步擴大,稱之爲“心臟地帶”(The Heartland)。向南延伸的部分包含了中亞的山地和中國的新疆、西藏,海上力量對這一地區的政治變動很難做有效干預;向西擴展的部分則容納了整個黑海及波羅的海沿岸,當陸上國家足夠強大時,這兩片海域實際上只是封閉的內水。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易北河與亞得里亞海之間的東歐——這裏擁有成就一等強國所必需的勞動力、工礦資源和耕地,卻又處在德奧俄三大帝國的交界處,內部渙散分裂,極易被一個大國征服,而這個大國必將成爲歐亞大陸(世界島)霸權的最有力爭奪者。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將“樞紐地帶”的範圍擴展到了東歐,稱之爲“心臟地帶”,並暗示德國極有可能成爲新的歐洲霸權覬覦者。這一理論隨後得到了豪斯霍費爾的重視和接納。
然而在1919年時,只有戰敗者聽得進這樣的教誨: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剛剛以少將軍銜從帝國陸軍中退役,並在慕尼黑大學謀得一份教職。這位50歲的前軍人知識淵博、學養深厚,在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裏佔據了好幾個頁碼。從1911年起,他就致力於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研究。這涉及到一項奇特的誤解——今天中文語境中所謂的“地緣政治學”,本質上是麥金德開創的英美地理政治學(Geopolitics);它承認技術環境的變化會導致地理態勢之政治潛力的沉浮,並認爲在不主動變更國界的前提下,仍有可能通過外交手段調控海陸之間的權勢分佈。
而原初意義上的Geopolitik卻是一個混合了戰略地理學、德意志民族主義以及僞達爾文主義的“純日耳曼”概念,它的基礎假設包括:一個國家佔據的地理空間(Raum)不是由現存的國界所決定,而是與其民族天性以及在世界歷史中擔負的“使命”有關。正如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民族天性決定了他們將向海洋發展,從德國這塊“無水之地”發跡的條頓人註定要成爲歐亞大陸的主宰者。但德意志民族在當下尚未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只有在實現了經濟(尤其是糧食和戰略性原材料)的完全自給、人口的最大限度增長,國家纔有能力踐行其在世界歷史中的使命——唯一的選擇是驅逐那些“不配”佔據其疆域的劣等民族,爲日耳曼人取得大空間(Gro?raum),如此才合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而麥金德的小冊子,恰好給豪斯霍費爾提供了一種現成的參照:大空間必須擴展到那一界限,才能確保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間”。
卡爾·豪斯霍費爾(1869-1946)集軍人、學者、神祕主義者的三重身份於一身。起自19世紀末的德國地緣政治學流派,在他的努力下達到了新高度,並介入了實際政策的制訂。儘管豪斯霍費爾在1941年後已經與希特勒疏遠,但他在1945年仍被盟軍逮捕。爲避免被送上軍事法庭,豪斯霍費爾夫婦在拘留所服毒自盡。
德國的野蠻計劃:“歐洲新秩序”
1919年底,豪斯霍費爾指定一名學生擔任課程助理,此人是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未來的納粹黨二號人物。四年後,赫斯和希特勒因發動啤酒館政變被捕,關押在蘭茨貝格監獄。豪斯霍費爾給自己的學生送去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拉採爾的《政治地理學》,並利用探監的機會,對希特勒進行了一番地緣政治學啓蒙。這種“啓蒙”的成果,在1925年出版的納粹“聖經”《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希特勒不僅全盤照搬了“生存空間”的概念,而且把豪斯霍費爾設定的向東擴張的路線視爲德意志民族的出路。一種最初僅僅是紙上談兵的理論,經過陰錯陽差的演化,最終成了制定政策的準繩。
無論是基於海洋人視角的“心臟地帶”,還是純德國基因的“生存空間”,本質上都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體。說到底,德國人並不信賴亞當·斯密式的全球開放經濟空間及其背後的自由主義政體,他們推崇的是以民族國家爲單位和中心的“國民經濟學”。早在1830年代,這個學派的創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就爲一百年後的德國地緣政治學留下了龐大的思想遺產:權勢政治和貿易保護主義,重視鐵路在資源動員方面的作用,大陸擴張,必要的海外殖民……這種立足於充分自給、不依賴國際市場的論調,在剛剛被全球性大蕭條波及的德國尤其有市場。國民經濟學、地緣政治學和納粹種族主義的結合,共同塑造了第三帝國的經濟結構。
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指出:工業革命在歐洲的早熟造就了一個數量驚人的城市糧食消費者羣體,土地的有限意味着糧食供給只能通過國際市場來獲得,這顯然有悖於“生存空間”自給自足的初衷。爲了確保糧食供應,德國在1933年立法建立“世襲農場”,規定此種農場只能由血統純正的公民耕種,不可轉賣、亦不可挪作他用。農業從業人員被納入官方組織的“自治團”,不得改行,每年由國家下達生產指標、並以定價收購產品;城市青年也經常由國家強徵前往農村勞動,以彌補勞動力缺口。私人工商業同樣按類別組成自治團,工人則被納入“勞工陣線”(DAF)體系,接受國家管理,1936年後又將卡特爾置於國家控制之下,形成一種嚴格的計劃經濟。
爲減少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並避免馬克貶值,1936年以後德國原則上只以易貨貿易的方式從事商品進出口。對中南歐那些嚴重依賴德國市場的中小國家來說,他們不得不接受柏林的“經濟協調”指令,從而成爲“更大的德意志帝國”的定點生產基地:羅馬尼亞負責提供石油、木材、大豆和棉花,保加利亞提供肉類、水果和蔬菜,匈牙利則出口禽蛋。作爲交換,德國向這些國家提供農機、化肥、農藥和加工機械,但並不補償這些國家爲實現經濟調整而付出的代價。換言之,柏林關心的只是確保“主宰民族”的“生存空間”,對其他民族和國家(包括僕從國)則儘可能少地承擔義務,這也是1941年後納粹在歐洲控制區推行的“新秩序”(Neuordnung)的實質。
圖爲普洛耶什蒂的維加煉油廠。在戰爭的絕大部分時間裏,羅馬尼亞的普洛耶什蒂油田供給了德國軍事機器所需的燃料。在“歐洲新秩序”中,羅馬尼亞將繼續扮演石油、木材和農產品提供者的角色。
“新秩序”的領土安排以“生存空間”的初始假設爲憑據:盧森堡、阿爾薩斯-洛林、丹麥南部、比利時西部和但澤等存在德意志人聚居區的板塊直接“復歸”到帝國(Heim ins Reich),以爲德國的人口增長提供領土,當地的非德意志居民則以強制遷徙等手段加以驅逐。與帝國本土鄰接、但由非日耳曼人控制的地區,如斯洛伐克、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和克羅地亞,以保護國的形式加以統治。波羅的海沿岸、烏克蘭、白俄羅斯和高加索將成爲帝國的糧倉和油田,由德國駐軍實施軍事化管理,這些地區原有的工業設施或者被拆毀、或者由德國企業接收。名義上保持獨立的國家則按照德國經濟部長馮克(Walther Funk)的規劃,成爲柏林主導下的歐洲一體化經濟的一個部門:羅馬尼亞等多瑙河國家繼續扮演戰前的燃料和農產品提供者角色,並在德國的指導下開發礦藏;比利時、荷蘭和丹麥原有的工業體系由德國接收,大部分勞動力轉爲生產蔬菜、肉類、奶製品和深加工農產品。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負責向德國輸送礦石、木材、禽蛋和奶製品,被剝奪了工業產區的維希法國同樣將淪爲農產品和原料輸出國。
換言之,通過摧毀歐洲各國原有的經濟體系、並將其變爲從屬於德國的農產品和原材料供給者,柏林不僅最大限度地確保了自己的“生存空間”,而且使各國一旦脫離德國的政治控制就無法生存(因其工業製成品都須從德國進口)。全歐洲的貨幣政策同樣由德國支配,帝國馬克爲最高通貨,本幣的匯率取決於該國在歐洲一體化經濟中的生產業績;柏林通過一套多邊清算機制來調控歐洲內部的收支平衡,各國的黃金儲備則由德國代爲“保管”。據英國財政部估計,1940-44年德國從各佔領區掠奪的黃金儲備總價值超過5.5億美元,只有半數左右在戰後被索回。
在“新秩序”中,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Endl?sung)不僅是出於種族主義動機,也構成一種經濟手段。通過剝奪猶太人的財產權和公民權、並最終將其送入集中營,已經獲得的“生存空間”將爲德意志人獨佔。至於集中營,它既是一種執行強制收容和虐殺政策的警察機關,也是黨衛隊中央經濟與行政部(SS-WVHA)管轄下的經濟單位。猶太人在分批被送入毒氣室的同時,還須爲設在營區周邊的採石場、食品企業、皮革廠和出版公司充當軍工。黨衛軍甚至把“出租”猶太和斯拉夫奴工變成了一門生意:亨克爾、容克斯、梅塞施密特飛機公司,克虜伯軍工集團,法本化學康采恩以及西門子-舒克特電氣公司都在東方的集中營設立了生產車間,使用奴工。而法本公司正是滅絕營所用的“齊克隆B”毒氣的生產商——這無疑是20世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歷史之一。
奧斯維辛集中營第1營區入口處的著名標語——“勞動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在“新秩序”下,集中營成了榨取猶太人“剩餘價值”的經濟單位。
美蘇vs德日:“洲級大國”力壓“中等強國”
應當指出,納粹德國並未計劃從領土上侵佔整個歐亞大陸,亦不打算征服太平洋和美洲,這和第三帝國的單一民族特性有關。早在“一戰”爆發前,正在日本擔任武官的豪斯霍費爾就認定日本也是一個潛在的“主宰民族”,他們將在東亞大陸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並建成一個涵蓋了中國、印度、南洋諸島以及澳大利亞的獨立“大空間”。進入1930年代,美洲被認定是另一個“大空間”,它將由美國主導,控制權掌握在德裔移民及其支持者手中。德國對美日兩國的“大空間”甚少覬覦,而樂於接受三個“泛區域”(泛歐、泛亞、泛美)並存的狀況。因此,納粹的領土征服目標最遠只到非洲,也無意建立英國式的全球性多民族帝國。
對德國而言,雖然它通過支配歐洲實現了最大程度的經濟自主,但在燃料、橡膠、紡織品和稀有金屬方面仍存在缺口,需要從國際市場獲取;柏林也迫切希望把過剩的工業製品銷售到其他地區。由於三個“大空間”各由一個強國掌控,且自給程度較高,國際貿易也將按計劃模式進行:美日每年向歐洲輸入定額的戰略性原材料和農產品,換取歐洲的機械、光學器材和礦石。考慮到德國控制了全世界最富裕的單一市場,並且佔有某些至關重要的原料產地——以美國的物資進口狀況爲例,它急需的銻、錳和鋁幾乎全部來自德國控制區,橡膠、絲、鎢砂和錫則要從“泛亞區”輸入——它在這類貿易中必然不會喫虧。而美日企業若想打入歐洲市場,則須接受德國政府的“督導”。
1930年代豪斯霍費爾設想的四大“泛空間”。日後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將其進一步簡化爲“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
最奇特、也最矛盾的是對蘇聯的處置。包括豪斯霍費爾在內的所有德國地緣政治學者都認定,第三帝國與蘇聯結盟對雙方而言乃是最理想的選擇;在1930年代的設想裏,他甚至爲蘇聯也預留了一塊“大空間”。這兩個國家的結合將使“心臟地帶”連成一片,創造出無人能及的工業產能(這是麥金德最擔憂的情形);東歐將由蘇德兩國瓜分,德國以工業製成品和軍事技術交換蘇聯的石油、農產品和礦藏,蘇聯的遠東港口則爲德國提供破解海洋國家貿易封鎖的“後門”。1940年底,許多英國分析家在哀嘆:蘇德同盟對歐洲的統治將持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然而希特勒的“生存空間”焦慮和意識形態偏執否定了這種前景,他最終步拿破崙的後塵,發兵東侵。
從本質上說,拿破崙和希特勒的親俄都是在對抗海洋國家失敗之後,爲彌補經濟缺口而開啓的補償機制。在頒佈“大陸封鎖令”後,拿破崙法國無力爲歐陸國家提供替代產品,又不可能打破英國的海上封鎖,只能嘗試從俄國獲得補償。而希特勒在1940年夏天取得大勝之後,同樣面臨糧食和燃料短缺的問題:由於無法從國際市場獲得石油和食品,且戰爭影響了德國本身的農業生產,德國佔領的疆域最大之時,也是它的經濟負擔最重之時。唯有立即佔領東歐,獲得大量勞動力、耕地和燃料,才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內化解經濟壓力,最終實現自給自足。
希特勒似乎並無完全佔領蘇聯的野心:遙遠的亞洲領土對他來說缺乏吸引力;倘若不能使布爾什維克政權從內部崩潰,則將之驅趕到烏拉爾山以東、令其自生自滅即可。但他顯然低估了整件事情的難度。托克維爾在1835年就已斷言:“俄國和美國將各自主宰半個世界。”這不僅因爲兩國在地理上皆有屏障、難於被外部勢力徹底征服,更因爲它們在人口、幅員和資源方面超出了西歐國家一個數量級。如果把德、法這樣千萬級人口的西歐工業國家稱爲“中等強國”,則美國和俄國無疑屬於擁有大洲級體量的“洲級大國”。
爲運行自給自足、高度計劃性的控制型經濟,納粹通過各種行業協會和“自治團”對各個經濟部門實施垂直領導。圖爲1940年“德國勞工陣線”成員在進行軍事化訓練。
比較一下主要國家的人口、資源和工業產能,便可以窺見洲級大國的體量優勢。1940年德國總人口約7000萬,全年鋼產量爲2150萬噸,發電量630億千瓦時;尚未進入戰時狀態的美國的相應數字爲1.32億、6070萬噸和1780億千瓦時,技術上較爲落後的蘇聯爲1.7億、1830萬噸和480億千瓦時。換言之,已征服西歐的德國在鋼產量和發電量上只是稍微領先於剛剛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蘇聯,而後者的勞動力數量是德國無法企及的。從1940年到1944年,德國人殫精竭慮才把軍火產量提高了200%,而美國的軍工業規模膨脹了整整19倍。到1944年,美國的軍火年產量爲德國的2.5倍、日本的6.7倍,蘇聯的軍火產量也升至德國的90%。同一年,美國生產的飛機數量(96318架)相當於德國(40593架)的2.4倍,生產能力遭受巨大破壞的蘇聯由於得到英美提供的鋁材,也生產了40300架,與德國相當;而另一箇中等強國日本只生產了28180架。截至1945年8月,美國的戰時飛機產量爲德國的3倍,這還沒有計算提供給其他盟國的原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等強國甚至也無力逾越洲級大國的天然空間優勢。蘇德戰爭前半年,在兵員和機動裝備大體充足、且先發制人的情況下,僅僅由於地理空間過於廣大、環境和氣候不利,德軍就遭遇了驚人的消耗。從1941年6月到次年1月底,柏林在東線損失了整整94萬官兵、3000輛坦克、10萬輛汽車和2500架飛機,相當於蘇德開戰時陸軍總兵力的1/3。這足以證明即使是技術上具備優勢的中型武裝力量,也無力征服一個洲級大國。“大空間”的悖論也正在這裏——只有在它完全建成之後,德國纔有能力和一個洲級大國對抗;但爲了建成“大空間”,柏林必須首先在現實中同時與兩個洲級大國交戰,這就決定了它永無希望實現“新秩序”的藍圖。
那麼,軸心國真的毫無獲勝的希望嗎?1944年,荷裔美籍地理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在遺著《和平地理學》中提出了一種設想:假如日本在1942年春向西進軍,自海路席捲印度洋、同時從陸上攻擊印度;而德軍在全力爭奪烏克蘭的同時,強化在北非的兵力,就有可能將兩國的控制範圍連結起來,形成一個瀕海的“邊緣地帶”(Rimland)。德日在中東會師之後,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喪失了海岸線的內陸同盟國將遭到徹底的封鎖,外圍的英美無法經海路對其輸送軍火和物資,也就無從開發蘇中兩國在領土縱深和人口規模方面的潛力。如此一來,中蘇退出戰爭、英國因印度獨立和能源通道被截斷而對德媾和的幾率將會大大增加。軸心國控制下的歐亞大陸將獨佔全世界大部分戰略資源,同時對北美實施封鎖;而美國面臨的將是它的開國者們最恐懼的情況——由於自由政體在其他地區被消滅,它在美國也無法維持下去。
但德國人的所見卻不及於此。當美蘇兩國正以前者提供技術力量和資本、後者提供人力和地理空間的方式展開合作,並在此過程中增殖其全球權勢時,柏林所設想的卻依然只是某種基於單一民族、機械呆板的“大空間”。戴高樂的政治顧問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譏諷說,希特勒試圖在一切方面模仿拿破崙,卻忘記了時間已經過去了130年。在20世紀40年代追逐一種19世紀式的帝國藍圖,不過是那位奧地利畫匠的惡趣味罷了。
斯皮克曼在1944年提出的新三大板塊:“心臟地帶”、“邊緣地帶”與“新世界”。他認爲,只有當德日兩國完全控制了歐亞大陸的瀕海地帶時,纔會對美國的經濟安全和全球地位構成真正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