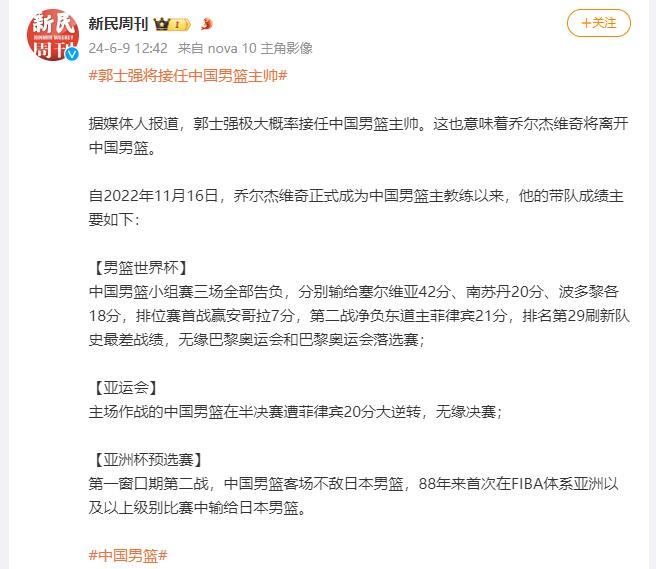三峽大壩泄洪讓大壩下游地區的洪災“雪上加霜”?真相是……
近日,北方多地遭遇強降雨,華北雨勢強盛。河北邯鄲、邢臺等地出現大範圍強降雨,局地爲暴雨和大暴雨。8月12日,北京平均降雨量40~80毫米,爲大雨到暴雨量級,局地降雨量達到200毫米以上。
降雨“主戰場”的北移並未減少南方壓力。洪水浸泡、風浪和局地降雨的疊加影響仍在,沿海地區防範颱風的警報隨時拉響。
7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有20個國家級觀測站突破日降雨量歷史極值。23個省(區、市)385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
強降雨以及連續性降雨超過城市排水能力,會導致城市內澇災害。近年來,我國發生過內澇的城市已有300多個,在內澇災害嚴重程度上,南北方城市幾乎呈現出一致的特點:即影響範圍廣、持續時間長、破壞力強大。
讓城市內澇不再發生,是市民一年又一年的殷切期待。增強城市防洪治澇能力,需要經濟有效、綠色生態的針對性措施,需要修復水生態、涵養水資源的系統性方案,更需要持之以恆,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決心和耐心。
文|李璇 編輯黃琳
7月30日下午4點多,古城西安迎來一場暴雨。強降雨導致許多路面積水嚴重。
水利工程:防澇重器
城市治澇,要給水留有充足的行洪空間。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黃江林 編輯陳融雪
7月27日,長江三峽樞紐工程開啓泄洪深孔泄洪。
8月4日,颱風“黑格比”在浙江登陸,受颱風影響,溫州內澇嚴重。
儘管多地都定過“小目標”,確保2020年全面消除城市內澇,然而,2020年入汛以來,從廣州到天津,從溫州到重慶,“城市看海”頑疾難去。
本刊記者查閱《中國水旱災害統計公報》發現:2006年至2018年,我國平均每年有151座縣級以上城市進水受淹或發生內澇。
有人質疑:我國的大型水利工程,難道沒有發揮作用嗎?
三峽工程
洪災之下,我國最大的水利工程——長江三峽工程,再次成爲焦點。
“三峽工程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有網友直接質疑:三峽水庫到底是“減緩災情”還是“雪上加霜”?三峽大壩“氣勢磅礴”的泄洪,是不是讓中下游地區的洪災更嚴重?上游重慶市區的被淹,是不是因三峽大壩的攔水所致?
“一些人誤以爲三峽大壩‘噴薄而出’的泄洪是讓大壩下游地區的洪災‘雪上加霜’,其實正好相反。”中國三峽集團總工程師張曙光稱,三峽大壩不僅攔腰削減了來勢兇猛的天然洪峯,而且何時泄洪、泄多少量,都有科學測算,保證長江中下游幹流河道有安全餘量。
在他看來,此次重慶出現洪澇,證明當地亟需加強水利設施的建設。“比如這次洪水流量達80年之最的綦江,如果建有足夠庫容的調蓄水庫,重慶的汛情就絕不會這樣了。”
作爲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三峽工程從構想提出,到規劃、設計、論證及建設過程中,各種質疑聲音一直存在。一些聲音不僅誤導了社會公衆,甚至影響了其他重大水電水利工程的建設進程。
譬如,“早就列入國家相關規劃、一直被擱淺的金沙江虎跳峽水庫,如果建起來的話,今日三峽工程的防洪壓力就會大大緩解,今天整個長江流域的洪災情形也會大不一樣。”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說。
洪澇之間
7月13日召開的“防汛抗旱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水利部表示,未來三年我國將推進150項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總投資約1.29萬億元。
新世紀以來,我國已投入運行了一批控制性水利樞紐工程,如三峽工程、小浪底工程、臨淮崗洪水控制工程、尼爾基水利樞紐工程等。
要釐清這些大型水利工程對城市內澇的作用,不妨先釐清“洪”和“澇”的關係。
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專家程曉陶表示,受暴雨影響、排澇系統集中排放,導致河網水位升高,是因澇成洪;如果河流水位過高對排水系統產生頂託,甚至倒灌,就是因洪致澇。
以三峽工程爲例,其對武漢等地的防洪作用毋庸置疑。
“武漢若單獨依靠堤防,可防禦20年~30年一遇洪水;三峽工程的建成則改善了長江中下游包括武漢的防洪形勢。”張曙光稱,今年長江第1、2、3號洪水期間,由於三峽工程的攔洪,降低了漢口河段的洪峯水位,有效減輕了武漢地區的防洪壓力。
進一步說,也就降低了頂託、倒灌產生的“因洪致澇”風險。
如果沒有三峽工程,今年洞庭湖城陵磯地區和鄱陽湖湖口將超保證水位,部分分蓄洪區將分洪運用,武漢段漢口站水位將更高,長江中下游城市的洪澇形勢也必將更加緊張。
“爲什麼2010年、2012年和2016年出現比1998年更大的洪峯時,我們反而保證了江漢平原安瀾?”水利部水旱災害防禦司副司長王章立認爲,正是因爲我們有了技術手段——以三峽爲骨幹的水庫羣聯合調度、攔洪削峯錯峯,大大減輕了中下游地區防洪壓力。
水利部近日批覆的《2020年長江流域水工程聯合調度運用計劃》顯示,經過多年來的大規模水利工程建設,長江流域聯合調度體系中的水工程總數已達101座,其中控制性水庫41座,總防洪庫容598億立方米。
城區蓄滯洪工程
相比大江大河上的水庫、大堤,城區蓄滯洪工程的作用或更爲直接。
早在2014年,九三學社中央提交《關於防治城市內澇的提案》,就明確指出“隨着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和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城市建設規模逐步增大,水泥屋頂和路面等不透水面積越來越多,城市自然的滯洪調蓄能力越來越小”,並建議“防止城市內澇,建立城市蓄洪區”。
此間,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萬豔華亦呼籲:“城市治澇,要給水留有充足的行洪空間”。
在山東省東營市,投資29.04億元的天鵝湖蓄滯洪工程剛於6月30日順利完成主體建設任務。
該工程位於東營城區東南部,根據規劃,蓄滯洪區總佔地面積約40平方公里,總蓄洪能力4000萬立方米,由南部、北部兩個蓄滯洪區相機調蓄。
工程建設組組長周天奎介紹,當小雨來時,天鵝湖蓄滯洪工程南北部蓄滯洪區可有效收儲雨水;遇到颱風強降雨時,可啓動蓄滯洪區分洪,有效解決中心城區內澇問題。
在福建省福州市,江北城區山洪防治及生態補水工程正在推進。
據瞭解,該工程總投資33億元,是福州城區有史以來最大水利工程,將在閩江北港北岸文山裏上游設五礦泵站,沿福州北面山區開挖引水隧洞,經八一水庫、登雲水庫,最後至魁岐匯入閩江。主隧洞全長約30公里,沿線設5條補水支洞、12座截洪樞紐、6座控制閘。
建成後,汛期可泄洪緩解福州城區內澇,枯水季可抽取閩江水補給內河。
至於我國最大的蓄滯洪工程,則要數湖北省荊州市的洪湖東分塊蓄洪工程。
作爲2014年國務院確立的172項國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該工程在洪湖市東部築起圍堤,形成面積877平方公里,容積61億立方米的分蓄洪區。整體包括新建腰口隔堤、高潭口泵站二站、洪湖主隔堤等工程,總投資約48億元,預計2022年完工。
湖北省洪湖分蓄洪區工程管理局總工程師張祥彬稱,如遭遇1954年、1998年那樣的特大洪水,該工程將成爲保護大武漢、江漢平原和荊江大堤的一張王牌,爲湖北防洪保安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今年的汛情中,該工程亦迅速反應,由“建”轉“防”,高潭口二站正式參與到荊州市河湖泵站的統一調度,3臺泵站機組全部開機,24小時搶排洪湖內澇,爲四湖中下區及洪湖市排澇紓困解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