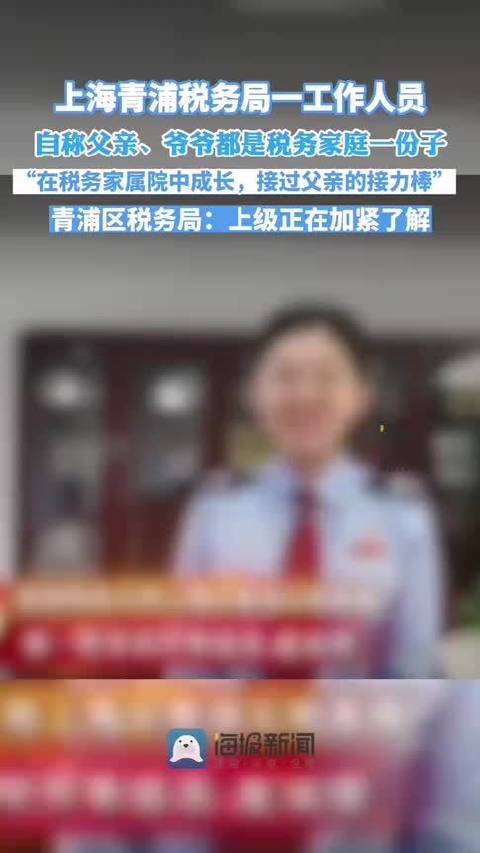淚目!山東24歲研究生離世捐獻5器官,喪子後第十天,父親回老家工地搬磚
離開世界一週後,牛忠楠的雙腎、肝臟救了3位終末期器官衰竭患者。他們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帶着牛忠楠身體的一部分,將開始嶄新的生活。
捐出的5個器官中,牛章華和郭金花一直惦記着孩子捐出的兩片眼角膜,他們看新聞說有人用了。依照捐獻遵從雙盲原則,受助者的信息不能告訴他們。牛忠楠的成績非常好,這個24歲的小夥子,正在西安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讀研究生二年級,還有一年就能畢業。
牛章華夫婦抱着一絲期望,他們盼着那個接過了兒子視力的人,或許正是西安交大的某一位學生,他們帶着孩子的眼睛,幫孩子完成未竟的學業。
10月9日,24歲的聊城莘縣人牛忠楠在西安交通大學讀研期間突發腦出血,不幸離世。父母悲痛之餘無私捐獻了他的雙腎、肝臟及兩片眼角膜5項器官。母親說:“讓別人爲社會爲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這也算是俺的一個心願吧。”
1、拼命的“牛院士”
同學們都喜歡管牛忠楠叫“牛院士”。
收到班長李磊發來的信息的時候,王雲鳳反覆確認,不敢相信那個躺在搶救室裏的“牛忠楠”,就是班裏的“牛院士”。她是牛忠楠研究生的同班同學,但兩人的交集並不多。實際上,如果不是這次“出事”,牛忠楠在同學中依然不會有特別的存在感。
穿着白色的襯衣,戴着黑框眼鏡,靦腆而安靜的牛忠楠給很多同學留下的印象就是“背影”。一個人坐在那裏默默地學習、做實驗。但因爲學習成績好,科研牛,他是同學公認的“明日之星”,也就有了 “牛院士”的外號。
李梓璇實驗室的工位緊挨着牛忠楠。李梓璇說,每次見牛忠楠,基本都是在實驗室。學校研究生的課業比本科生緊張,大家都很努力,牛忠楠更是到了“拼命”的地步。
“他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我們一般是大二纔開始做實驗,但是他大一就開始做科研。這次獎學金評定,他的總分是班裏第二名,如果人還在,這學期能拿到 1萬元的校獎學金。”
包括李梓璇在內,幾乎牛忠楠身邊的所有同學都會說起他的“拼命”,哪怕是在倒下的時刻,牛忠楠都是在實驗室裏。在同學看來,牛忠楠不屬於“天才型”的學習選手,他用超過身邊所有人的勤奮,爲自己爭取到最好的成績:班裏僅有兩個研究生保送生,他是其中之一。
“今年夏天我們去煙臺參加一個比賽,當時包括清華北大在內的很多博士生都參加了,真是神仙打架的一個比賽。忠楠所在的小組是初賽第一,決賽的優等獎。”李梓璇回憶起自己曾經有一段時間需要準備考試,在教室學習到夜裏11點多。可自己並不是最晚的那個,牛忠楠纔是。
“飲水機上的這個插排是牛忠楠買的。”王雲鳳指着牛忠楠空空的座位,幾盆綠蘿代替了電腦,在桌子上長得生機勃勃。“工位上的插電孔都不夠用的,牛忠楠卻拿出一個專門的插電孔接飲水機電源,他就是這樣一個從來都不說,總是默默在做的人。”
因爲學習計劃,牛忠楠要離開創新港校區。走之前向王雲鳳交代了飲水機的管理,包括什麼時候送水、要打哪家送水公司電話、水票放在哪裏等,“他囑咐我,送來水後我不用搬到飲水機上,等男同學來了扛上去。”王雲鳳說,在此之前,實驗室從來沒有斷過礦泉水,大家也沒想到,原來習以爲常的飲水機竟然有專人來管理。
“我們常會因爲一些學習上的事請教他,因爲他成績好。每次謝謝他,他都會說‘沒關係,我們是互相幫助’”。王雲鳳說着紅了眼眶。
在10月11日,學生自發開的追悼會上,牛忠楠的大學同學發來了這樣一段話:“牛哥,忠楠牛,牛牛,c牛腩,牛院士,大學裏幫助過我最多的人,每次要感謝你的時候,你總會說:‘沒關係,我們應該互相幫助’。這次,該我幫你了,但是我真的沒辦法幫到你了。我知道你喜歡睡覺、怕冷,但是每個冬天的早上都是你第一個起來去教室學習,我記得你說過等你研究生畢業了一定要逃離西安,去一個暖和的地方。現在你可以安心睡了。最後看到你的父母決定捐獻你的器官,我又想起你最常說的那句,我們都應該互相幫助,我終於繃不住了,牛哥啊,你是我大學裏最佩服最尊重的人,到最後你還在以這種方式幫助別人,我真的心痛,難受啊。兄弟呀,這一晚上,我一直在回想我們一起生活過的四年,牛哥你一直是我的榜樣,永遠充滿着正能量,積極向上,無私付出。”
2、雙腎、肝臟和兩個眼角膜
郭金花來過三次西安。
第一次,是送兒子上大學。以超過本科線60多分的高考成績,牛忠楠考上了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全村一年也出不了幾個大學生,郭金花的驕傲無法描述。第二次來西安,是參加兒子的研究生開學典禮。學校貼心的給父母準備了觀禮席,郭金花坐在一羣“城裏人”家長中間,雖然臺上學校領導講的很多詞都聽不太懂,但是郭金花至今還記得當時的“陣仗”:“地方特別大,人特別多,還有警察帶着警犬維持秩序。
郭金花第三次來西安,卻是因爲兒子毫無徵兆的離別。
10月4日,牛忠楠在實驗室裏感覺到不舒服,半邊身子麻痹。打電話找來關係好的師兄把他送到西安交大一附院,雖然身體已經不能受控制,但因爲意識清醒,這個邏輯性一直很強的年輕人能夠清晰條理地描述出自己身體上的感受。醫生診斷爲輕微腦出血,建議留院觀察。在收到學校的通知後,牛章華和郭金花連夜坐車往西安趕。見到兒子後,倆人放下心來——孩子一如既往的清瘦,但是精神還好,反過來安慰父母不用擔心。
孩子是一直很懂事的。但每每回憶這種懂事,只讓郭金花覺得更難受。她過後無數次的回憶和自責,要是自己能夠不顧慮孩子的“懂事”,自己多做一點,多檢查一些,多照顧一些,多掙點錢,是不是孩子就不會走?
病情是突然加重的。10月7日,牛忠楠陷入深度的昏迷,當晚進行開顱血腫清除術。手術後,牛忠楠送往神經外科ICU病房觀察,醫生說,要是能挺過去,命就救回來了。
但最終還是沒有挺過去,這個清瘦斯文的年輕人,在考試和科研面前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卻沒有敵過病魔。腦出血的原因很多,目前醫生能確定的是牛忠楠腦中有根天然的血管畸形,也可能因爲長期熬夜、營養跟不上等原因加劇了病情的發生。因爲術前腦疝形成,牛忠楠在手術後一直呈深昏迷狀態,無法自主呼吸,最終醫生宣佈搶救無效。
從發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5天。這5天中,這個來自山東莘縣的農村家庭經歷了命運最殘酷的折磨。一個年輕的生命倉促的離去,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的隻言片語安慰家裏人。
牛章華做主,將兒子的一個肝臟、兩個腎臟、兩片眼角膜無償捐獻給醫院。他不識字,也很少離開家鄉以外的地方。這兩年通過看一些短視頻和新聞,知道了器官可以移植,也知道了很多人因爲等不到合適的器官在等待和絕望中死去。
他主動找到醫生說,“如果救不回來,就把娃能用的器官捐出去,給那些需要的人,那個人最好是西安交大的學生,或者是個年輕人。”
牛章華說,不是覺得老人、孩子就不要救了。而是想兒子以這種方式延續生命,爲社會做更多的事,因爲關於未來,“楠楠還有很多事沒做。”
“學校、老師、同學還有社會上的好心人對楠楠幫助很大,楠楠還來不及回報。捐出去,就算是楠楠給社會做的最後的回報。”
郭金花一開始並不算同意。兒子是娘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這個生命,曾經在她的腹中孕育,在她的懷裏撒嬌,被她牽着手送到學校。如今,這個曾經給她帶來無限希望和甜蜜的孩子要走了,她希望能完完整整的離開,正如她完完整整的把兒子帶到世上。
丈夫的一句話,打動了郭金花。“器官捐了,救了人,這樣孩子還留在世上,還沒有走。”
在深夜醫院走廊的日光燈下,牛章華顫抖着拿着兒子的器官捐獻書,裏面密密麻麻全是字。牛章華不認識,郭金花認識的也不算多。工作人員幫着填好了其他信息,最下面的簽名欄,牛忠楠的堂哥幫着簽了字,牛章華和郭金花最後在名字上按了個紅色指印。
10月9日晚23時08分,在陌生的西安交大一附院,他們與兒子告別。
3、5張卡,22塊錢和17萬
在牛忠楠和病魔搏鬥的同時,不只他一個人在奮鬥。
錢,是牛章華夫婦在憂心之餘最擔心的事情。在ICU,錢是紙,也是命。每天一萬多的費用,是這個農村家庭不可承受之重。
夫妻倆一直非常能幹。牛章華在村裏當建築小工,郭金花種地和打零工。一年到頭起早貪黑,生活卻沒有好多少,夫妻倆都“沒什麼文化,只能做體力活兒”,所以才一定要拼死拼活地供孩子讀書。
牛章華說,因爲不識字,他沒有辦法走出農村。因爲沒有文化,他一直靠着賣力氣生活,出去打工被工頭欺負。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孩子不要像他一樣,走出農村,找個“能在辦公室裏的工作。”
幹建築工,一天拿起放下幾千塊磚頭,能掙100多元錢。這些年的生活像刀子一樣縱橫交錯地刻在牛章華的臉上,雖然只有48歲,整個人看起來卻比實際年齡滄桑很多。
站在ICU病房前,每一分每一秒的逝去,不僅意味着搶救和治療的寶貴時間,也意味着源源不斷的醫療賬單。
王雲鳳捐了500元,班長捐了1500元,班裏的同學、學校的老師陸陸續續地都在捐款,也在不斷地轉發水滴籌的鏈接。幾十、幾百、幾千……一筆筆善款像一條條小溪流,匯向在醫院和死神搏鬥的牛忠楠。
這是愛心和死神的搏鬥,也是一個貧困家庭最後的指望。在牛忠楠治療期間,不斷有陌生人添加牛章華和郭金花的微信。很多人不留下姓名,會直接轉款,最後籌款多達17萬,可以支付第一階段手術和治療的費用。腦出血的患者留下後遺症的概率非常大,牛章華都想好了,就算是孩子以後傻了、癱了,自己都會養着他。自己還有一把力氣,不能再向社會伸手,會用雙手再養着兒子,就像孩子小時候那樣。
但人最終沒有救回來。就算所有人都在爲這個年輕的生命追求每一絲希望,都不能抵抗命運錘下的榔頭。
從牛忠楠發病到去世,學校的老師一直陪伴在側。牛章華一直反覆說着道謝的話,生怕麻煩老師和同學。只有在10月10日,孩子離開的第二天,他向學校提出了唯一一個要求:去孩子上課、生活的地方看看。
教室、實驗室、宿舍、餐廳……在實驗室,學校的領導說可以把牛忠楠的電腦帶走,但牛章華拒絕了,電腦是學校的,下一個學生還能用。他帶走了兒子實驗室工位上的名牌,因爲上面印着牛忠楠的名字和照片。
遺物的清點十分簡單。除了一些簡單的日常衣物,唯一的貴重物品就是一臺筆記本電腦。牛忠楠有5張銀行卡。牛章華和郭金花去銀行查詢餘額,其中4張卡是空的,只有一張卡里有22塊錢。
在參觀學校時一直繃着眼淚的郭金花再也控制不住了。每次夫妻倆給孩子打電話,都會得到同樣的回答:“媽,我有錢,不用給我打錢。”但這22塊錢的餘額,讓她意識到孩子平時過得多麼辛苦和節儉。
對於牛忠楠在學校的生活,作爲班裏比較親密的朋友,王亮亮多少能猜測到牛忠楠的經濟條件一般。“忠楠每次去食堂喫飯,基本都不會超過10塊錢,都是喫素菜。”王亮亮說,他們很少會談論起各自的隱私和家庭,牛忠楠是很隨和的人,大部分時候都是自己在說,他在聽。
同是山東老鄉,班長李磊對牛忠楠的家境瞭解的稍微多一些。從大學開始,牛忠楠就申請了助學貸款。有時候遇到一些整理材料之類比較輕鬆的兼職,他也會推薦給牛忠楠。“從來沒見忠楠自己去外面的飯店喫飯,穿的衣服也從來沒有品牌。但是班級的一些集體活動,他都會參加,一些班級開展的捐款等他從來都積極響應。忠楠只是捨不得給自己花錢。”李磊說,獎學金、讀研國家給補助以及牛忠楠平時做科研課題老師給的一些補助等加起來,勉強夠學費。牛忠楠不想問家裏要生活費,就只能省錢和掙錢。
這是牛章華和郭金花最心痛的地方。
“還有錢嗎?缺錢你就說,在外面別難爲着。” “有錢,我不缺錢,足夠花的,放心吧。”
這樣的對話經常上演。實際上,不管是在西安的牛忠楠還是在聊城的父親,倆人都沒錢,他們的銀行卡上已經沒有了積蓄。家裏還有一個弟弟,上學的開銷不小。而且今年由於疫情和胳膊骨折的原因,牛章華已經大半年都沒有工作。
“他從來都不要錢,之前開學的時候他爸爸都是不等他要,直接給他往卡里打錢。”郭金花說,7月份的時候跟兒子打電話,他還說自己接了一個新的兼職,一個月能多掙600塊錢,“生活費足夠了,不用給我錢。”
牛章華和郭金花,寧願孩子不那麼懂事。多喫一點,多玩一會,也許這些就不會發生。
在同學給牛忠楠開的追悼會上,有大學同學說,牛忠楠從大學入學之初就幹兼職,最開始是發傳單,後來是幹家教、整理文件材料等,而這些,牛忠楠基本都是瞞着父母。
兒子一直很瘦,回憶裏基本沒什麼他特別愛喫的東西,或者不喜歡喫的東西。都是家裏做了,他就喫什麼飯,從來不會提要求。但是牛章華知道,兒子愛喫豬蹄,有一次一個人啃了一大個豬蹄。“豬蹄這麼貴,天天喫也喫不起。”牛章華的聲音顫抖,“早知道,多買點。”
4、關於未來和愛情的夢
10月23日,按照老家的說法,這是牛忠楠的“二七”,是“頭七”之後第二個紀念的日子。這一天,郭金花騎車到兒子的墳上又哭了一場。墳地離着村子騎車要近半小時,當時選墓地的時候,家裏親戚都勸把墓地選址在遠一些的地方,以免看了傷心。實際上,雖然墓地選址不近,郭金花基本上還是天天都去。
“我要多去看楠楠,我怕地方太遠,楠楠找不到家了。”郭金花說,她每天都盼着做夢,希望兒子能到自己的夢裏來,但從來沒有。郭金花安慰自己,也許這是兒子在地下過的心安,“我跟楠楠說,你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就要告訴媽媽。”
實際上,即便沒有到母親的夢中訴說心願,關於未來,牛忠楠還有很多計劃沒有完成。
如果沒有這次意外,牛忠楠將在明年面臨甜蜜的苦惱:是直接工作,還是選擇繼續攻讀博士。導師已經向他明確表示希望他繼續讀博,心儀的公司也向他伸出了橄欖枝。
除了工作,這個年輕人,本該開始一段美好的愛情。
郭金花很想知道那個在生命盡頭,兒子牽掛的姑娘是誰。聊起兒子這段愛情的時候,郭金花難得的露出了一點點的笑模樣。她熱切地問記者,“是哪個姑娘?長得什麼樣?”
關於這段還沒來得及展開的愛情,只能從同學那裏拼湊出模糊的輪廓:牛忠楠參加了學院的聯誼,女孩在聯誼的照片上發現了這個清秀的小夥子,女孩很勇敢,直接拿着照片去找同學打聽牛忠楠。
“隔壁院系的漂亮姑娘倒追‘牛院士’”的消息一出,班級羣裏炸了鍋,幾個和牛忠楠關係不錯的同學都在調侃這是“牛的春天來了”。有女孩子喜歡,這讓牛忠楠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倆人約了在週末見面,見面之前牛忠楠還向班長取經,應該怎麼樣跟女孩接觸。
“我給他出主意,說你就買點女孩子喜歡的零食、花茶,不用貴重,但是別空着手,說話多主動一點,注意人家的情緒。”李磊說,在他的“策劃”之下,牛忠楠和女孩有了第一次約會。“忠楠說他緊張,把所有能想到的話題都說完了。”
第一次約會很緊張,但很完美。大家沒有見過那個女孩,但牛忠楠說她很漂亮,“這應該是忠楠第一次戀愛,因爲他說了一句‘想不到我這樣的人也能找到女朋友’。但是估計還沒正式開始,因爲忠楠後來沒再提這個姑娘”。
可惜的是,少年的美好剛剛開始就結束了。“10月3日,就是他出事的前一天,我還聽忠楠特別高興地說得抓緊幹活,幹完了要有個約會。”
到目前爲止,沒有人知道這個女孩是誰,但是郭金花感謝這個女孩,是她,爲兒子短暫的生命增加了愛情的希望。
5、喪子後的第十天,重新開始打工
#捐獻5器官研究生父親回老家搬磚 24歲的聊城莘縣人牛忠楠上學期間突發腦出血不幸離世,父母捐獻了牛忠楠的雙腎、肝臟及兩片眼角膜共5項器官。23日,記者在莘縣見到牛忠楠父親,他已經回到工地上搬磚,生活還在繼續…
即便是看慣了生死離別場面的遺體捐獻協調員,也對牛忠楠父母的印象極爲深刻。因爲就是在西安,用幾位醫護人員的話來講,主動捐獻器官的也是很少有“這麼高的覺悟”,而在莘縣這座魯西南的小縣城裏,當地人的傳統觀念裏,也講究入土爲安。
西安交大附一院派車送回了牛忠楠的遺體。牛忠楠回到了生他養他的這個農家小院。
院子很大,收穫的玉米碼的整整齊齊,依然顯得格外空曠。院子裏一棵梧桐樹,角落上有個磚頭壘的小狗窩,還有個大牲口棚,但看起來已經荒廢了許久。在深秋的風裏,看起來更爲破落。
“前幾年貸款養豬,結果碰上豬瘟和豬市不好,都賠了。”
這是一個極爲樸素,稱得上貧寒的農家院,堂屋地板的磚石都坑坑窪窪的不平。天花板上有房子漏雨溼出的褐色水印子。牛章華說,家裏房間少,就把堂屋的這個角落隔出來,做了倆孩子的臥室。趕上雨季的時候,屋子就會漏雨,得拿洗臉盆接雨。
牛章華按照村裏壽終正寢的老人才能享受的規格給兒子操辦了葬禮,算的上是厚葬。棺木和儀式等加起來花了2萬多。這是家裏僅有的存款,也是最後一次有機會給兒子花錢。
儘管家庭貧寒,但牛章華已經給予了孩子一個父親所能給予的全部。在這個貧寒的家裏,最值錢的電器就是一臺空調。這是牛章華去年花4500元錢從朋友開的電器店裏賒來的,到現在欠賬也沒還上。
因爲貴重,空調上蒙了一個帶着小花邊的空調罩。
“怕楠楠冷給他買的空調。”空調,無線網絡,家裏一切跟現代化沾邊的都是爲兒子準備的。他一直是家庭的驕傲,也一直是所有親人的希望和驕傲。
不管是牛章華家,還是郭金花家,往上幾代推都是土裏刨食的農民。到了牛忠楠這一代,仰望星空成爲可能。
“我想楠楠。”郭金花跟丈夫訴說,也像是一種自述。在兒子離開後的每一天裏,這樣的對話都會無數次出現。牛章華沒有吭聲,但這個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覺得難受。他打開一個銀色的行李箱,反覆收拾清理兒子遺物時帶回家來的東西。銀色的行李箱放在灰撲撲的堂屋裏格外顯眼——裏面全放着兒子從小到大的榮譽證書、學生證、錄取通知書。
郭金花常常喃喃自語的一句話是“毀了,啥都沒了。錢也沒了,人也沒了。”相比妻子,生活留給牛章華沉浸悲痛的時間不多,在兒子去世後的第十天,牛章華就吊着胳膊去蓋房子當小工。因爲家裏從養豬時就欠下的賬沒還完,還有14歲的小兒子需要撫養。
哥哥去世之後,小兒子彷彿一夜之間就長大了。在哥哥的葬禮上,這個正在青春期,讓父母頭疼的少年第一次表現出了大人的成熟,跟在媽媽後面,不哭也不鬧,就一直看護着幾近昏厥的母親。
6、謝謝啦,再見
捐獻兒子器官的事上了新聞,突然間,牛章華和郭金花發現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網絡中。電視臺和網站的記者也給她打來電話,這有點嚇到了他們。
“沒想到搞這麼大,我們沒想通過這個事出名,我們不想接受採訪。”她抓起手機翻翻微信,裏面有各種媒體來聯繫她的留言,看幾眼又放下,反覆幾次。“前面很多媒體我們都拒絕了,你們大老遠跑來了,還去了楠楠上學的地方,不容易。”
最讓他們難受的還是村裏的蜚短流長。“有人說我把孩子給賣了!把孩子器官賣了!”一直低着頭翻看兒子相冊和遺物的牛章華突然抬起頭來,聲音也提高了幾個分貝,“那是我兒子!”
最終,他又低下頭,給記者找他收藏的關於媒體報道捐獻的視頻,帶着些許惶恐的神色感慨:“都有點後悔了。但是我想如果楠楠能有意識,他肯定會支持我。他愛幫助人,能幫上別人他高興。”
雖然家徒四壁,但在辦理完兒子的後事後,牛章華託侄子給忠楠的同學和朋友羣發了短信:“因爲之前處理的有點倉促,所以對大家的幫助額度記得不是很及時。希望大家收到信息後及時回覆我金額和姓名,以便於我及時準確地退還給各位。再次感謝大家。”
微信上沒有人發來賬號,相反牛忠楠大學時期的11位舍友,一起給牛章華打來電話:希望能夠把牛忠楠的弟弟當成自己的弟弟,資助他一直到畢業。
“好意我們都心領了,但是我們怎麼把楠楠供(大學)出來的,我們就怎麼供他弟弟。”對記者轉述的牛忠楠研究生同學計劃籌備二次捐款的事,牛章華也明確拒絕,“謝謝同學們了,但我們不用了。你們還是學生,錢自己都不夠用。你們已經幫了我們太多了,我替楠楠謝謝你們。”
不管是家人,還是同學,在所有熟悉牛忠楠的人看來,如果讓他自己選擇,他一定會選擇捐獻器官,“因爲他就是這樣一個喜歡幫助別人的人。”同學王亮亮說,“如果是我,我也會這麼做”。
王雲鳳深刻地記着最後一次見牛忠楠的場景:9月19日的傍晚,她到實驗室去拿東西。牛忠楠如往常一樣在做實驗,用電烙鐵焊接一塊電路板,電烙鐵預熱需要一段時間,放下就意味着要重新開始預熱。
“我說,‘牛院士’,方便時借我電腦用一下。忠楠就放下電烙鐵去幫我拿電腦,還說重新預熱也沒關係,幫我清空了SD卡,現在這張卡還在我手裏。”
實驗室是正西朝向,夕陽透過窗戶照進來,牛忠楠就沐浴在一片夕陽裏。出門的時候,王雲鳳說了句,“再見‘牛院士’,謝謝啦。!”牛忠楠從夕陽裏抬起頭來,笑着說:“不客氣,我們是互相幫助。”
來源:齊魯晚報
聲明:轉載此文是出於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註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繫,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來源: 西安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