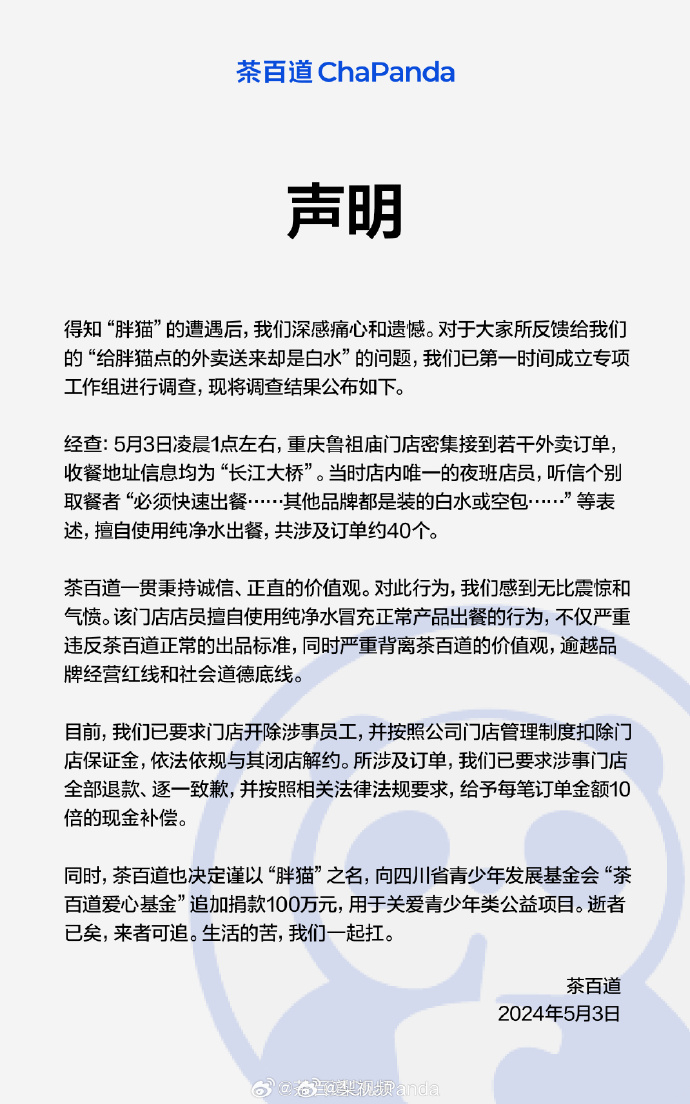現代人養寵物爲什麼那麼貴?
來源:SME科技故事
養寵物的開支問題,算得上是當代青年與老一輩的巨大代溝之一了。
根據《2019年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的調查報告,去年中國城鎮人均單隻寵物的年消費金額達到了5561元。在很多年紀較大的父輩眼中,這無疑是十分難以理解的一項支出。

現在我們在都市中養一隻寵物,光是購入就要動輒幾百上千的價格。接下來還要給它體檢、打疫苗、準備專用的窩、籠、繩、食物,甚至還有玩具、沐浴露等等日常用品。
而對於我們的父輩來說,養貓養狗?無非就是拿個麻袋,去鄉里剛下了崽子的家庭討要一隻,有些地方按習俗最多也就是給主人家一袋紅糖討個吉利罷了。回到家後呢,小貓小狗就喫着一家人的剩飯剩菜長大。別說體檢打疫苗了,以前很多寵物一輩子也不見得有主人家給洗一次的。

冰心奶奶與她的貓
現代人養寵物的成本爲什麼那麼高?我們還能不能以父輩那種低成本的方式來擁有一隻屬於自己的寵物?
從最常見的貓、狗這兩種寵物入手,回顧一下它們在人類社會的各種變化歷史,或許我們便能找到上面這兩個問題的答案。

放錯了,是這張。

以前的中國民間社會,大家養的幾乎100%是被稱爲“土貓”、“土狗”的中華田園貓犬。
這些本土品種貓犬的特點是易得易養,但同時它們也普遍保留了較大程度的原始野性,並且其品種特徵豐富多樣,較難把握概括。

一個原因是中國地大物博,光是中華田園犬就有北方品系、江浙品系和兩廣品系三大分支。而除了這三大品系之外還有很多過渡區域的品種和特殊的亞種。
另一個原因則是在多年的養寵過程中,我們沒有像西方人那樣強烈的慾望對貓犬進行大量的育種定向培育。
所以貓犬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地位,從文化角度導致了它們的價格不會太高。

反觀西方世界,在17到18世紀間,獵犬作爲貴族狩獵的陪伴者存在,而宮廷中貴婦們懷中的貓也是社會上流精英的標誌。到了19世紀,中產階級崛起並加入了飼養寵物的大軍之中,由此養寵概念深深印刻在其階級文化之中。
從19世紀中旬到20世紀初的維多利亞時代,現代意義上的寵物飼養就已經在西方城市中興起了。狗的品種分類對應着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秩序等級,人們愈發注重其寵物的血統,也進一步推動了寵物商業的發展及其價格的飆升。
十九世紀中葉的倫敦上流社會,抱着一隻什麼寵物出場,就跟現代社會開什麼車去參加宴會是同樣的意義。

所以當我們開始引進英短、美短、布偶、加菲、蘇格蘭摺耳貓等等外來品種時,就會發現它們的價格比中華田園貓怎麼都高到不知道哪裏去了?
很明顯的區別在於:這些品種貓比起中華田園貓在抓老鼠方面完全不行。但是,它們在陪伴跟討好人類方面可有一套了——這就是歷經上百年時間培育出來的結果。
又因爲這種狀態顯然更適合都市生活,所以更多人選擇了貴的情況下,現代寵物的價格一下子就飆升上去了。

英國短毛貓
而既然貓犬都買了貴的,就像買了一臺好車一樣,“配套設施”當然也得跟上去。貓舍、犬舍、食物、玩具、洗浴裝備,甚至美容套餐等額外消費也就隨之而來了。
從科學角度考慮也有根據。
都市生活不如鄉鎮寬敞,這意味着我們需要在狹小的空間裏與貓犬長時間共處一室。它們可能帶來的病毒、細菌、真菌還有寄生蟲等等就成爲了我們必須加緊防範的考慮因素。
所以打疫苗,時常清潔也成了必須做好的日常功課。

“貓展打分”也是貓種提高身份地位(價格)的重要途徑
那麼我們還能不能以父輩那種低成本的方式來擁有一隻屬於自己的寵物呢?
答案當然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生活在一個足夠“野”的地方,能夠讓貓狗自娛自樂呈半放養狀態。另一方面則是對它們的期待只是像父輩一樣,只需要它抓抓老鼠或者看好大門。兩相結合,就可以從成本和後續支出角度大幅削減開支。

但如果想在城市裏養一隻作爲陪伴的寵物,還是好好爲它進行體檢,打好疫苗。
絕對不要爲了削減一點成本,最終釀成更大的人畜健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