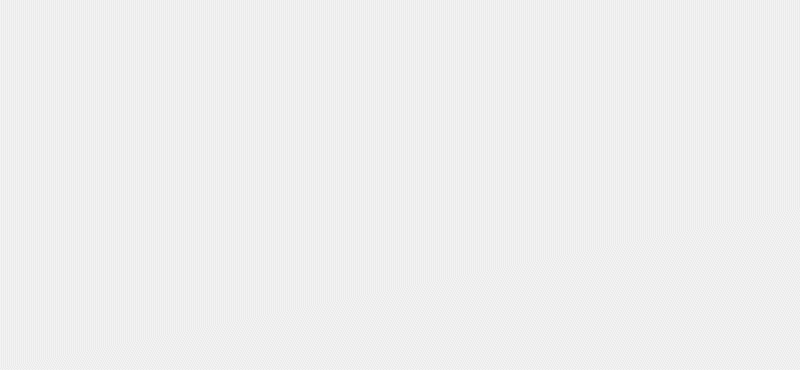《失落的衛星》:“每次旅行我都有種恍惚,生命像一場幻覺”
旅行是一種逃避嗎?爲什麼在旅遊網站和遊記盛行的21世紀,嚴肅的旅行文學作家還值得作爲一種職業?劉子超在九年裏幾乎去了中亞能去到的所有地方,帕米爾無人區、前蘇聯的核爆試驗場……寫了一本22萬字的《失落的衛星》。層出不窮的新事物、一波又一波時代浪潮裏,他執着於那些失落之國、部落和遠古族羣。
這一次,五天的公路旅行。兩個不熟的人,將穿過大興安嶺,沿着中俄國界河額爾古納前行。路上偶爾嘗試交談,但一定不是我們熟悉的城市咖啡館裏的聊天:在擔心冷場中槍林彈雨一般的妙語連珠。現在,我們出發。
···············
陌生的鄰居
沿着風與路,車從海拉爾遊蕩到了草原裏,我幾乎把頭探出窗外,九月中旬,北京連着工作已被車遠遠拋到腦後,山野無盡。
一旁開車的劉子超平視着前方,作爲專職旅行作家,這幾年他隻身出入中亞各國,對將至之地的歷史人文又熟悉,並有着作爲旅伴最珍貴的品質——安靜,車上宜人的長時間安靜。
他偶爾活動脖子,更偶爾視線偏航望一眼風景。

過去五年,劉子超去了中歐南亞東南亞中亞,寫了三本旅行文學,第三本《失落的衛星: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剛出不久。他幾乎去了中亞能去到的所有地方,帕米爾無人區、前蘇聯的核爆試驗場、曾在歷史驚駭一時如今幾近消失的城市——蘇聯解體後,那些地球村裏幾乎最被遺忘的、我們陌生的鄰居。
爲什麼在旅遊網站和遊記盛行的21世紀,嚴肅的旅行文學作家還值得作爲一種職業?想起這些我又望着窗外草原出神,開車的人忽然愉快指着遠處一座白塔,“看,還是來北海公園了。”
“水面倒映着美麗的白塔”的北京北海公園,是我們原本要去的地方。一場拖了三個月的採訪,我正要把預約門票的叮囑發出時,他的信息發來:
“我正打算去大興安嶺,你要不要去?”
馴鹿上山了嗎?
三天後,我們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碰頭。中午在海拉爾市一家火鍋店,這兒飯量顯然比北京大,我們望着盛上的一碗碩大米飯瞪圓了眼睛。
“明天我們可能會看到馴鹿。”劉子超有點兒高興地說。
他託朋友找到一位在根河的鄂溫克族馴鹿人,兒子住在城郊部落聚居點,頗新潮,父母仍生活在大興安嶺深林養馴鹿。“不過下雨鹿就上山了,就看不着鹿了。”他興致勃勃介紹起鄂溫克族和鮮卑的淵源,我們將經過額爾古納——像要從裏面嚼出什麼似的念着這個名字,“你想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那是一個市。”我心裏說。
我和劉子超之前見過兩次。一次是他和歷史學家羅新關於《失落的衛星》的對談,年輕時讀了大量蘇俄文學的羅新在過去十年常去中亞,但接觸的都是當地同行,這是羅新讀到的第一本中國人寫的中亞紀行,57歲的他羨慕作者在中亞接觸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另一次是和他喫飯的人拉上我,“子超屬於超級大悶鍋,我都不知道和他說啥。”他很少談論自己,社交網絡上個人生活完全隱形,在他前兩本書裏我也看不清作者本人。那次見面,我們一直在等店員通知打烊。

第三次見面很快結束,我藉口要午睡提前離開。作者還是在書裏更親切一些——整個下午我都在咖啡館看他的新書,幾次笑出聲。收到他問我在哪喫晚飯的信息時,我正看到書里人坐車貼着阿富汗邊境前行,司機想讓他換到低於票價的後排座位——我馬上回復今晚有稿要編,再接着看書。
出發,“今天我們先去額爾古納,再到根河歇下。”第二天換上自駕車後,劉子超邊開車邊說。他給我看過這一程的路線圖,我們將穿過大興安嶺——我只在小學課本見過的景色,他曾坐着穿越西伯利亞的火車繞過大興安嶺外圍,兩天窗外都是金色森林。那趟火車上,人們從早上九點多就開始喝酒,整個車廂都是伏特加和黑麪包氣味。
車上很安靜。音響無法連藍牙,他徒勞地調了一下收音機功能。我全神貫注地看風景,有時想起要寫的這篇採訪稿,又問一些徒勞的問題:你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
“你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他反問。
但聽到我說林間有采蘑菇的人時,他馬上掉頭往回開,走進白樺林找到採蘑菇的夫婦聊起來。他們住在我們要去的根河市,大興安嶺的蘑菇採摘季到了,前一晚下雨,林裏冒出許多白樺菇,這個下午他們摘了兩桶。過了會兒,“聊的差不多了。”他和我說。我們離開。
車到根河遇上大雨,那戶人家告訴我們馴鹿上山了。但在鄂溫克獵民聚居的敖魯古雅,有個地方或許可以上山找鹿。距離敖魯古雅還有4公里,“要去嗎?”他問。
“不去了。”我說。
他接着開過去,我們到達敖魯古雅,聚居地竟然要收100元門票,裏頭只有漂亮木屋售賣鹿製品。但有另一條上山路,需要穿過城區,再開二十多公里小路。“還要再開嗎?”他說。
“不要了。”我說。
然後他繼續往前開去,大雨瓢潑,進山口被封山架攔住。我們沒見到馴鹿,但大雨中,出現了兩道光柱一般的巨大彩虹。

“今天的工作結束了。”車到旅店門口,他滿意地說。
我回房點外賣,接着編那篇不存在的稿子。他去喫晚飯,發來一張“鮮卑”啤酒照片,我掃了一眼繼續看書;書裏已經到吉爾吉斯斯坦的塔姆加了。
白樺林裏的改道
“去莫爾道嘎的路封了。”
在根河一家羊肉燒麥店喫早餐時,劉子超以一種試圖讓我別擔心的語氣說道,看我依然忙於燒麥,他加重語氣,又加了砝碼,“如果路上出現修路、斷路,或其他情況,我們就得折回根河,再想其他辦法。”
我們決定改道,山霧還懸在林梢,走兩條小路彎到原本要去的莫爾道嘎。山路邊停着三輪車和裝蘑菇的桶子,一些人把封山架抬起,騎摩托進了山。根河是森林與草原的界線,大興安嶺和呼倫貝爾大草原在此交匯,一邊是草原、河流,一邊是森林、山崗。
“再往前就是林區,手機就沒信號了。”他說。
信號消失前,我在車上還不時收到工作信息,他安靜聽完我關於工作的氣話。他辭職寫作後,我陸續在他以前工作過的兩家雜誌工作,聽不同人說起他,在趕稿和曠工中看他在雜誌上一頁一頁走去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在前單位時,編輯常勸我想一想以後的出路,“你不能一直當記者吧?”舉的正面案例是隻身赴中亞寫中亞的劉子超和一位用幾年時間重走西南聯大之路的前輩——“做一些屬於你自己、真正重要、能抵抗時間的東西”。
去年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擔任顧問的首屆“全球真實故事獎”中,一箇中國人視角的中亞失落之國——劉子超寫的烏茲別克獲了特別關注獎。

劉子超從高中起就想當作家。那時他讀着國內先鋒派文學和海明威們,投稿到新概念作文大賽得了二等獎,同屆獲獎者有郭敬明。北師大二附的文科實驗班同學們也愛寫作,大家還自費出了本作品合集。2007年北大中文系畢業後進了南方報業當記者,每次採訪完作家和導演,他就想自己的作品在哪兒。
寫什麼?他覺得自己沒有父輩那樣大起大落的人生,沒經歷過飢餓和戰爭,找不到“支點”,只好在業餘時間譯書。
一切都是新發生和新建的,經驗始終是嶄新的,他這代人都會有這種錯覺——飛速變化和發展是世界的常態。2012年,他在旅行雜誌《穿越ACROSS》當記者出差去中歐自駕時,像站在了歷史岔口。
他當時寫到80後一代“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變化最爲迅猛的30年,目睹了層出不窮的新事物,見證了一波又一波的時代浪潮。我們希望找到某種恆定的東西。”那時他還是位青澀的新晉旅行者,很容易浪漫,很容易感動,與陌生人蜻蜓點水的幾句交談也放心上,回國寫稿時還鄭重其事地話別:
“你要是寫布拉格的話,一定要寫寫米洛斯拉夫,”臨走前,米洛斯拉夫醉醺醺地對我說,“你就寫,米洛斯拉夫有三個漂亮的女兒,他幸福地生活在布拉格。”
我告訴他,我一定會這樣寫。
現在,米洛斯拉夫,我寫下了這句話。我希望你和多米尼卡、艾莉絲卡、安娜能繼續幸福地生活——在布拉格,或者在別處。”

當記者採寫社會報道時,他有時苦於幾千字裏總要給出一個完整邏輯或定論,“但有些事你去採訪,發現就不存在一個看似合理的簡單邏輯,更不說定論,世界的複雜程度是不能用短短一萬字理清的。”文學不用涇渭分明,書的容量更大,他想用寫書來對沖以前當記者的副作用。
工作第一年的記憶只剩三個新聞標題:天價釘子戶的人生傳奇、福建元代沉船挑戰盜寶者、華裔美軍士兵成長簡史。“可我的生活發生了什麼呢?”他能想起的全是採訪對象的人生片段,當記者久了,他覺得自己生活被不斷切成一個個小的採訪,其他工作雖然接觸不到這麼多人,但對自己生活有更多沉浸和體驗,不至總圍繞着一個一個採訪對象打轉去努力感受和理解別人的人生,36歲的他望着我:“你沒有這種感覺嗎?”
我也望着我的採訪對象,這不就是此刻我在做的嗎?
26歲的記者劉子超去了新疆霍爾果斯口岸——那是十年前,他站在國門處看着通往中亞的卡車隊列和遠方壯闊的天山,對國境口岸另一邊的哈薩克斯坦和那邊的人無限好奇。第二年秋,他去了烏茲別克斯坦,像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又遇見突厥人波斯人俄羅斯人……有種強烈震撼,歷史中的撒馬爾罕和七河之地不再是虛構之所,而國際新聞中正值蘇聯解體二十週年之際。
回國寫了一千來字便寫不下去,巨大篇章展現在他面前,他抓不住。
界線在日落日升間
我們在黃昏抵達中俄邊境的室韋口岸,日落在蜿蜒的額爾古納河面,波粼泛動。卡在兩個景區化的村落之間,車停下,我們分了罐啤酒,站在國境網前看太陽一點點掉下去。

我不明白他爲什麼總和那些遠古的、現在看不到的東西有特殊的勾連,但對他從小長大的地方沒什麼特別情感。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十三四歲時的快樂是初中上學路十公里,6點半出門,蹬上自行車,圍着後海穿衚衕。等冬天結冰,他就騎車在冰上溜,一溜飛很遠。“現在後海早成了酒吧一條街了。”他說,北京也在新世紀後的城建中陌生起來。
我不太能理解他這樣的人對邊緣人物、對失敗的這種感同身受——首都長大,北大畢業,行業前輩,全職作家,36歲前出了三本書,譯了四本書。
2015年,31歲的劉子超出版的第一本書《午夜降臨前抵達》獲得單向街書店首屆文學獎“年度旅行寫作”。同一年,他任職四年的《穿越》雜誌停刊。當記者的幾年裏,他在若干家媒體裏打轉,每當處在棘手環境,他就申請一個國外讀書項目離開,和單位辭職。
《穿越》停刊後, 他回到《南方人物週刊》, 原來做着一樣工作的朋友和同事開始創業,朋友圈裏一輪一輪的泛媒體類的創業企劃書、A輪B輪投資的進展消息源源不斷。站在分岔口,他也動了心,甚至和熟悉的人具體介紹過一個旅遊媒體類的創業項目的想法。
但這一年,他最終決定去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院待兩個學期,然後辭了職。在朋友圈裏看北京,創業景象熱火朝天,但接着,很多分享創業進展的朋友和前同事慢慢在朋友圈裏消失了。他想如果自己在國內,很可能被浪潮裹着做些事、失敗,再消失。“那些沒成功像潮水一樣被沖走的那些人,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嗎了。因爲失敗者就默默地就走了,難道你失敗了還要大張旗鼓嗎?”

大學時,北京大學的文學社迎新大會上,那些最被看好未來成爲作家的文學青年挨個上臺自我介紹。社長上臺,滔滔不絕。到編輯部主任,“大家好,我叫劉子超。”就下去了。
後來,那些最被看好的青年們,有的在中央黨校當老師後又回北大中文系任教;也有人趕上教育發展大潮,成了知名培訓機構裏的核心人物。往日在主流道路同行的同學們繼續晉升創業、討論買車買房孩子補習班時,劉子超忽然岔開道口,走去另一個方向。
30出頭,劉子超從牛津回北京後,沒找工作,開始一趟一趟地跑去中亞——同時,他把這之前的旅行文章梳理補充成第二本書《沿着季風的方向》,並打算在第三本書裏挑硬弓拉。沒有穩定收入和出差報銷可隨心出遊了,積蓄少,他申請了一些寫作項目資金,又給雜誌寫稿。但他當然不用像一些北漂的專職寫作者那樣離開北京,因爲北京就是他的家。
前兩本書無人問津,父母沒明勸,但偶爾也讓他知道,“行了,差不多了,該找個正經事了”。
第三本書出版,有人關注,兩個月銷量兩萬多冊——在純文學出版界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成績。父母不再說什麼。他去了幾個城市籤售,沙龍里和人對談。“我很羨慕你啊,你很自由,還在堅持寫作啊。”總有以前認識的人這樣對他說,他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只好謝謝。
尋找消失的黑山頭
中亞許多城市的相似街景總給人一種恍惚感,比如棋盤一樣規劃整齊的街道、高大行道樹、雕像衆多的公園,劉子超有時有種被遺棄感,來自那些蘇聯國家意志的遺蹟。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他遇到一個給自己起中文名叫“幸運”的年輕人,小時候學俄語,後來學英語,現在又學中文,口頭禪是“我被困在這裏了,哥!”
出發前,他沒想過現在的中國在中亞的意義,直到在一個個城市裏見到一些中國援助的基建項目和孔子學院等,最後他把中亞定義成一個失落的衛星,放進整個世界和歷史的版圖裏。
“衛星不就是總要找一個行星圍着它轉嗎?”他反觀中國,感到以往認爲理所當然的高速發展和機會其實那麼偶然,“完全可能就像中亞一樣繼續保持這種失落的狀態,在一些歷史岔口就消失了。”
在我們通往黑山頭古城的路上,沿途很多部落和旗都成了景區,連手機導航也失效,在一望無垠的草原播報“注意前方路段擁堵”。我望風景時,一轉頭看到劉子超還在專注開車,不能四處張望,就爲自己沒駕照這件事感到很不好意思。

這次出行,他的洗漱用品都是便攜小瓶裝,行李整齊疊在行李箱,揹包機動。早晚分別做30個俯臥撐、40個仰臥起坐——我老聽到隔壁屋有動靜,在一次早飯時發現原因。開車、喫住、路程都是他負責,顛簸途中,他也認真喫三餐,不喫我買的垃圾食品。“你平時出差時喫飯怎麼辦啊?”他問。
他的寫作旅行比我更像出差:出行前把地區的歷史、文化、政治分成不同切面,再在旅行中找到對應的有代表性的人聊天,他隨身攜帶可換芯的筆記本記關鍵詞。一個城市短時三四天,長時十天,等素材累積夠了就去下一個地方。
找人有技巧:新潮的地方會遇到能講英語的人,傳統的地方能遇到不同階層的人,飯館、咖啡館、酒吧,網絡平臺……想用多維度視角碰撞出一個更廣闊的圖景,他身上依然保留着媒體公共性寫作的塑造,“我從來就沒想寫我自己在中亞怎麼着了,本意還是通過我的經歷和視角反映歷史與世界的流動軌跡和風向,反映中亞這片區域的人心和麪貌。”
抵達成了一切的意義。爲了寫作,旅行被削減了純粹出遊時的輕鬆,但推着他路上不斷和人“套瓷”,問出那些當記者時無法問出口和追問的話,外國遊客的身份也讓他收穫不少坦誠回答。找不到人時,他也有點沮喪、着急。行程結束後還有大量素材要整理成文,核試驗場那篇成稿後他又改了一個月,最後半夜醒來都在背裏面的話。
他在杜尚別的一週如局外人般在外圍盤旋,但寫作中又打撈起很多一閃而過的瞬間,最後成了書裏流傳最廣的一篇。那位“幸運”在申請中國大學時,面試官因爲劉子超的文章認出了幸運,現在幸運在北京留學。
直到日落,我們還是沒找到黑山頭古城。
這天我在路上睡着了好幾次,他也停車睡了會兒。“是不是路上風景太單調了?”他問,草原在窗外搖搖晃晃,綠到泛黃。
“一個人的時候更難熬啊。”他的平時旅行大多都這樣,“非常容易疲倦,非常容易覺得無聊。但旅行作爲一種工作的話,它就是一種常態。”車停路斷、定好的住處沒了是常事,偶爾暴風雪在天山深林迷路,夜裏差點一腳跌進大河,前一天經過的地方出現ISIS碾殺事件。但更難的是那些要在一瞬間下的決定,這個決定往往會影響到最後所有事的呈現。這比看書學俄語做行程計劃都難。
書裏沒寫過他這些遲疑,“這有什麼可說的呢?都是一瞬裏自己的決定。而且,操,這跟別人有什麼關係,我這點屁事跟別人有什麼關係?”他社交網絡也完全隱形。
在中亞的顛簸路上,他有時和妻子、父母幾天不聯繫,家人們也不會聯繫他。“我一直都是這個性格,自己可以照顧自己。我沒‘被關心’這個需求,別人也不是非有這個需求不可。”
中亞的城市之間,還有許多荒涼的陌生地方,一次司機繞路把他放在自己親戚民宿前,兩側光禿禿的石山間,騎小毛驢的少年緩緩走來和他招手,沒人認識他,誰也不在意他,他也可以成爲任何人,旅行者置身其間,又有超然世外的特權。“這就是世界真實的樣子,充滿瑣碎的細節,而我用盡所能來理解它們——這讓我感到自由。”

“每次在旅行時我都有種恍惚,生命像一場幻覺。”這天我們又回到額爾古納,晚飯後喝酒,我說,“有時我甚至都不太相信自己在這一刻看見的、感受到的,因爲你知道你的寫作可以篡改回憶,好像你當下受的真實的苦是不重要的,你寫下的東西纔會刻在生命裏。
“是的,我也這麼想。因爲其實很多對話一晃而過,你還沒來得及反應就過去了。實際上,日後寫作會像鍊金術一樣,一點點提煉出那些無聊裏一閃而過的元素,讓你發現那些事的真正意義。”他獲取現實世界“支點”的過程就是寫作,如果不能以寫作這一艱苦方式對所見所聞所想加以確認,那所有發生的都會消散。
他說起70多歲還在旅行和寫作的保羅·索魯、奈保爾,原計劃接下來要寫的環黑海和環地中海,現在哪條路線能成就先去哪兒。“我也想七八十還在走,還繼續寫。”
書裏的行程到了盡頭,這晚我讀到他從自己26歲時在霍爾果斯口岸探望的另一頭走了出來。穿過十年時間,路過一個個岔口,被抹去遲疑和疲倦的22萬字長路一句收尾——“我走出海關大樓,穿過空曠的廣場,回頭眺望天山。”
失落的衛星
我們的行程到了盡頭。竟然到了公園,滿洲里市,在蘇聯紅軍烈士公園裏紅星與戰士雕塑的背影裏,“我覺得你在中亞這本比你《午夜》時和人親近了很多。”有一搭沒一搭地聊。
“是嗎?我其實跟好多人都還有聯繫,如果明年能去,我可能還去找他們玩兒。不想人走了就沒信了,我不想讓他們有這種失落感。”這幾天,他還在和吉爾吉斯坦遇到的人聊天。我們坐在長椅各拿一瓶啤酒,一瓶沒開,一瓶空了。

這糟糕的一年。今年我也還是在當記者,新聞千變萬瞬,有種什麼也抓不住的徒勞。劉子超今年在家譯書和改小說,去年開始寫的一個記者去歐洲領獎沿途見聞的小說,今年國際形勢疫情下急劇一擰,那些烏托邦色彩的故事竟快成了新聞內容了——“我感覺我要發黴了。”“我也是憋得難受。”同行能敲定的原因是兩個人都想出去透透氣,恰好湊上,明朝散去。
暮色中,白天散落四方的遊客都匯聚到了滿洲里這家最有名的俄羅斯餐廳前,居民和遊客在街上來來往往,我們是其中兩個。突然一大朵煙花騰空,炮響聲巨,煙花接連不斷,一時間街上所有人都駐足望向煙花不斷消失又重新騰空的同一個方向。
“像新年!”他轉回頭望我喊。“是啊!”我也喊。
又一大朵騰空,“新年快樂!”
*本文原載於GQ報道,本文有刪減。原文戳→:公路旅行:和旅行作家劉子超一起穿過大興安嶺

版權說明:
本文原載於【GQ報道】,經授權後轉載
採訪、撰文:歐陽詩蕾
編輯:陳遠
圖片:歐陽詩蕾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