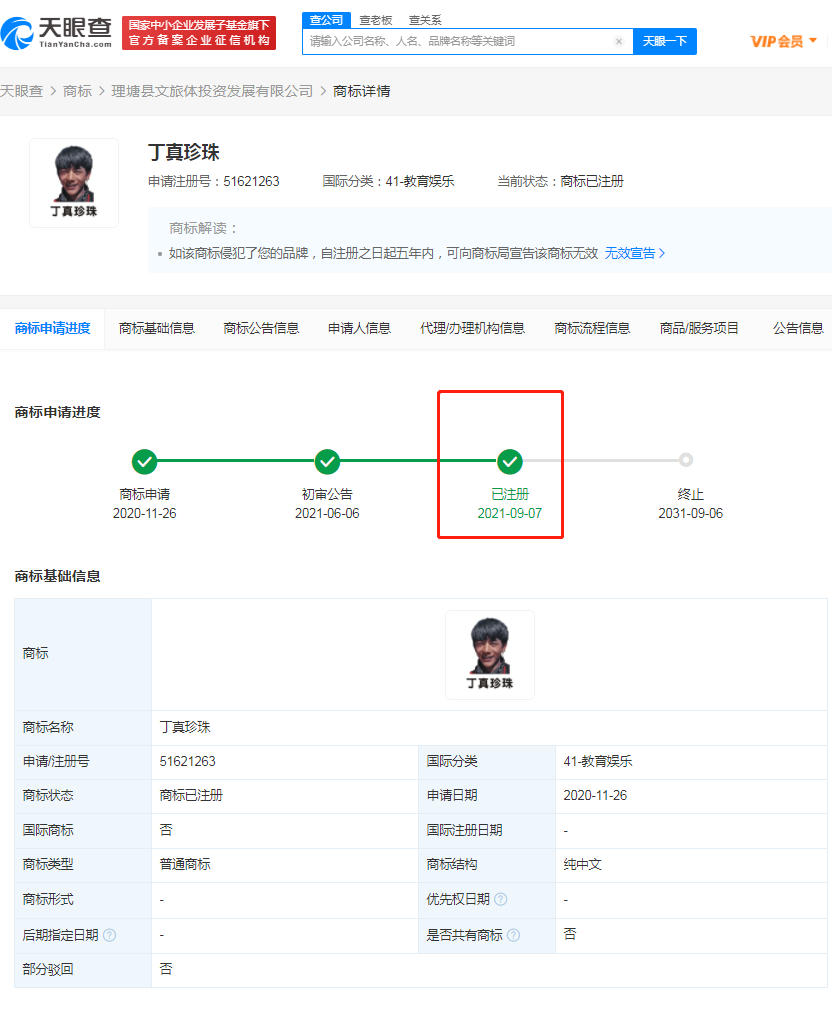再看丁真:一個“高高原”縣城的試驗與破冰
原標題:再看丁真:一個“高高原”縣城的試驗與破冰
每經記者 朱玫潔 每經編輯 張建
進入2020年12月,青藏高原的季風凜冽地刮過理塘,天橋上的人幾乎難以站穩。村子裏鮮見人影,村民們都窩進屋子裏避寒,但在縣城的仁康古街上,還能看見走幾步就要吸口氧氣的外地人——爲了丁真而來。
抓住2020的尾巴,丁真成了“頂流”,家鄉理塘隨之沾光。在中國超過1400個縣城中,如果沒有丁真的出現,很多人對理塘也許至今聞所未聞。
超出人們想象的是,這座海拔超過4000米、2020年初才摘掉“貧困縣”帽子的小縣城,理念開放、反應快速,把流量導向文旅,展開精準營銷。
2020年12月23日,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文旅部公開爲“丁真現象”點贊,認爲網紅通過直播、短視頻對當地文化旅遊產生了生動傳播效果,提升了當地旅遊產品吸引力。
走進理塘,開在傳統藏寨裏的咖啡館、餐廳、精釀啤酒館和精品民宿,既有藏族風情,又與都市消費接軌,很容易令從大城市遠道而來的遊客感到意外。皮膚黝黑、輪廓精緻的藏族女孩,還會熟練地詢問客人咖啡濃度:“你要single還是double?”
穿梭在覈心景區勒通古鎮上,轉角就可能遇到一座微型博物館,布展水平甚至不輸許多大城市的展覽。
在理塘,不少當地人篤定,“沒有丁真也會有卓瑪”,“理塘早晚得火”。丁真的走紅,只是一場“偶然中的必然”。這也被看作一次“壓力測試”,檢驗了這些年理塘的文旅發展成果。
這背後的重要“推手”杜冬,把理塘當下的探索視爲一場“高高原”上的旅遊試驗。從杜冬到丁真,一羣或主動或被動捲入的“破冰者”,正通過各自不同的嘗試和努力,推動這場試驗走得更遠。

理塘縣濯桑鄉黨委書記扎西拉姆 每經記者 張建 攝
破 冰
2020年12月初,汪堆帶着兩位投資者到格聶雪山看一個溫泉酒店項目,在冒着熱氣的泉眼附近,幾座木屋已建好雛形。這幾年,汪堆卸任理塘縣文旅局局長後,擔任格聶景區管理公司董事長。對這位老文旅人來說,格聶旅遊開發做了20年,“現在終於起步了”。
格聶雪山位於理塘縣熱柯鄉,是徒步愛好者心中的聖地,但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並未出圈。
和丁真一樣,汪堆也出生在格聶腳下。他喜歡以“格聶之子”稱呼自己:“我是格聶人,我就希望旅遊做起來後能把老百姓的生活也帶起來。”
對於丁真走紅,汪堆一開始並不理解——比他好看的小夥子多的是。“任何人都不適應,我也不適應。”他停頓了一下,仔細想了想,又覺得這是偶然中的必然:“理塘這兩年旅遊搞起來了,去格聶採風拍視頻的人就多了,如果不是那個拍紀錄片(照片)的,怎麼會有丁真?”
至少近五年,這座GDP僅在10億元上下的高原縣城,把文旅產業擺在重要的戰略位置。在財政並不寬裕的情況下,爲了建設勒通古鎮4A景區一期,2018年就投入近8000萬元。
截至2019底,理塘縣常住人口7.3萬,其中農業人口6.2萬。高原縣城“靠山喫飯”,居民主要收入來源是蟲草和松茸——4~5月挖蟲草,6~8月撿松茸,或者倚賴高山草甸餵養犛牛。高原上種植農作物侷限性很大,只能種植青稞、油菜等耐寒作物。旅遊,成了爲數不多的發展選擇之一,只是起步維艱。
身處318國道旁的理塘,平均海拔4014米,貧困率一度高達38%。6年前,理塘整個縣城能做到24小時提供熱水的賓館屈指可數。彼時去格聶,到達丁真家鄉下則通村後,要繼續騎馬前進至少10公里。以前,汪堆帶人去考察格聶旅遊線路,就不得不經常充當馬伕。
這幾年,當地道路水電一類基礎設施短板逐漸補上,村村通了水泥路,縣城也打造出勒通古鎮這樣的主要景區。2020年2月,理塘“摘帽”成功。但直到今天,駕車從理塘前往格聶之眼,依然需要5個小時,90%的路段沒有信號。
除此之外,理塘的高原地勢也頗爲特殊,成爲影響當地旅遊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甘孜州州府康定,如果有遊客要去理塘,可能會被當地人提醒,“小心,缺氧。”
“區位太極端了。”理塘旅投公司總經理杜冬說,拉薩平均海拔3700米,理塘比它還高。相比普通的高原旅遊,他把理塘的動作視爲“高高原上的旅遊試驗”。
“這種‘高高原旅遊’別的地方有沒有出現過?沒有。可能珠峯大本營有,但這不一樣,那是珠峯。有合適的參照樣本嗎?沒有。我們做的事情就是破冰性質的。”杜冬自問自答。
之前,理塘想了很多辦法來“對沖”高反的刻板印象,比如推出“天空之城”的標語,把它印在路牌上、刻在山坡上,但效果甚微。2020年11月之後,杜冬不用再擔心這個問題了——理塘沒有珠穆朗瑪峯,但有了站在流量巔峯的丁真。“把理塘‘高反’的標籤撕下來,丁真一個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杜冬說。
執 念
現在,丁真的工作地點是倉央嘉措微型博物館,一座由老房子改造而來的玻璃房。博物館外,能看見極其壯觀的“快遞山”。在之前網上熱傳的視頻中,丁真和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坐在這裏拆網友寄來的書。在他們頭上,每盞燈底部都印着一個藏族文化名人的名字。這是杜冬的創意,寓意“像燈一樣點亮文化自信”。
文化,是理塘旅遊的“執念”。許多理塘文旅人都明白,丁真火,恰恰是火在文化上。“大家喜歡的是丁真的笑容,丁真的笑容背後是他的村子。”仁康古街那木薩餐廳老闆諾爾布說,理塘有很多這樣的笑容,是這裏的山水養育出來的,也是這裏的文化養育出來的。
在諾爾布看來,如果一個人因爲喜歡丁真的笑容來到理塘,他領略到高原的藍天白雲、格聶雪山、毛埡草原,感受到這裏的文化,體驗到這裏的生活,那會帶來積極正面的反饋。但如果來了發現這裏什麼都沒有,他可能對丁真也會失望。
汪堆說,如果(丁真)要繼續(火)下去,他的淳樸、他的原生態,纔是真的。理塘要在景區雲集的318國道線上做旅遊,必須突出當地文化風貌,進行保護性開發。
理塘縣城主要景區是勒通古鎮,由理塘老城區改造而來,包括仁康古街、仁康古屋,以及千戶藏寨——甘孜州最大的藏寨羣,擁有13個藏寨,4000餘戶藏房,2019年成爲國家4A級旅遊景區。2020年,仁康古街專門引進包括咖啡館、民宿、餐廳等業態在內的8家品質商鋪,開在改造後的藏寨裏,既有藏族文化風情,又與都市消費偏好接軌。
“沒有咖啡館,怎麼做旅遊?”回到家鄉理塘之前,“大丁真”在外打拼了20多年。跟丁真一樣,他也出生在格聶雪山腳下,算下來還是丁真的遠房叔叔。
他是理塘第一批走出去從事旅遊業的人。上世紀90年代,他到雲南香格里拉“當學徒”。彼時,香格里拉旅遊業剛起步,國內外遊客蜂擁而至。很多人第一年被當地建築吸引,第二年、第三年再來,發現原來的老屋消失,水泥建築拔地而起,不禁發出“so bad”的感嘆。
有遊客因爲訂不到有當地特色民宿,乾脆取消行程。“我提出換成另一家五星級酒店,客人覺得(跟其他地方)差不多,就不來了。”“大丁真”回憶。
在外打拼教會他最重要的一點是,保護和突出當地的高原風貌和獨特文化,就是理塘的核心競爭力。
現在,“大丁真”會給理塘本地酒店做培訓,也給理塘民宿做設計——從櫃子到門簾,都遵循本地特色。他經常跟本地居民講,要保護文化、保護生態。“一定要讓大家都知道這些(理念)。”他說,要像朋友聊天那樣不停地去講。
專 業
這樣的理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2018年,理塘請來了一位“關鍵先生”——理塘旅投公司總經理杜冬。
在成爲理塘旅遊“推手”之前,杜冬的標籤是“做文化研究的人”。當時,他剛完成少數民族史方向的碩士學業,原本計劃“十年做翻譯、十年做作者”,身上的文人氣息再明顯不過。
爲何理塘會“選中”自己?杜冬也不太明白。不過,早些年杜冬爲全球著名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西藏系列供稿時,就覺得藏區旅遊比較粗糙單一,以自然風光爲主,碰上天氣不好,體驗就大打折扣。過去,也有景區出現過無序開發、破壞文化生態的情況。杜冬希望,有一種“專家式玩法”,這與理塘想做文化特色的理念恰好吻合。“我們就是要繞開前人走過的彎路。”汪堆說。
目前來看,這個搞文化出身的總經理,至少爲理塘做了兩件大事。
其一,是牽線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人類學研究團隊,請他們到理塘做口述史研究,挖掘和梳理當地文化脈絡;其二,是帶團隊着手建設改造多個微型博物館,把理塘博物館集羣的框架搭了起來。
“能原汁原味,就原汁原味。”在仁康古街上,當地政府租賃整理出不少老建築,不用新修場地,杜冬只需負責空間改造和內容設計。“文化策劃我不擔心,設計我不擔心(能找到設計師),改造也不很擔心。”在杜冬看來,“預算可控、週期可控,大量環節我們自己控制着,這種事可以做。”
2019年至2020年間,康巴人博物館、石刻館、唐卡編織黑陶館、喜馬拉雅之聲微博物館、318旅行記憶博物館、倉央嘉措微型博物館等一一落成,到現在,勒通古鎮已有11家博物館開門營業,還有一批在籌備中。
如今,穿梭在古鎮上,轉角就可能遇到一座博物館,它們往往由一戶藏式院落改建而成,進門後穿過院子,上樓是極具特色的陡峭木梯。仔細觀展,內容之精良讓人驚訝——大大超出人們對一個偏遠小縣城的預期。
理塘的策展團隊“實力不凡”,其中不少是通過杜冬牽線搭橋從外地請來的。
比如,喜馬拉雅之聲微博物館牆壁上,有一排耳機,可以聽見極具理塘特色的生活:擠牛奶、搖籃曲、放犛牛等。
這些錄音工作由秦思源帶隊完成——一位專注於聲音的知名藝術家。他十餘年前就曾擔任位於北京798的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副館長兼首席策展人。2019年夏天,秦思源團隊來到理塘,用半個多月時間,奔波於牧場、田地、古鎮、寺廟採集聲音。
旅居法國的設計師五之是喜馬拉雅之聲微博物館另一個幕後主力。作爲一名藏族文化的追逐者,2019年初,杜冬邀請她到理塘爲博物館做設計。
還有爲理塘留下無數宣傳照片和明信片素材的攝影師大刀,在理塘開過數年客棧、又轉型爲318旅行記憶博物館(以下簡稱318博物館)主理人的孔二,他們把自己稱爲“一羣無法徹底離開的人,一羣執着把川藏當成故鄉的人”。
2020年,一位20多歲的川藏線驢友根根,又受孔二邀請,來到318博物館做運營,成爲新的理塘“歸人”。
杜冬也是一名理塘的“歸人”,14年前,他就與理塘結下緣分。“我們就像理塘的窗口。”杜冬評價像他一樣的這羣外鄉人時說。
下 沉
“這兩年,全縣都在提旅遊。”在理塘縣濯桑鄉黨委書記扎西拉姆看來,如今,發展旅遊的理念,早已下沉到理塘各地。
前段時間,理塘就有一位村書記任敏,因爲“發動”作家桑格格爲村裏帶貨在網上引發關注。她其實正是任職於濯桑鄉下轄的一個村子,與扎西還是室友。兩人平時一起晨練時,還會專門討論怎麼做旅遊開發。
濯桑鄉位於227國道旁,距離理塘縣城約45公里。
受縣上“博物館熱”帶動,濯桑鄉也籌建了微型博物館。因爲經費有限,濯桑鄉微型博物館在空間上並未做太多設計和改造,二樓的屋頂規整地拉上一層紅藍塑料布,吊上幾盞白熾燈,展櫃也是二手的。可以說它很簡陋,但又因爲房屋本身的歷史感,使這種簡陋變成一種原汁原味。“很有味道。”扎西特別指出。
行走在各個老式院落之間,一面土牆很有味道,一片屋瓦也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四個字,是扎西重複最多的一句話。
這兩年,濯桑鄉專門買下一些村裏的老建築,用紅色噴漆打上標號,打算在未來做一些公共空間、民宿等配套。扎西心裏很清楚,這些保存完好的老屋、村落古樸的風貌,是當地發展旅遊的最大資本。
爲此,她甚至說服村民不修水泥房。“主要有點攀比心態,有些錢就想修水泥房子。”扎西說,“老百姓一般看眼前,但鄉幹部應該要看得更長遠一點。”
扎西還說,她現在在學英語,爲了更好更廣地介紹家鄉。“縣上鼓勵發展旅遊,很多事情我們敢放開想、放手做。”
比如,沿着227國道直行,濯桑鄉兩側房屋牆壁上,融合了嘻哈和地域文化元素的大幅塗鴉,在一片綿延的草原風光中很是醒目。“我希望讓經過的遊客注意到這裏,踩一腳剎車。”扎西說。一開始,有鄉幹部接受不了塗鴉。權衡之後,扎西認爲,還是得做。
現在,濯桑鄉規整出多處可參觀的地方,許多細節都是當地基層幹部自己動手施工。
比如,60多年前的鄉政府大院,現在只剩四周土牆和當年種下的一棵蘋果樹,他們將這裏打造出來作爲景點“草木間”,夏天可以坐着喝茶,兩旁有基層幹部自己弄的花草叢。
“我們隔十幾天、一個月去撒不同的草種,在夏天會不間斷地有花依次開放。”這種設計是模仿了毛埡草原,扎西說,自己從小在理塘長大,知道這些花草的季節,而毛埡草原上自然形成的植被就是這樣。
2020年旅遊旺季期間,“草木間”人流量不錯,本地居民通過賣酸奶、藏餐,也嚐到了旅遊的甜頭。還有一家經營銀飾的店鋪找上門,想入駐“草木間”,儘管零售業可以很快帶來消費增長,扎西仔細想了想還是拒絕了。
“我想把這塊地做成青年旅社。”扎西用手比劃着。她的考慮是,青年旅社雖然消費不高,但有活力和氛圍,如果能吸引年輕人到這裏,不僅旅遊名氣能傳播出去,還有更多年輕人能和村子形成交流。溝 通
一開始,扎西的英語學習小組只有3個人。她和另一個在縣上任職的幹部是學生,還有一位免費授課的老師。現在,學習小組裏的學生已經發展到十幾個。
另一個在這兩年間壯大的學習小組是普通話學習羣——裏面有理塘本地的教師、公務員,也有四川廣播電視臺主持人等普通話水平很好的成員。這個羣現在有300多人,每天都有理塘人在羣裏發自己的朗讀視頻,讓大家幫忙糾錯指正。
羣是理塘縣普通話語言文字協會組織起來的。協會成立於2019年,成立初衷是爲了推動語言文字脫貧工作。
說起協會由來,會長黃威說,他在大學期間就創辦過民族文化推廣社團。他發現,身邊的同學會問一些關於少數民族的奇怪問題,他能感覺到這些問題並非惡意,而是因爲了解太少、存在刻板印象。多年後,機緣巧合,理塘縣普通話語言文字協會得以成立,雖然形式不同,但初衷是一脈相承的——做一些促進溝通的事情,讓外界更瞭解理塘,也讓理塘更瞭解外界。
平時在協會奔波做事的主要有12個人,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他們大多是本地公務員、教師等,都是兼職,用下班時間從另一個維度改變理塘。
洛絨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訴城叔,週末是他們工作的主要時段。這兩年,協會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到鄉里進行教師和居民的普通話摸底測評,建立教師普通話水平數據庫,也順帶推廣微信學習羣。如果教師普通話水平低於三乙,會被理塘教育局方面要求參加專門的培訓班。
理塘鄉村地廣人稀,遠一些的村子駕車5個小時才能到達。爲了提高效率,每次下鄉,他們一般是12個人一起出動,開兩輛車,到了鄉上散開負責不同的學校。時常早上7點集合,晚上9、10點回來,跑上一天,把一個鄉做完。
做測評縣裏有補貼,每人100元/天。不過,這件事明顯不掙錢,車、油費、用餐都是自己協調和負擔。“都是自己有興趣,然後一起做事。”洛絨說,山路崎嶇,協會里很多老師暈車,有的一路吐過去,又一路吐回來,到鄉上人都沒精神了,但還是堅持做完事情,“大家覺得值得”。
2020年,儘管受疫情影響,12位年輕人還是去了14個鄉進行摸底測評。因爲氣候原因,冬季各方面活動停得早,剩下的摸底測評只能留待明年繼續。不下鄉的週末,協會會不定期組織普通話沙龍,也會邀請離縣城比較近的鄉鎮教師參加,地點就在喜馬拉雅之聲微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現在交給普通話協會運營管理,洛絨是主要負責人。比起“丁真熱”,洛絨似乎更關注關乎本地內生髮展的公益事業,比如語言脫貧,比如博物館。最近一個月,原本博物館已經歇業,爲了各路來的媒體,他又重新開門,做起解讀員,聊聲音博物館、普通話協會和理塘旅遊。
踉 蹌
在理塘自上而下推動旅遊業快速與前沿接軌的同時,跟丁真一樣,更多本地年輕人以一種踉蹌的姿態,被推進了旅遊業的大門。
從外面“闖入”的杜冬,花了半年時間適應理塘的工作節奏和工作方式。
“痛苦!痛苦!痛苦!”從2018年10月出任理塘旅投公司總經理至今,回憶起剛來工作時的情景,杜冬連嘆三聲。
首要困難不是思路決策,而是執行層面做不了事。“這個公司不像我們想像中成型的公司體制模樣,它是一個公司的雛形,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執行力不夠,孩子們(年輕員工)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杜冬說。
第一年,杜冬在基層行政事務上花費了巨大精力。“有人問我犛牛喫花了怎麼辦?老頭河邊撒尿了怎麼辦?我不知道怎麼辦!”杜冬一提起來就語速加快,用手不斷撓頭,“還有,公司的硬盤丟了,張三說給李四了,李四說給張三了,沒有記錄。一罵兩個人都開始哭。怎麼辦?”
實際上,接受這份工作前,杜冬已有預期會很痛苦,第一是因爲高原環境,第二是這裏工作效率比不上其他地方。走馬上任半年後,杜冬決定接受現實,“大規模地改變不太可能,先做一些繡花的功夫。”於是,他開始着手推動改造微型博物館。
如果沒有一開始的這些消耗,杜冬的“高高原旅遊試驗”或許可以推進得更快,但這注定是難以避開的一關。“不管你在理塘還是別的什麼地方(類似區位條件),這種(基層行政與項目發展混雜)情況應該都會有。”他說。
反過來看,公司的年輕人也在適應杜冬。
在理塘,年輕人心中最好的工作是公務員,學歷不高的就去服務行業,少數懂旅遊的可以做導遊,還有一些人外出務工。對他們來說,可選擇、有意思的工作並不多。在旅投公司上班的年輕人,大多隻把這裏當作“跳板”,曾經一度到了公務員考試月,幾乎全公司的人都去參加考試了。
磨合到第二年,情況逐漸明朗。杜冬不僅覺得團隊好帶多了,有的項目甚至可以放手給孩子們去做,旅投公司的年輕人也開始覺得有奔頭和成就感。
剛開始做微型博物館時,杜冬刻意讓員工一起參加施工。“他們也很痛苦,又要到公司上班又要做博物館。”杜冬說,“但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的,讓員工看到他們自己是這個東西(博物館)的一部分。”
2020年,旅投公司4個年輕人到了成都,成爲第一批出去培訓的人。與他們想象的對着PPT上課不同,成都的旅遊培訓要洗杯子洗碗,如同去做了一次服務員。“培訓就是這樣,先感受什麼是城市的氛圍,什麼是城市的節奏,再來談別的東西,否則都沒用。”杜冬說。
回來後,這些年輕人開始知道可以上網搜索攻略,學會了寫方案,還端上了咖啡,用上了釘釘考勤。“這對我們來說是前進的極大的一步。”杜冬感嘆。
可 能
杜冬常說,在理塘兩年,教給這裏的孩子兩樣東西,一個是咖啡,一個是筆記本電腦。咖啡讓人隨時辦公,筆記本讓人隨地辦公。
新的人羣、新的理念、新的事物,像無數涓涓細流匯入理塘,又如水波一般盪漾開去。微型博物館“熱”起來後,有本地老人來問:“這裏收不收古董?”儘管老人對博物館的理解讓杜冬哭笑不得,但“博物館”這個充滿都市氣息的概念,正在走進本地人的生活。
前段時間,318博物館運營負責人根根迎來一羣小客人——幼兒園的學生,紅撲撲的臉蛋讓這位河南小夥感到“心都化了”。這裏的客人還包括寺廟裏的喇嘛、好奇的居民。根根估測,來這裏的本地人大概佔四成。
平時,博物館旁邊一位高高瘦瘦的藏族小夥子喜歡來這裏玩。他在附近做保安,在陌生人面前很靦腆。與根根他們熟了,即使沒太多事情可說,也喜歡來待一會兒,拉幾句家常。
還有4位藏族阿媽在318博物館上班,她們在這裏參與“媽媽樹”工作坊項目,專門從事“妮熱”牛羊毛編織技藝——這是當地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而項目的初衷,是探索出一條當地婦女就業的路徑。
她們每天在庭院的陽光棚裏紡線,在博物館一樓繡圖案,最後做成抱枕和隨身包。“阿姨你腿這裏繡錯了。”根根和一位阿媽討論皮卡丘的圖案。顯然,對於這位藏族阿媽來說,皮卡丘這種“生物”的構造不太好理解。
“(阿媽們)這邊離不開人。”根根說。儘管她們是技藝傳承者,但對於色彩、圖案的審美,與“外面”有差異。早期摸索後,2020年9月左右,一位女設計師應邀前來,工作坊運轉才終於走上正軌。很快,繡着青山、民居和皮卡丘的“妮熱”靠枕套,一起上架了。
根根說,這些產品在博物館和相關社羣中售賣,初步銷路還不錯。順利的話,“媽媽樹”工作坊未來還要擴大,形成一種專業模式。
根根從以前工作的地方離職時,並不缺邀約,在318博物館工作薪資不高、也忙,但他做得很開心。
他說,在理塘上班,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更談不上打卡。人的身心沒有那種做“螺絲釘”的感覺。在博物館裏,根根每天碰見不同的人,跟他們打交道,讓他覺得待在理塘的老房子裏,眼界反倒比在城市做白領來得開闊:“有的事情,以前覺得特別在意,現在一下看開了。”
到理塘之前,根根漂了一頭紫發,現在早已褪色。他在這裏買了3套民族服裝、學會了“妮熱”染線,甚至有人把他認成本地人,用藏語向他問路。
12月初,女設計師離開了,她跟理塘的關係是有事了就過來幫忙,就像候鳥一樣。根根過年也要回家,但他還是會回來,“至少等博物館運營走上正軌”。
未來“高高原旅遊試驗”能不能成功?現在看來一切皆有可能。“丁真效應”的加持,讓一切更加樂觀。
丁真在偶然間被推入互聯網,繼而像一個陀螺,迅速被捲入進來。或者說,本來就是理塘推進旅遊的風浪將丁真颳起,最後又是這艘“高高原旅遊試驗”的大船,接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