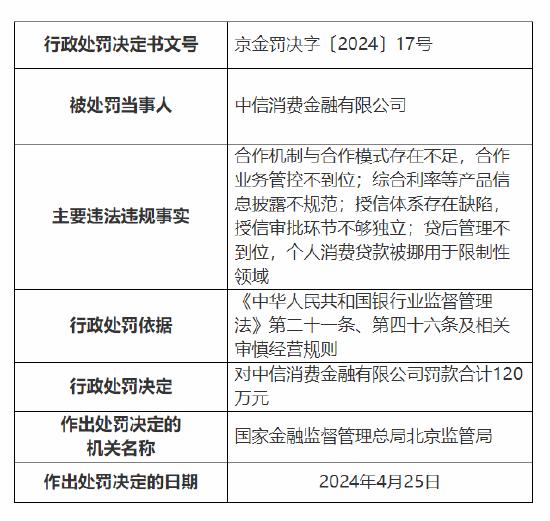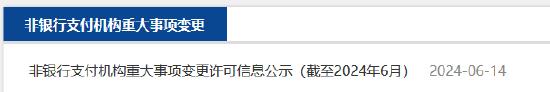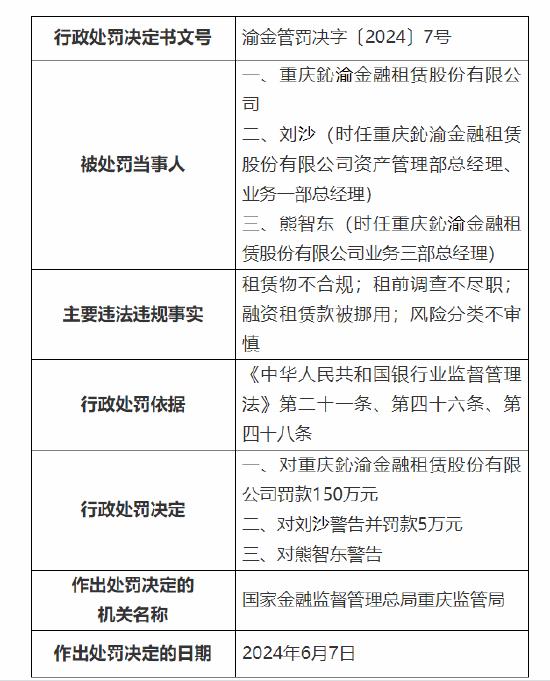唯品會等多家企業“拋棄”網絡小貸牌照 行業撤退潮來臨
原標題:唯品會、華潤等多家企業‘拋棄’網絡小貸牌照,行業撤退潮來臨
近期,多家小貸公司被股東剝離、轉讓,小貸公司撤退步伐在加快。
比如,唯品會剝離旗下一家小貸公司、世聯行8.06億出售世聯小貸所持信貸資產、華潤擬轉讓旗下小貸股權、君正小貸二股東退出、赫美拍賣持有的赫美小貸股權,奧馬電器擬轉讓子公司寧夏小貸......
此外,有從業者向新流財經透露,某傢俱有外資股東背景的小貸公司以及重慶某家累計放款近600億元的小貸公司也正在尋找新的買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放棄”的公司多數爲網絡小貸公司,曾經的“香餑餑”似乎突然之間變成了“燙手的山芋”。
但在多數玩家紛紛撤退的同時,山東首家網絡小貸牌照——山東國晟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於2020年12月24日正式成立,註冊資本10億元。在業內人士看來,目前網絡小貸的監管步調基本已經確認,國晟小貸成立就是建立在監管基礎之上的。
經歷了多年的角逐之後,小貸行業正從各路玩家瘋狂湧入到逐步迴歸冷靜。
政策寬鬆、利潤可觀,玩家瘋狂湧入
時間倒回到2010年,我國第一家網絡小貸公司——阿里小貸正式誕生。彼時,小貸行業還處在傳統小貸公司數量迅速擴張的時期。
2015年,傳統小貸公司數量一路擴張至1.2萬家之多。但在數量激增的背後,利率過高、催收不當等問題慢慢浮出水面,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逐漸增多。
與此同時,隨着P2P和現金貸等互聯網金融迅速崛起,網絡小貸憑藉流量、技術以及展業範圍等優勢在小額貸款行業中異軍突起,也因此掀起了申請網絡小貸牌照的熱潮。
據統計,網絡小貸市場於2014年加速啓動,2016年開始大幅增加,共有47家網絡小貸公司成立,2017年這一數字達到了71家。
其中發起設立的股東各式各樣,包括上市公司、互聯網公司、大型傳統線下機構等。文首部分提到的玩家,也大多在這個時候入局。
與其他具備放貸資質的銀行、消費金融牌照相比,網絡小貸能既打破地域限制,在全國範圍內展業,門檻又相對低,性價比較高,這成爲很多公司佈局金融業務的首選。
當然,各路玩家瘋狂湧入小貸市場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利潤可觀。
以海爾集團旗下網絡小貸公司爲例,經過了幾年的發展,據公開數據顯示,2015年-2017年,海爾小貸分別實現淨利潤4464.17萬元、9852.23萬元和1.38億元;放款量也在逐年攀升,2015年-2017年分別放款41.7億元、122.49億元、181.29億元,放款額年複合增長率108.51%,發展速度可見一斑。
對於想要將金融作爲一項新的收入來源的企業而言,這無疑是一塊充滿誘惑力的大蛋糕。
政策寬鬆、門檻不高、利潤可觀,各自在主業領域有着充分實力的玩家,對佈局金融業務充滿了熱情。
大家都想分一杯羹。
直到2017年底,受現金貸風波影響,監管踩下急剎車。
2017年11月,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特急文件《關於立即暫停批設網絡小額貸款公司的通知》,由於近年來,有些地區陸續批設了網絡小額貸款公司或允許小額貸款公司開展網絡小額貸款業務,部分機構開展的“現金貸”業務存在較大風險隱患,要求立即暫停批設網絡小額貸款。
據統計,截至2017年11月21日,市場上共有249張網絡小貸牌照,完成工商註冊的有229張。
儘管只有200餘張牌照,但是網絡小貸卻憑藉助貸、聯合貸等模式成爲了近幾年行業內不可忽視的力量,攪動着互聯網金融市場整池的春水。
外部政策、內部治理不善雙重夾擊,企業撤退加速
2020年的疫情讓包括小貸公司在內的消費金融行業整體承壓。“一開始我們認爲這或許是在2020年遇到的最大困難,但沒想到,我們低估了2020年。”一位網絡小貸從業者顧何表示。
2020年8月底,最高人民法院修訂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爲4倍LPR,即年化利率15.4%,較此前24%和36%的利率基準大幅下調。
同年11月,《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出爐,對屬地經營、聯合貸、股東參股數量等方面做了詳細規定。最重要的是,行業准入門檻比以往大大提高了,足以將一衆小貸平臺拒之門外。
可以預見的是,新規落地後,很多小貸公司將清退或者侷限於當地,網絡小貸的牌照價值也會大大縮水。
但在顧何看來,監管收緊是一方面,小貸公司內部治理是撤退的另一重要原因。
自從2017年底,監管暫停網絡小貸牌照審批之後,行業經過了幾年平穩的發展期。不過由於各家定位、發展戰略各不相同,差異越來越明顯,有的成爲了集團撬動萬億元估值的基石,有的則年虧損幾億元。
“一些小貸公司屬於跨界做金融,領導層來自大股東一方,對金融並不是十分了解,發展方向不明晰,有的甚至內部鬥爭激烈,導致金融業務難以真正發展起來。”顧何談到。
經過幾年的發展,有的旗下小貸公司仍舊處於虧損狀態,網絡小貸新規意見稿下發後,一些小貸公司股東的對其未來的發展前景和盈利能力產生了動搖。
以華潤擬清退的潤信(汕頭華僑試驗區)互聯網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爲例,2019年度,其營業收入約3270萬元,淨利潤虧損約115萬元;截至2020年10月底,營業收入約2629萬元,淨利潤虧損約3990萬元。
而其註冊註冊資本僅3億元,若要達到網絡小貸新規要求的50億元註冊資本金的要求,補足幾十億元的差距或許只能依靠股東方的支持。
當前部分網絡小貸公司都面臨同樣的尷尬,但是這已經不是三、四年前,股東們對網絡小貸抱有一腔熱情的時候了。相對於補足網絡小貸公司的資本金,運用這部分資金去獲取一張價值更高的銀行或者消費金融牌照,顯然更划算。
政策的出臺,猶如最後一根稻草,加速了這些股東們尋找其他出路的步伐。
“賺快錢”不如“細水長流”
有業內人士預計,網絡小貸新規正式出臺後, 90%以上的網絡小貸機構將因無法達到監管要求而出局。
大浪淘沙,網絡小貸史上最大規模的撤退潮來臨。
除了股東們,正在親身經歷這場撤退潮的從業者們的感受更加深刻。
“目前已經準備轉行做貸後相關業務。”一位重慶小貸從業者談到,多數從業者們還在觀望,有的則已經提前辭職謀求新的機會或者直接轉行。
儘管如此,不容置疑的是,小額貸款行業的存在具備其合理性,可以爲銀行無法觸及到的中小微企業、三農以及無法在銀行獲得信貸的次級用戶等提供金融服務,這部分市場將長久地存在,並且規模巨大。
小貸公司協會會長王非近期公開表示,小貸公司的股東要有產業投資者的耐心,要明白“賺快錢”不如“細水長流”的道理。
實際上,早在2015年十部委下發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便規定,在功能定位方面,小額貸款公司發放網絡小額貸款應當遵循小額、分散的原則,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主要服務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羣等普惠金融重點服務對象,踐行普惠金融理念,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發揮網絡小額貸款的渠道和成本優勢。
如今再縱觀整個國內小貸市場,一場洗牌期正在降臨,但留下的小貸公司或許已經有了比以往更加清晰的發展方向。
在多位小貸從業者看來,未來小貸公司在經營發展上,成爲普惠金融的補充,不誘導消費者過度負債,或許纔是生存和可持續的根本。
(以上人名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