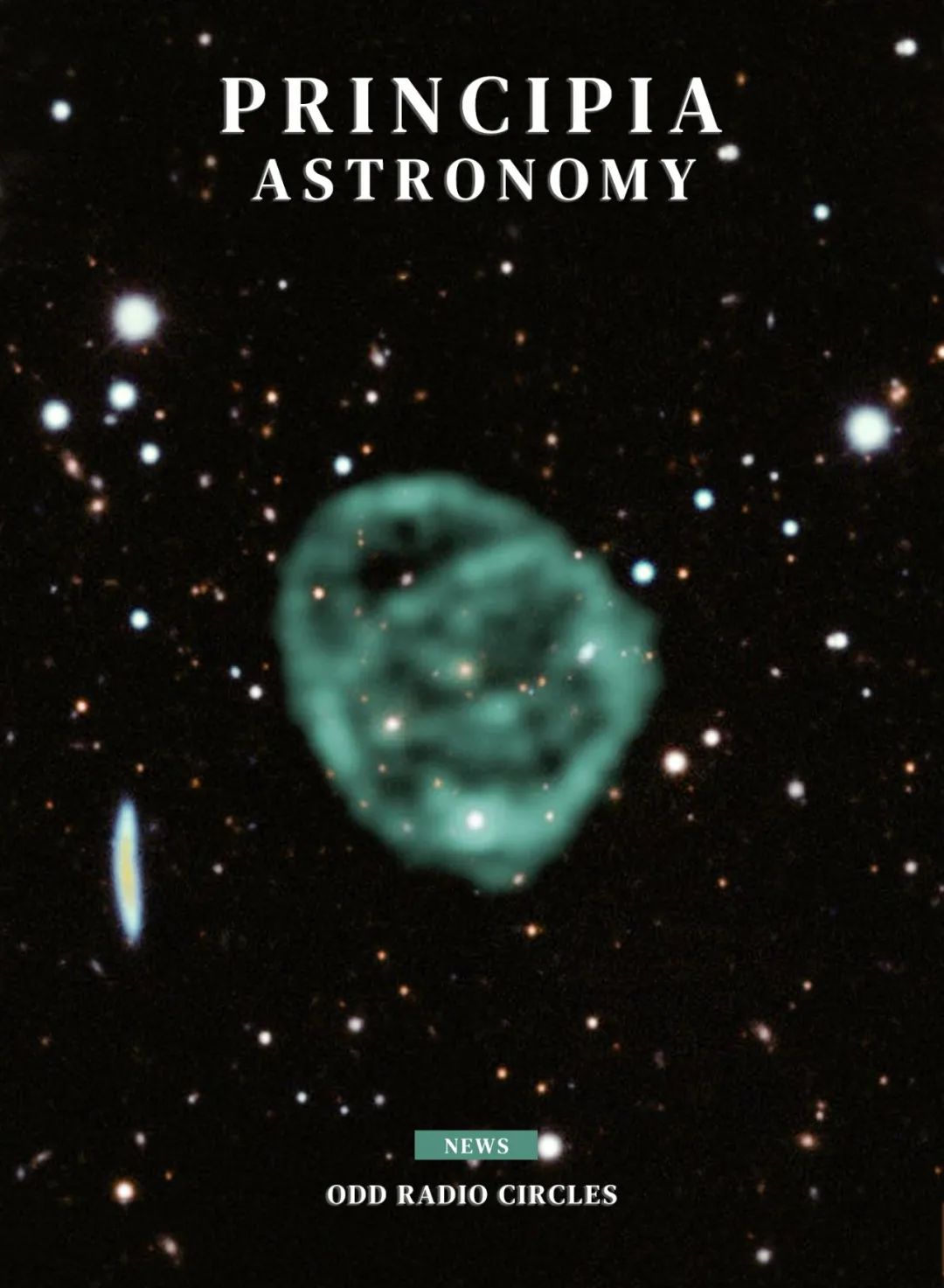追憶著名天文學家王綬琯:拉有科學夢想的青年人一把
來源:賽先生
“著名天文學家王綬琯先生於昨晚(2021年1月28日)21點37分因病辭世,享年98歲。四年前,‘賽先生天文’採訪了王先生,先生的謙虛、對LAMOST的期待以及對‘大手拉小手’的執着,令筆者難忘。2019年春,清華大學天文系成立,先生也特賜墨寶。今重發此文,以示對先生的哀悼。願先生在天國安息!” ——清華大學天文系主任毛淑德

王綬琯院士
導讀
王綬琯: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早期開創者之一。曾任北京天文臺(國家天文臺前身)臺長、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現爲名譽理事長),開創了中國射電天文觀測研究的先河,並和蘇定強院士共同設計了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LAMOST)。
在王綬琯院士94週歲生日(2017年1月15日)之際,“賽先生天文”拜訪了王先生並進行了採訪。王先生講述了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歷和舍舟問天的心路歷程,回顧了科研生涯中激情燃燒的難忘歲月,並分享了晚年開展“大手拉小手”活動的諸多感想。本文根據採訪錄音和書面採訪整理而成。
採訪 | 薛隨建(國家天文臺)、毛淑德(清華大學)
整理 | 劉國卿(清華大學)

圖1。《賽先生天文》拜訪王綬琯院士(右:王先生;左:薛隨建)
青少年經歷
賽先生:王先生,您又能做科學,又能寫詩,還很有哲學思想。我們很好奇,您的家教是怎麼樣的?您小時候的啓蒙教育是怎麼樣的?您父母對您有什麼影響?不知能否和我們聊聊您的早年經歷?
王先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狀態。我兩三歲時父親就沒有了,是母親把我帶大。那時候我除了讀私塾還有新式學堂,在母親的督促下背了好多書,我記憶中自己在學習方面始終不曾懈怠。

圖2。 馬尾海軍學校
我13歲那年,到南京去考試。我叔叔是軍官,可以保送;還有華僑和各省市也可以保送。有了保送資格,先預考,然後一起會考。我們那一屆是1936年保送去會考。我最終考取,一共100個人;現在在北京還剩一個。
賽先生:您的同學中還有一個在北京?
王先生:還有一個,年齡都是一樣的;當時是13歲,現在都是93或94。
賽先生:您剛纔提到您十三歲就讀於福建馬尾海軍學校(這所學校的前身是左宗棠創建的馬尾船政學堂)。您在那裏主要學到了哪些東西?

圖3。 王先生在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時期的照片(圖片來源:CCTV 10)
王先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因眼睛近視從學習航海改學造船。現在,我無法太好地總結那個時候的成長,但在當時我看了很多書,那時的老師跟學生很親近,什麼書都借給學生看。
舍舟問天
賽先生:王先生,您1945年去了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在那裏有沒有接觸到一些新鮮的東西?
王先生:當時在英國,我發現有很多好看的東西,包括科普的天文書籍;以前我在中國也看到一些,當然主要還是興趣使然。
賽先生:您曾經提到有一本雜誌叫《宇宙》,所以您看過那個?

圖4。 民國期間由中國天文學會出版的《宇宙》雜誌(汪景琇院士提供)
王先生:知道,那上面有很多正規的文章。比我還小一點的李元先生,他在中學時候就在寫文章了。他剛剛去世了。
賽先生:後來,您在倫敦大學天文臺做了三年天文工作,您在那裏學到了什麼?對您影響最大的天文學家是誰?
王先生:當時物理學發展得非常快、非常有趣。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像丹麥天文學家赫茨普龍(Hertzsprung)這樣的人,有很深的一些功底,以後他才做出來赫羅圖。
賽先生:對,英文是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
王先生:那時他們有些人寫的一些科普的東西很有趣。你們知不知道在英國有一位老前輩,Patrick Moore,一直做天文科普。
賽先生:知道,2010年左右他還健在。(編者注:Patrick Moore,2012年過世,享年89歲)
王先生:這種書看多了,我對天文的興趣就大了。現在不一樣了,在北京,有不少學校都有自己的天文臺(圓頂)。有現在這麼好的條件,如果再有大手來拉你的話,就是人生一個非常大的機遇了。但我那個時候,能夠有書讀,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了。
當時倫敦有格林尼治(Greenwich)天文臺,是英國皇家的,現在算是歷史文物,當時歸國家海軍管理,我去不了。還有一個倫敦大學天文臺,它有一個60公分的望遠鏡,這算是英國當時最好、最大的設備了。當時的臺長是一位老科學家,叫C.C.L。 Gregory,我就寫信給他。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老先生,當時已經快退休了。他自己做了一輩子的天體測量工作。他那個望遠鏡做三角視差最好,所以做了好多這方面的工作[3]。我跟他說,我到你天文臺做二年或者三年工作,我能不能變成一個天文學家。他鼓勵我去做,說你就來吧。
於是在1950年,Gregory給了我一個助理天文學家的職位,並給了我很多好的建議,使我得以實現這個願望。當時他的學生E.M.Burbidges 和G.R。 Burbidges正着手進行一項關於恆星物理的課題研究,他們讓我加入,半年左右完成了這個研究[4]。這是我第一次進行天體物理學研究,是一次自我考驗。一年之後Gregory退休,C.W。 Allen繼任臺長,他就是寫Astrophysical Quantities那本書的人。
我向他提出了一個利用倫敦大學天文臺60公分望遠鏡進行觀測研究的方案,得到了他的支持和幫助。這是我第一次自己設計課題,做了一些關於恆星顏色的工作。雖然這個課題因我回國而中斷,但這三年的一切都爲我對自己轉換專業的決定增強了自信。
賽先生:那您1952年回國,當時選擇回國困難嗎?爲什麼沒有留在英國?

圖5。 1950年在倫敦求學的王先生(中)
王先生:英國政治家還是挺有眼光的。我們解放軍一過江,英國就承認新中國,是西方國家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我們當中多數人都決定回國,但是後來經過許多曲折才得以成行。
做了回國的打算之後,在做課題的過程中我給紫金山天文臺寫信,瞭解天文臺的情況並說明了自己回國工作的意願。很快,在1952年秋,我就收到了當時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教授敦促我回國工作的來信[5]。在後來的一篇紀念文章裏我寫下了當時的感受[6],在和Allen商量後,我於翌年回國,開始了回國後的科研之路。

圖6。 紫金山天文臺50週年(1984年)時“老同志”合影。前排左起:李鑑澄、孫克定、張鈺哲、陳遵嬀、陳展雲;二排左起:王綬琯、席澤宗、羅定江、李元、吳守賢;三排左起葉叔華、苗永瑞。
開啓射電天文建設
賽先生:1958年您選擇了射電天文,是一個什麼樣的機緣?好像和蘇聯專家有關?
王先生:射電天文學,是藉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軍用雷達接收技術的發展而崛起的。上世紀50年代,我國在這方面尚屬空缺。1957年中國科學院決定利用1958年4月中蘇聯合組隊到海南島進行日環食射電觀測的契機,向蘇聯引進射電天文技術,以助我國的射電天文建設的起步。日環食觀測隊伍中,中方團隊除了天文臺年輕研究技術人員外,還有幾所高等學校無線電專業的年輕教師,團隊由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和我負責。蘇方的領隊是射電天文學家Molchanov,他們的團隊相當龐大,帶來各個不同地區的天文臺的射電望遠鏡,波長從短釐米波到長分米波都有。
這次觀測選在三亞進行,很成功。技術引進也很順利。我和陳芳允,也和Molchanov成了很好的朋友。日食觀測結束後,吳有訓副院長向蘇方提出,留借兩臺釐米波射電望遠鏡,並決定把它們安放在沙河工作站,由電子學研究所和北京天天文臺(籌備處)合作啓動我國的射電天文研究。
可惜不久後“大躍進”開始,射電天文的啓動被捲入運動的大潮,但我們還是啓動了三個項目:一、堅持“消化”日食觀測中從蘇聯團隊引進的技術;二、邀請各有關單位(天文臺站及高校天文部門)的射電天文年輕骨幹到沙河參加爲期一年的“射電天文講習班”;三、在實施“大躍進”運動的“大幹快上”方面,當時極其匆促地仿照“Christiansen Array”,着手“太陽米波多天線射電干涉儀”的研製。1962年底,國家度過了“三年困難”。前面說的三個項目中,我們完成了頭兩個。兩者均在以後的歲月裏顯示出一定的效果。第三個項目中,6米天線及其裝置已交付加工,基地選址已初步定在密雲水庫的北岸。
1963年,我巧逢“Christiansen Array”的創造者澳大利亞的W.N Christiansen,從此開始了彼此長達四十年的密切交往。1966年5月,他帶來了一個全部可以靠自己動手製成的“雙明線”傳輸方案(用以取代當時我國尚不能生產的同軸電纜)。1967年完成了總體調試,得到了第一張射電天體的一維高分辨率圖像。
1973年,Christiansen來華時談到了他在悉尼大學的天線陣,正在改裝成綜合孔徑系統。這給了我很大的啓發。綜合孔徑方法是20世紀60年代射電天文方法上的一項革命性創新。我們如果以16面天線陣爲基礎(加上備用天線),採取“地球自轉-綜合”方法,應當可以在米波宇宙射電巡天研究上登上當時的“國際平臺”。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會是一個很大的飛躍。經過對各種可行性的考慮,我們擬出了一個方案。1974年,我們派了兩名研究人員到Christiansen的實驗室進行接收機核心部分的研究。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當時管理科研的領導支持我們向日本進口一臺NOVA型計算機。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密雲團隊已經在困難的環境和落後的條件下基本完成了項目中各分部方案的預研究。項目的總體建設也得以開始循序進行。但是隨着“對外開放”,大家很快看到了國際上高、新技術進入射電天文學的形勢。密雲團隊接着開始了新一輪的奮鬥。終於在1984年完成總體調試獲得了第一張射電巡天天圖。在隨後的日子裏,米波巡天仍有一方自己經營的園地。但是由於起始條件過於簡陋,工作中的維修成本和時間耗費很大,進一步的發展將需要較大的經費及人力投入,因此需要考慮不同的可供選擇的方案。南仁東、彭勃、邱育海等發現了貴州的喀斯特地區,開始對500米球型望遠鏡(後來立項建立貴州的“FAST”)進行探討。
對LAMOST的期待
賽先生:LAMOST(LargeSky Area Multi-Object Fiber Spectroscopy Telescope,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的優勢是什麼?您對它現在的狀態滿意嗎?
王先生:LAMOST是我們發展的一種大視場光譜巡天望遠鏡,以其設計做到了兼備“大口徑”和“大視場”的性能獲得同行的廣泛認同。把多目標光纖光譜技術裝備這種望遠鏡用以從事光譜巡天,其學術效果將足以置身當代天體物理觀測研究的前列。LAMOST望遠鏡達到了設計指標要求,實現了強調以人才造就爲本的目標,即兩類人才——天文儀器研究人才和“觀測天體物理學”研究人才——的培養目標。
2013年LAMOST發佈第一批光譜巡天資料,所含恆星光譜數量超過全球以往歷年所得的總和。這標誌着LAMOST已經帶動我們的團隊開始登上當代天文光譜巡天開拓的國際平臺。我對LAMOST的狀態以及趙永恆他們目前的工作是很滿意的。
但是LAMOST觀測的弱點在於興隆基地的觀測條件:每年晴夜日數相對少和視寧度僅屬中等水平。不過,和SDSS相比,LAMOST的聚光面積大一倍多,可以適當彌補視寧度的欠缺,而光纖數達4000,每年可得的光譜數可能超出很多。所以,在SDSS獲得了“第一輪巡天豐收”之後,兩者將處在同臺進行進一步開拓之勢。
我想再表達一下我對LAMOST的希望和期待。就光譜巡天來說,天體物理學研究上對大規模天體光譜信息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目前SDSS已經獲得豐收。和國際上許多重要天文設施一樣,“下一代”(在這裏也就是“後-SDSS”)設施的研究和實施備受關注。而對於我們,用LAMOST與SDSS接力,應當可以通過國際合作,把現有的LAMOST複製一臺,安放在國際上現有的觀測條件優越的臺址上,由國際共建一個“南天LAMOST”。聚光口徑仍爲4米(可以考慮增大到6米,視學術效果與建造時間而定),焦比仍爲5米左右,以保持大視場的優勢。
南天LAMOST可以和北半球相應的設施合作,進行完整的巡天。這樣做的學術效益毋庸贅述。進入這種規模的國際合作(共同攻堅和共享成果)對於我國“後-奠基”的人才(“觀測天體物理”研究人才和天文儀器研究人才)“更上一層樓”的造就也是毋庸置疑的。
”大手拉小手“
賽先生:您晚年注重科普事業,諸如以大帶小活動。您覺得科普最重要的是什麼?
王先生:嚴格說起來,我做的事不是科普,不是向學生們普及天文學知識。我在當時,大概18年前,有感於很多年輕人很有科學天賦,想引導他們。早些時候我們有一段全民皆兵嘛,叫做民兵,後來有一段全民皆商,大家都做生意。那麼,現在當然也不是爲了提倡全民皆科了。應該順其自然。如果一個學生確實有科學天賦,我們還是非常願意幫忙的,可以捎上他一把。在高中這個年齡段,在他對科學感興趣的時候,如果有人能引一把的話,那麼他就會有信心往科學上做了。

圖7。 王先生參加“大手拉小手”活動,與小小科學家在一起。
北京市科協有一個部門叫做青少年部,這個部門在積極執行一個口號,叫做“大手拉小手”。很多科學前輩對小孩兒特別關心,包括橋樑專家茅以升先生。我們做“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的初衷,就是針對那些科學稟賦已顯、對科學有高度熱情的高中學生,給他們創造機會,幫助他們到優秀的一線科研團隊中求師交友。一個人要做出成績,機遇很重要。比如現在的伊斯蘭國難民營裏面,即使有十個愛因斯坦也出不了諾貝爾獎,因爲機遇太壞。
一個人到了一定年紀,他回憶人生的時候,大半會回憶起中學教師。中學教師對一個孩子來說非常重要,如果這個中學教師很喜愛學生,把他推薦給一個或者幾個合適的人,這個孩子就有可能成長爲一個小小科學家。
賽先生:非常贊同您的想法。暑假期間,高中生到大學裏面來做一個小的暑期項目,體驗一下科研的樂趣,可能對他以後的人生髮展具有很大的影響。
王先生:我逐漸想清楚一件事情,真正的科研人才的培養,應該是傑出人才的培養。所以我很贊成像海外人才招募這樣的做法,我們目標就是放在高層,因爲這個(人才結構)類似於金字塔,上面有個高層,下面自然就會展開,高層非常重要,而且高層比較難得。所以,如果整個國家有很多高層次人才的話,它就會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國家才能發展得快。
對上個世紀的諾貝爾獎,你可以做一個很有趣的年齡統計。科學家做出物理科學諾貝爾獎工作時的年齡,有30%是在30歲以下,67%是40歲以下[7]。物理科學家的創造性高潮應該是在二十幾歲:愛因斯坦是26歲發表他的四篇文章,其中我覺得有三篇都可以得諾貝爾獎的。一個人的創造力了到40歲之後,就已經過了峯值。當然,現在的科研題目難度要比以前大。以前做課題,一個博士畢業生就可以了,現在要一個,甚至兩個博士後,這是因爲競爭的人多了,並不說明人的基因變了。

圖8。 王綬琯先生《自述》中的詩作、書法
這樣推斷的話,科學家在二十出頭就應該在科學上有所作爲,或者至少能夠有所作爲。對於基礎訓練,大學頭兩年非常重要。現在,任何一個大學生的數理基礎都比牛頓強,因爲那個時候微積分還沒發明,還要他去發明。但牛頓用現在看來比較初級的工具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所以有的題目不一定就要用最難的工具做;反過來,要有一個好的想法,科學家應該是挑最容易用的工具來做。所以,中學生不見得不能通過普通的數學做一些比較難的課題。這也是我們想通過“大手拉小手”培養年輕一代科學家的想法,希望更多一線的科學家能參與其中。
賽先生:完全贊同。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