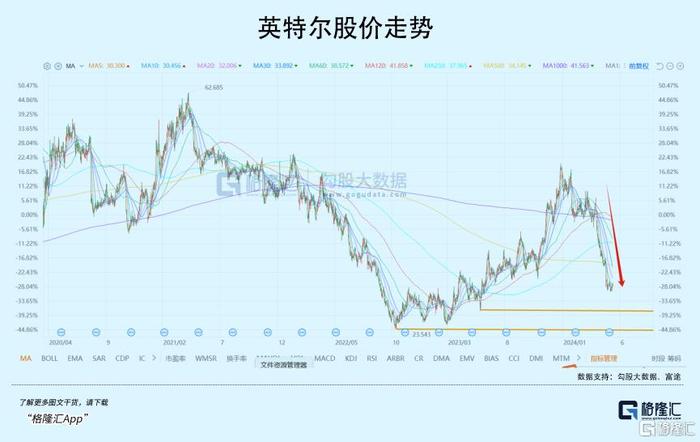“芯”求大戰:中國芯片產業投資難在何處?
記者 承天蒙
一“芯”攪動全球。國內芯片投資熱潮似有冷卻,全球電子企業又深陷“缺芯”危機,全球車載半導體三強日本瑞薩電子的一場火災,或致全球汽車減產150萬輛以上。
芯片危機是否會重塑供應鏈?中國企業該如何找準定位?如何佈局投資?澎湃新聞行業觀察與產業調查欄目“痛點”今起推出《“芯”求大戰》專題,通過採訪專家和業內人士,梳理目前全球芯片現狀,拆解投資佈局,探求“芯片”供應破解之道。
全球芯片短缺蔓延,從汽車到手機再到遊戲機,越來越多的行業需求紅燈亮起。
汽車行業芯片短缺是2020年底全球出現的新情況,福特、豐田、奧迪等部分工廠已經因此停產。汽車行業習慣了低庫存的運營模式,在疫情爆發初期曾大幅削減芯片訂單。現在,車企需要增加芯片供應,但芯片製造商正急於滿足蘋果等巨頭的訂單,沒有多餘的產能。
由於整個芯片行業高度依賴少數亞洲製造商,現在這些代工廠已經滿負荷運轉,芯片產能的限制直接衝擊了下游包括汽車、智能設備等產品的交付。
在我國,芯片供應過於依賴海外市場,自給能力嚴重不足。作爲“卡脖子”的關鍵領域,中國芯片近年來受到政府和民衆的廣泛關注。
集成電路、半導體行業的發展無法一蹴而就,尤其是近一兩年來,國際環境變化下,華爲、中興等企業的遭遇更是凸顯了中國芯片領域的短板。
過往中國互聯網行業蓬勃發展時所擅長的“模式創新”、“彎道超車”不再適用。“自主創新”和“國產替代”的趨勢之下,中國的芯片產業能否不負衆望,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解讀。
近來芯片投資熱潮中究竟有多少泡沫,國際分工和國產替代是否矛盾,爲什麼百億芯片項目相繼爛尾,發展芯片產業中國的短板在哪兒,投資人怎麼看?澎湃新聞記者採訪多位業內芯片領域資深投資人,從他們的視角看評說中國當下的行業發展。
百億項目失敗頻出
2020年來,6個百億級芯片項目先後“爛尾”引起廣泛關注。
據《瞭望》週刊記者在幾個地方的調查,僅在最近1年多時間裏,中國已有6個百億級芯片項目陷入爛尾,江蘇、四川、湖北、貴州、陝西等5省的6個芯片大項目“如今已人去樓空”,其中個別項目規劃投資規模甚至達到千億級別。有統計表明,除個別省份外,全國各省區市準備在芯片項目上的投入已有數萬億的規模。
這些爛尾的芯片項目,往往與芯片的生產製造有關,涉及土地資源的調撥、廠房建造以及相關的資金配套,而這些項目的失敗最終總是會回到一個詞上:“騙補”。
實際上,越是重資產的、需要大量廠房建設的項目,投資風險之大越是有目共睹。市場化的投資基金由於靈活的投資選擇,普遍會更傾向輕資產的項目模式。這些出了問題的項目,往往在投資架構、投資方案上都有很多不符合市場化風險投資機構的投資邏輯之處。
芯片製造壁壘極高。
光速中國助理合夥人朱嘉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除了在技術層面要紮實之外,真正做好芯片製造生產的大項目,還需要把控項目的管理者在整個芯片產業鏈中擁有豐富的經驗。芯片的產業鏈十分複雜,從上游供應鏈,所需的設備和材料採購到製造時用電和生產的需求,再加上下游的市場開拓、銷售等,每個環節都需要專業人士,且還需要頂層的業內管理人才來協調統一好整個項目。
目前,全球芯片代工50%的產能都在臺積電,而中國大陸芯片製造企業中最先進的中芯國際與其仍有較大差距,追趕也尚需時日。2011年,臺積電便實現了28nm芯片的量產,中芯國際直到2014年才實現了28nm芯片量產。2020年,當臺積電開始5nm量產之時,中芯國際才即將完成14nm的量產。
大鉦資本執行董事林小欽介紹,芯片製造需要投入的研發成本極高,並且需要長期投入,就算一家做得好的芯片公司,也可能處在長期虧損的狀態,這個資金體量不是普通風投機構可以滿足的,同時芯片企業也需要政府各方面的支持。
“芯片製造還需舉國家之力去支持頭部企業。”林小欽直言道。
投資機構的打法:整體化投資佈局
由於缺乏產業基礎,目前很多市場化的投資機構,在芯片領域投資時,採用的方法是整體併購、合資入股,或者是押注從成熟大廠出來的有經驗的團隊。
以譜潤投資爲例,康代影像是譜潤投資於2017年從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剝離、全資收購回來的機器視覺領域國際領先的資產,目前已經重組成爲一家總部和運營在中國,核心研發在以色列,營銷網絡遍佈全球的國際型的公司。越亞半導體原本是一家中以合資的集成電路封裝載板龍頭企業,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局勢下,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目前正在南通投資建新廠,譜潤投資於2018年投資了越亞半導體,股份佔比13%。
大鉦資本旗下芯片設計公司天數智芯半導體有限公司致力於打造完全自助知識產權的高端/雲端通用計算芯片和計算力軟硬平臺產品,林小欽介紹,目前公司正在研發7納米的GPGPU芯片。
“做7納米GPU芯片,全世界目前只有英偉達和AMD擁有成熟的團隊。但英偉達在中國沒有正式的研發團隊,只有AMD在中國有一支完整的GPU研發團隊。目前,天數的多名硬件團隊成員來自於AMD上海。”林小欽介紹,“目前天數的GPU研發團隊可以說是國內頂尖的,也是起步最早的,這是天數的優勢。”
上海國際集團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上海國方母基金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國方資本)意識到,在半導體行業領域投資,需要具備對行業的深刻理解和專業洞見,並建立平臺型、節點型的產業資源鏈接。
“我們所做的,就是藉助資本的連接,把半導體產業鏈接起來,去打穿、打透,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縱深式的佈局和專業化的投資。”國方資本行業合夥人王磊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
王磊介紹,做專業化的半導體投資背後需要有清晰的邏輯:半導體投資像一個棋盤,芯片作爲基礎是一個橫向的底層技術,並在縱向的行業中得以應用。在芯片這個橫切面之下,也有自身的短產業鏈,即芯片設計、晶圓製造、芯片封裝測試等。因此,國方資本與半導體產業節點的平臺型資源合作,發起了元禾璞華、中芯聚源和金浦新潮等產業基金,不斷加深對半導體細分領域的鑽研、對產業鏈的洞見,在此基礎上立足產業上下游進行項目投資,有效推動被投項目的產業協同對接和賦能成長,形成國方特色的“生態圈”投資打法。
缺配套產業鏈更缺人才,科研與實踐脫鉤
芯片產業鏈條很長,包括設計、製造、封裝、測試等環節,每一個環節中,中國都有被“卡脖子”的地方。
而實際上,半導體人才的稀缺更是貫穿於各個環節。如果說中國有一個半導體重鎮,那應該是上海。
上海張江是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最早,也是人才儲備相對最爲豐富的地區。目前,包括天數在內,中國幾家研發7納米GPU的公司全都在上海,這其中的歷史原因也不難發現。當年英偉達和AMD的芯片團隊都在上海,這些團隊成員如果跳槽創業,也會由於產業配套的原因繼續選擇上海。上海擁有包括臺積電在內的芯片產業配套,目前已經形成了較爲完整的產業鏈。
朱嘉表示,光速中國在投資半導體相關產業時,也會關注這個公司落地在哪裏。
“很多區域城市做不好,主要還是專業性,或者說更直接的就是人才,人才所在地與項目是否成功有很強的關聯性。如果很難吸引優秀的行業人才來落地工作和生活,要做一個很前沿的半導體項目,就很難成功。”
朱嘉同時表示,上海張江是國內半導體發展最早、相對人才儲備最豐富的地區,隨着時間的推移,現在北京、深圳、南京也聚集了很多相關人才。但總體來說,必須要有很好的項目,同時匹配優質的人才集羣,這樣纔能有良性的發展。
“整個行業的人才肯定是嚴重不足的。大學培養是一方面很重要的人才來源,但目前行業的中堅力量還是來自於具備在跨國公司或行業頭部公司經驗的工程師,但這樣的人才極其短缺和搶手。”林小欽這樣表示。
“我們中國最大的一個問題,基礎科研和實際產業是完全脫鉤的。”譜潤投資周林林介紹,這裏面基礎研究的積累、產業的積累缺一不可,而中國在兩個方面都較爲欠缺,需要中長期的戰略規劃,不能急功近利。”
“中國的基礎科研很多都是爲了發表文章,文章發表完了以後就結束了,然後再搞一些新的,再發表文章,又結束了,它沒有一個科學研究的積累過程,而這個積累,不是一兩個研究所,也不是一兩個大學能夠做到的,需要整個社會大家都來做基礎研究,並且最後一定要跟實際去對接起來,不能僅僅是發表論文。在實際的產業中,產業積累也需要一個個產品、一個個關鍵點的突破,慢慢積累起來,彙總了以後纔是一個真正的大海。”周林林表示。
如何尋求國產替代
現階段國產化的聲浪掀高,但是國產化不可能一蹴而成,需要堅持不懈的投入與努力,尤其在EDA工具與IP及半導體設備與材料等方面,它們都是“硬骨頭”,至少在短時期內不太可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據大鉦資本林小欽透露,天數芯片的核心IP都是團隊自研,但是國內芯片設計用的高端EDA工具仍然被外國公司壟斷。
投資老將周林林則介紹,上世紀80年代他參與了一個上海政府主導的做半導體塑封材料的科研項目,雖然已經拿到了日本的專利,但當時因爲國內缺乏關鍵材料只能放棄。而兩年前,他再看半導體塑封材料時,發現中國仍然只能做中低端產品,因爲高端的關鍵材料還是隻有日本有,中國沒有。
實際上,半導體產業是最徹底的全球化產業,沒有全球協同無法成功。以荷蘭ASML的EUV光刻機爲例,光刻機有10萬個零部件,其中涉及德國提供蔡司鏡頭,日本提供特殊複合材料,瑞典的工業精密機牀技術,美國提供控制軟件、電源等。一臺光刻機,是全球化分工協作的結果。
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美國高科技對中國的限制卻也給市場空出了新的機會。
“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要發展自己的硬科技,發展自己的上游核心技術已成共識,這將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市場機會,會創造出百億美金甚至千億美金的價值。我們預測在未來幾年,中國國產芯片的市場佔有率會不斷地提高,目前國產市佔率大概是百分之十幾,未來可能會逐漸提升到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朱嘉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國產替代會成爲越來越強的投資主題,我們也將持續看好中國半導體領域未來的長遠發展。”
另外,雖然國產替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現在中國在產業鏈的某些環節已經開始起步,慢慢滲透。
“我們看到,現在有一些領域國產化已經做得比較好了,比如說芯片設計、低端一點的芯片EDA開發工具,一些IP,包括生產製造裏面一些中低端的硅片、生產設備,現在都逐漸地有國產廠商供應,而且都做得還可以。但是距離高端領域的道路現在都還非常漫長。”林小欽表示。
周林林則表示,中國應該花5-10年的時間,尋找到幾個領域來重點培育,有所突破之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佔到主角地位。
“你看韓國人做芯片,跟日本人做芯片就不一樣,跟美國人做芯片又不一樣。每個地方做芯片的重點都不一樣。韓國是記憶芯片大規模地做,美國這種規模化的不太做了,但是美國在做尖端的、特殊應用的芯片,臺灣人就善於做foundry(晶圓)、幫你生產加工,所以他們每個地方都是找到自己擅長的特色,然後專注做到全球最好。周林林介紹,“所以中國也要慢慢找,找到自己的特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