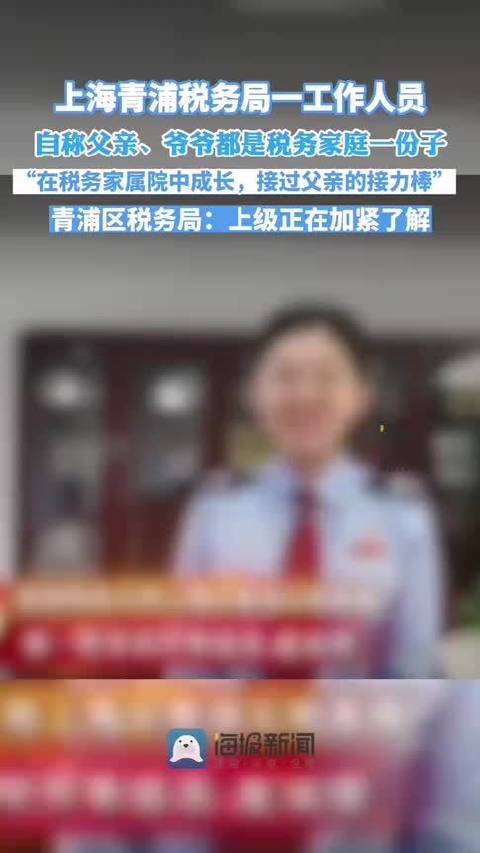【原】中国冷兵器时代古典战车发展史
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战车出土于殷墟,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 世纪至公元前11 世纪的殷商晚期。出土的商代车辆车厢高度为0.5 米,轮径为1.2—1.5 米;独辕,有直衡和弯衡两种,在衡两端上缚轭,用来驾马;方形车厢,车厢面积约为1.8 平方米,门大多开于车后。另外,车马坑中车队全部为一车两马形制,并且有大量的兵器做随葬品,如铜质、骨质的戈、刀、镞等。由此可见出土的这些车辆是战车,并且在殷商时代,用于驱动战车的马匹数量为两匹。在殷墟以外,于殷商时期的方国地出土的车马亦皆为一车两马。这说明在殷商晚期,马车已在商人的统治地区传播开来,并作为战争工具投入了使用。
根据对随葬人员的分析,在殷商晚期的战车作战中,一辆战车的人员配置基本为二人和三人。但是从随葬的兵器数量分析,一驾两士的可能性不大,一驾三士当为主流。根据随葬兵器的位置,战车上的三人中,居中者为御手;居右者当为持戈的武士,承担肉搏任务;而居左的武士当为射手,持弓,同时配有近战用的戈。根据墓葬考古,商代战车还配备有二十五名左右的徒步士兵。
(上图)中国殷墟车马坑
史料中不乏关于商人大量使用战车作战的记载,如《淮南子》中的商汤以战车三百辆在南巢与夏桀展开大战等记载。根据考古发现,殷商战车应该以五辆、二十五辆、一百辆、三百辆为编制级别。
总之,在中国刚出现战车的殷商晚期,战车的人员配置和装备较为完善,这也为后来周代的战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战车相较于步兵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在战场上,战车的运用并不多,由此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战车成本较高,多是作为“撒手锏”和“奇兵”而存在的。
殷墟发掘出的战车在结构上与在两河流域、高加索、埃及和欧亚草原发现的战车遗迹相似点颇多,而且如此大量的战车突然在商代晚期出现,可以推出我国战车外来的可能性极大。
(上图)西周车马坑
周代,中国进入了大规模使用战车的时代。在此期间,为了满足日益迫切的军事需求, 战车的配置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首先是战车的挽马数,根据现有文献来看,时人及后人多记载为“战马四匹”。如《诗经》中的“驷骐翼翼”“四牡业业”、《左传》中的“驷介百乘”等。但是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沿袭殷商一车二马配置的战车依然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渐扩大,战车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以战斗型车辆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车厢增大为广14—16 米,进深11 米或12 米。殷商和西周时期的战车车厢过于狭小,因此车上的军士只能紧紧背靠背来战斗,战斗空间很小。春秋战国时期车厢的扩大,使得战士在车上不会过于拥挤,活动空间变大,便于和敌方战斗。另外,当时战车的车辕较殷商时期增长了数十至一百厘米,长辕易于平稳,较为省力;轮辐增多,辐多则轮坚。这反映了制轮工艺的提高和重型战车的发展方向。
与殷商时期战车作为“奇兵”作战不同, 春秋时期车战规模扩大,车战很快成了主流的战争形式。如公元前632 年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一次性就出动了战车七百辆;公元前607年,郑、宋的大棘之战中,郑国一次就俘虏了宋国战车四百六十辆。春秋晚期,中国的战车规模达到了一个顶峰,晋国战车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四千辆。然而到了战国时期,虽然战车仍然在不断发展,战车的规模仍在扩大,但是战车在战场上的作用和地位却在迅速降低。这要归咎于战车本身的局限性。战车虽然是陆战的利器,冲击性、机动性强于步兵,但是其本身的问题却很多。
首先是环境因素的限制。随着战争的需要,用于战争的车辆变得高大而笨重,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在中国,战场环境十分复杂,南方多河网、森林、沼泽、丘陵,北方多山地与沙漠,平原地区相对较少,这极大地限制了战车的生存范围。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在双方出动数百辆战车的情况下,由于要摆出阵列,就需要非常理想的大平原环境,而中国这种少平原的地理环境难以满足这种需要。而且,战车的性能虽然高于步兵,但是一旦被步兵包围,丧失了冲击性,就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战中,强国因为环境原因战败的战例比比皆是。例如公元前575 年的鄢陵之战中,晋国的战车就因为陷在沼泽中而几乎全军覆没。又如晋国在与北方狄人的作战中,也因为战车受困而在前期吃了不少苦头,不得不“毁其车以为行”,这就是环境因素决定战车成败的一个深刻例子。
第二个就是战术方面的劣势。由于战车本身相对于普通步兵价格昂贵,驾车者也以贵族居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作战不利,指挥官必须做出选择,即保车弃卒,所谓“殿其卒而退”。这一做法无疑会扰乱原有阵形,只能让大败变为惨败。
虽然存在种种劣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更先进的兵种投入使用,战车无疑会以蓬勃的生命力继续存在下去。不幸的是,这样的先进兵种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它很快对战车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威胁,让战车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改变了未来中国近两千年的军事格局——它就是骑兵。
这一新兴的兵种进入军队序列后不久就改变了诸国传统的作战方式。骑兵的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用途广,各方面皆优于车兵。“急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是对骑兵作战最好的概括。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完善战车性能,骑兵取代战车统治战场也是不可逆的潮流,战车就这样在更加先进的骑兵面前败下阵来。
(上图)秦始皇陵铜车马
秦以后,随着高桥马鞍和硬质马镫的出现,骑兵更是迸发出了超强的生命力,而战车却逐渐成为骑兵的从属。在后来的车战中,战车队基本都以车骑相混的方式出现,如西晋时期马隆创偏厢车击败鲜卑、北魏太武帝北伐柔然动用战车十五万辆、唐代马燧利用战车大败安史叛军等。可以看出,历史的车轮越是向前走,战场上的战车规模就越小,战车的辅助倾向就越明显。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骑兵战术的成熟,冷兵器时代的古典型战车已经被画上了休止符。
冷兵器时代的古典型战车最终消失于热兵器开始出现的宋代。相对于北方的辽与西夏,宋朝的马政长期处于劣势,战场上能够使用的战马数量极少。由于北方防线缺少马匹,步兵野外对抗骑兵的成本和风险相对较高,战术限制条件也多。作为主力的宋军步兵的训练情况也十分令人担忧,欧阳修就曾犀利地指出当时的边军将士“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尽管这一指责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说明了当时步兵素质的低下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宋仁宗时期,战车作为一种战略构想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对抗西夏政权,汾州团练推官郭固上疏请用战车,并提出了“陷阵车”的构思。
“陷阵车”以民车为原型,车厢增为重箱,高四尺四寸。战车中装备床子弩一架,每车五人,操弓者二人,操弩者二人,一人擂鼓指挥车辆的进退。车前辕设置蒙幢一张以保护推车者,车的四周覆盖上毡毯以防备矢石。一辆车需配备二十五人,车上五人,前后推车的十四人,执肉搏兵器者六人。这种战车可与步骑相杂,随机进退。
郭固设想的战车偏向于重型野战兵器。它在理论上攻守相宜、武器齐全。所以提议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宋仁宗的重视,也制作了样车进行试验。但是最后,宋仁宗却并没有让郭固的战车投入到实战当中。
这是因为,郭固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他却忽略了冷兵器时代战车投入使用的可行性。首先,他的战车过于巨大笨重,一辆战车就要十四人推挽,推车的人数将近车上战斗人数的三倍。一旦和西夏的骑兵展开作战,宋军的非战斗人员数量就十分巨大,这无疑增加了军队的战斗负担。其次,一辆战车上一架床子弩、两弓、两弩的火力密度和杀伤效力根本不足以击退或迟滞敌方的重装骑兵冲击。另外,虽然郭固的奏议中提到了骑兵,但是在宋仁宗时期马政败坏的情况下,宋朝是否有能力长期维持车战的用马是一个问题。最后,骑兵固然用于追敌,但是一旦战车失去了骑兵的保护,在活动不便、非战斗人员数量巨大的情况下,进行战术移动是十分困难的。
除了以上战术问题,郭固的战车还面临着一个环境不适的问题。宁夏地区地势南高北低,境内有分布广泛的山地和丘陵,地表形态复杂。根据2004 年的数据,宁夏地区丘陵占38%,平原占26.8%,山地占15.8%,台地占17.6%,沙漠占1.8%。可以看出,宋军如若在这样的地形上使用战车,可展开作战的区域十分有限。而骑兵在此地形上作战,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就更突出了战车本身的局限性。可以说,宋仁宗弃战车而不用,实非对军事的轻视,而是看出战车不可用这一点后做出的决定。后来,虽然宋军里陆续有人提出使用战车,但是都因环境问题而作罢。
总体来说,秦汉以后,战车便通常与大规模骑兵协同作战。唐代以后,随着中原政权马政的败坏以及骑兵战术、装备的崛起,再加上战车本身对于战场环境要求较高的局限性,在冷兵器时代的大环境下,古典型战车被淘汰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规律。
本文摘选自《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