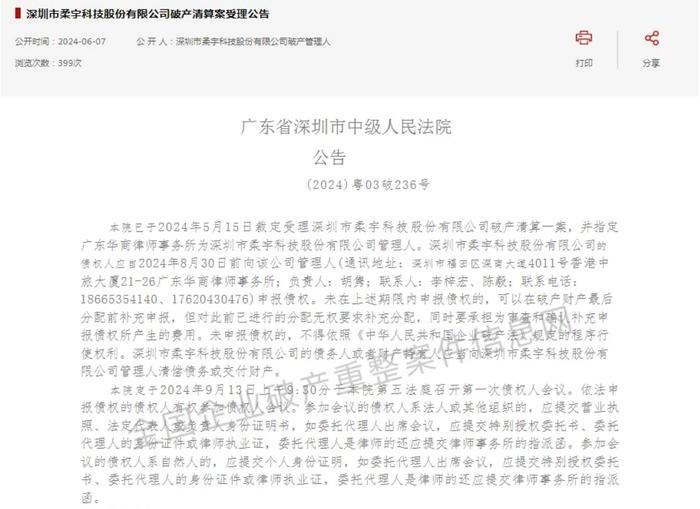對話黃怒波:做企業家和登珠峯都是挑戰不確定性
原標題:獨家對話黃怒波:做企業家和登珠峯都是挑戰不確定性
中新經緯客戶端6月25日電 (趙佳然)“登山時不會知道明天能否成功登頂,做企業也是如此,僅存偉大的幻想沒有用,需要一步一步頑強挑戰。”北京中坤投資集團創始人黃怒波在接受中新經緯客戶端專訪時,如此將企業家精神與登山精神聯繫在一起。
1995年,黃怒波辭職創建中坤集團並擔任董事長,通過投資房地產賺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投資創業同時,北大中文系畢業的黃怒波從未放棄對文學的追求,同時與登山結下了不解之緣。目前,黃怒波已出版詩集、散文集十餘部,並被翻譯成九種語言,完成七大洲高峯的攀登並徒步到達南北極點,其中三次登頂珠峯,2018年率北京大學山鷹社登頂珠峯。
前不久,黃怒波撰寫的小說《珠峯海螺》正式出版,作爲一部“商戰”“登山”雙主題的小說,書中不僅刻畫出攀登珠峯的艱難險阻,同時再現了企業家在商海鏖戰中的跌宕起伏。
《珠峯海螺》歷時十年完成,結合了作者登頂珠峯的個人經歷,濃縮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圖景,體現出不斷創新、永不服輸的精神氣質。在接受專訪時,黃怒波感慨道,企業家的挑戰與攀登山峯有諸多相似之處,在遇到不確定性時勇於挑戰的精神是一致的。

北京中坤投資集團創始人黃怒波 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北京中坤投資集團創始人黃怒波接受“全寶對話”專訪實錄(有刪減):
中新經緯:前不久你再次登上珠峯和大本營,作爲曾經成功登頂珠峯的企業家,此次再去珠峯有什麼感受?有什麼不同?
黃怒波:我登過5次珠峯,其中1次失敗,3次登頂。2018年,我作爲總指揮帶領北京大學山鷹社登珠峯,這也是世界第一支登珠峯的普通大學生登山隊。那次經歷讓我感慨萬分。
2002年,山鷹社登山隊在攀登西藏希夏邦瑪峯的過程中遭遇雪崩,從此以後業內便認爲大學生不能登這麼高的山。但對我來說,回看民族歷史,多少年來我們是從失敗中走過來的,倘若因爲一次失敗而不再嘗試,那麼便失去了向上精神。所以,我不斷地做北大的工作,2016年終於獲得了學校的准許。
探險不一定意味着冒險,要有一切可控的方案;同時,要強調組織紀律,要聽話,這兩點北大山鷹社都做到了。這次我們很順利地登頂,從失敗的地方站了起來,這樣纔對得起埋在雪裏的那幾個學生。
這次再回珠峯,見到了相識多年的嚮導藏族弟兄們,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實際上,我的小說背景就是珠峯頂上,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新一代西藏人,他們從過去的放牛娃成長爲了與國際接軌的新興產業參與者。
登珠峯對我最大的磨練就是,讓我發現人在山的面前如此渺小,然而但只要肯堅持,就沒有克服不了的東西。事實上,企業家的挑戰跟登珠峯一模一樣,就是挑戰不確定性。登山時不會知道明天能否成功登頂,也不知道未來的危險在哪裏;做企業也是如此,僅存偉大的幻想沒有用,需要一步一步頑強挑戰。
中新經緯:最近你發表了一個演講,題目爲“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企業家精神的審美批判”,爲何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企業家精神放到一起?
黃怒波:我們這一代做企業的人,也應該有一個反思。我們是誰?從哪裏來的?我這次在演講中談到,古樹參天是因爲它的根深深紮在大地裏;這一代企業家有如此成就,是因爲趕上了好時代,並不是因爲個人多麼了不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感謝這個時代。
企業家這個名詞是新出現的,過去我們被稱爲商人,企業家概念的出現,也代表着社會給予我們的尊重與認可,企業家在某種意義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榮譽。然而,我們也需要反思:我們所做的是否全部都對?我們是不是天生應該得到這麼多?
從我個人的反思來講,我認爲這一代做企業的人,嚴格來講都是套利型企業家,意思是並沒有在傳統的生產模式上進行創新,而是利用信息差或者機會差,拿到了別人拿不到的資源。
舉例來講,爲什麼房地產富豪多?因爲套利。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住宅是個大問題,但當時國有企業沒有重點做房地產。於是,民營企業便抓住機會,利用社會巨大需求和產品供給之間的差距,大量的房地產商由此而生。套利就是利用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能力,獲得你的利潤。
套利型企業家存在的問題是機會主義,比如今天倒鋼鐵,明天、後天又做不一樣的產業。市場經濟在發展過程當中,很多機會不是總是均衡出現的。機會主義背後的因素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即“落後就要捱打”,如果不做“老大”,就沒有市場份額,存在一定“賭”的性質。
從這個層面來說,我們需要看清事物本質,將企業家身上的社會達爾文基因剔除掉。如果我們得到的多,那肯定會有人得到的少;所以我認爲,21世紀中國社會已經步入小康,我們要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以及整個社會的和諧進步,不要落下任何一個人。
中新經緯:你提到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部分企業家產生了尋租與套利的兩種傾向。從反思角度來看,你認爲這種思想能清除掉嗎?
黃怒波:我們到了該清除(這種傾向)的時候了。
在數字經濟時代,作爲企業家要反思自己是怎麼野蠻發展過來的,以及要給後來人灌輸什麼。我們需要考慮和諧發展的問題。如此來看,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剛開始,但總得有人來做它。
中新經緯:你認爲老一輩的企業家應該如何去適應數字經濟時代?
黃怒波:在數字經濟時代,人們從最傳統的資源依賴走向了數字經濟的依賴。數字經濟的特點是透明、公平,要求企業不能依靠套利,而是需要技術創新,比如說芯片技術等。在數據化面前是造不了假的,這樣一來又帶來了另一種企業家審美的可能性,即追求創新。
在數字經濟時代,再依靠尋租和套利獲取利益的模式將不再適合。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時代也是我們創業的最好時期,因爲它允許你個體化、碎片化,也不一定依託傳統資源。在這個時代,誰能夠提高自己的數字素養,誰就會成功。
中新經緯:你還有一個身份是北京大學創業訓練營理事長,也接觸了許多年輕企業家。在你看來,“九二派”企業家與“80後”“90後”企業家的創業邏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黃怒波:我們創業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企業。我倒過鋼材,賣過茶葉,也倒賣過複印機,那時候就只能逮着什麼算什麼,也是套利的表現。然而,創業成功的概率是極低的。
這一代創業者面臨的,是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完善的法制。由於中國經濟的蓬勃成長,市場擴大,這一代人趕上了從未有過的好機會,而數字經濟時代也給予了個人創業的自由。
創新是需要敏感度的。當企業家不再創新的時候,就已經從企業家回到了商人。企業家的創新需要不停創新,但是由於財務自由問題已經解決,加之知識的侷限性,“九二派”已基本喪失了創新動力。敏感與生存是相關的,當人們覺得“明天不做就活不下去”纔會敏感,當功成名就之時就會缺乏動力。由此來說,現在的創新機會是靠新的一批企業家帶來的。
企業要適應現在的社會發展。現在的消費主力是年輕人,企業如果與年輕人脫節,可能就會受到影響。我認爲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會淘汰一批企業,不淘汰就沒有進化。舉例來說,傳統汽車行業如果不做電動汽車,那麼在5年內或將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我希望“九二派”能夠好好反思自己,能夠把自己的所得所失留給社會,要留給社會新的創新空間。
中新經緯:你認爲老牌企業需要適應或“討好”現在的“00後”嗎?
黃怒波:那是一定的。社會的消費羣體完全變了,所以企業的創業文化、傳統模式也得變。我認爲5-10年內,現在的大批傳統產業都會消失掉。比如房地產行業,未來“00後”們也許不買房,認爲租房就行了。所以,消費的觀念的改變,使得傳統行業將慢慢弱化。
中新經緯:有觀點認爲,現在的民營企業家遭遇到了輿論困境。對此你怎麼看?
黃怒波:目前,民營企業與企業家和大衆確實出現了對立情緒,這是全球都存在的現象;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是財富不公,這也是接下來需要被解決的問題。作爲企業家有責任反思,雖然不一定要把錢都捐出去,但需做到低調。
另一方面,對立情緒也反映出了社會進步。大家都在思考財富重要還是公平重要,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我認爲,社會也需要進行寬容教育,減少對立。
中新經緯:早在2008年,就有企業家呼籲開始新的商業文明。十幾年過去了,在你看來新的商業文明誕生了嗎?
黃怒波:當然,現在的許多新的商業文明其實並沒有被意識到。比如,企業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尋租的風險;此外,法制的健全標誌着社會的進步,也催生了新的商業文明。
中新經緯:你對現在的短視頻等互聯網新興熱點關注得多嗎?
黃怒波:我現在正在嘗試將旅遊行業等重資產清退出來,創業做數字經濟,包括數字孿生、虛擬人、區塊鏈等。
曾經我對互聯網知識一點都不懂,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互聯網信息與價值的理解。2017年,我帶着北大山鷹社登卓奧友峯,此前我買了50多本互聯網相關的書帶上山,涉及新媒體、短視頻等等。在山上讀完這些書後,我便決定開始內容創業。
隨後,我策劃的丹曾人文專注於線上及線下的素質教育。現在丹曽人文教育擁有100多個學者,60多部教程,內容涉及心理學、當代科技、人文地質等。我們將其做成多語種線上課,向全世界開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在搶救文化。(中新經緯APP)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