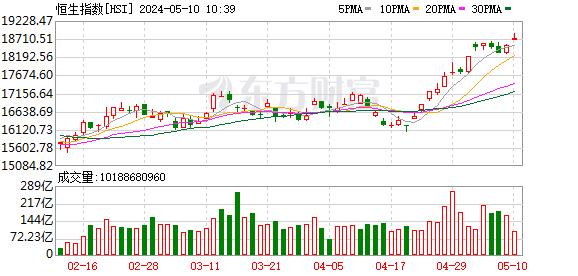“賺最多的錢,交最少的稅”,科技巨頭遭“全球最低15%企業稅”圍剿!
原標題:“賺最多的錢,交最少的稅”,科技巨頭遭“全球最低15%企業稅”圍剿!如何影響全球經濟格局?避稅天堂何處去?
記者/李孟林 張凌霄 編輯/蘭素英
在低稅率或零稅率國家和地區開設分部,再將全球各地所得利潤轉移過去,從而儘可能地減少上繳的稅款,一些跨國公司的慣常避稅手法多年來一直令不少國家政府頭疼不已。尤其是隨着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新業態不斷出現,科技巨頭的服務更多基於互聯網技術,而非實體經營,對跨國公司徵稅更是難上加難。
據《衛報》報道,公平稅收基金會(Fair Tax Foundation)的一份報告顯示,“硅谷六巨頭”——亞馬遜、臉書、谷歌、奈飛、蘋果和微軟——在2011年至2020年這十年間逃避的全球稅收達到960億美元。
今年7月10日,包括中國在內的二十國集團(G20)在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後宣佈,G20就重新分配跨國企業利潤徵稅權和設立全球有效最低企業稅率等措施達成“歷史性協議”。方案一旦正式實施,如果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不低於15%,全球每年將新增約1500億美元稅收。
曾代表美國政府參與經合組織全球稅改討論的德勤國際稅務主管羅伯特•斯塔克(Robert Stack)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國際社會能夠在多邊合作的機制下就稅改框架達成一致,這是一項重大成就。但是改革方案的執行還面臨着諸多挑戰。在斯塔克看來,美國國會能否批准與此稅率改革相對應的國內立法值得全球關注。
針對最低稅率改革方案可能給中國企業帶來的影響,多名稅務專家告訴記者,跨國企業未來會更全面地綜合考慮其他營商因素。相對於稅收,其他非稅務或商業因素,如人才、生活成本、金融基礎設施、法律制度等,對未來的商業和投資規劃將變得更加重要。
美國“砍一刀”,意欲何爲?
英屬維爾京羣島、開曼羣島、百慕大羣島、荷蘭、瑞士、盧森堡、愛爾蘭……這些國家和地區總是令全球知名企業趨之若鶩,不僅公司註冊程序簡單方便,而且繳納的企業所得稅、資本利得稅或其他稅費極低,有些地區甚至無需繳納,“避稅天堂”之名由此而來。
多年來,跨國企業通過將全球所得利潤轉移至“避稅天堂”,造成本國稅基流失,令各國政府頭疼不已。尤其是隨着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市場和實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離,對跨國企業的徵稅更是面臨巨大挑戰,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稅收利益顯著受損。據聯合國估算,每年全球各國因跨國公司利潤轉移行爲損失的稅收達到5000-6000億美元。
2013年以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經合組織”)便開始着手研究國際稅收體系的改革問題,並於2020年形成了重新劃分跨國企業全球剩餘利潤在各稅收管轄區之間的徵稅權和設立全球有效最低企業稅率的“雙支柱”方案。
今年以來,國際稅收改革加速成型。7月1日,經合組織宣佈,其協調的“雙支柱”國際稅改框架已得到130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的支持,其代表的經濟體量佔全球經濟總量的90%以上。7月10日,G20宣佈就重新分配跨國企業利潤徵稅權和設立全球有效最低企業稅率等措施達成 “歷史性協議”。
談及協議的意義,德勤中國國際稅收及企業併購重組稅務服務華南區領導人劉明揚對《每日經濟新聞》介紹稱,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設定或可降低大型跨國企業利用手段將利潤轉移到“避稅天堂”等低稅收管轄區關聯企業的動機,因爲在改革後的框架下,若大型跨國企業未能在各地區繳納最低水平的稅款,企業總部所在的稅務管轄部門能夠按新規定要求企業補交所得稅至全球最低有效水平。因此,此決議應有助於阻止企業把利潤向低稅收或無稅收管轄區轉移,同時亦可確保跨國企業履行應盡的納稅義務,繳納最低水平的所得稅稅款。
同時,劉明揚表示,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亦可降低稅收考量因素對投資和業務選址決策的影響,從而減少爲跨國公司提供低稅率優惠的稅收管轄區之間的稅收競爭。
目前,與G20合作推進全球稅改的經合組織正在緊鑼密鼓地敲定技術細節。按照計劃,詳細的規則和實施方案將在今年10月出臺,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
曾任職於美國財政部、代表奧巴馬政府參與經合組織稅改討論的羅伯特•斯塔克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美國政府十分關注國際稅收改革的進展。目前,斯塔克擔任德勤國際稅務部董事總經理。
斯塔克分析指出,拜登政府提出了規模龐大的基建計劃,對美國企業加稅是基建計劃的主要資金來源。爲了確保美國企業的競爭力,推動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遏制各稅收管轄區爲吸引跨國企業投資而競相降低稅率的“逐底競爭”便成了重中之重。
按照最新改革方案,全球企業最低稅率爲至少15%,適用範圍爲營收達7.5億歐元的跨國企業。
根據媒體此前報道,拜登政府尋求把國內的企業稅率從21%提高到28%,並將美國企業海外利潤的最低稅率從10.5%提高至21%。
曾任聯合國副祕書長的哥倫比亞經濟學教授何塞•安東尼奧•歐堪波(José Antonio Ocampo)對《每日經濟新聞》表示,21%的全球最低稅率遭到部分G7國家的反對,因此美國最終妥協,將這一標準設定爲“至少15%”。歐堪波教授也是倡導國際稅收體系改革的獨立專家委員會ICRICT的主席。委員會成員還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法國明星經濟學家托馬克•皮凱蒂等。
科技巨頭首當其衝?
在全球最低企業稅之外,經合組織稅改方案的另一個重點是對大型跨國企業的利潤進行更加公平的分配。
中金公司研究部在6月份的一份研報中指出,現行國際稅收體系嚴重依賴“物理存在”與“常設機構”來定義徵稅權力與利潤分配,難以對依靠數據和專利等無形資產獲得利潤的跨國公司徵稅。而改革後的新規則(“支柱一”)要求一些大型跨國企業在其客戶所在轄區繳納企業所得稅,即便該企業在這些轄區並不擁有實體運營、資產或者僱員。
按照規定,對於年營收超過200億歐元且利潤率在10%以上的跨國企業,市場國(跨國企業銷售產品和服務的國家)有權對企業利潤中超過10%的部分徵稅,總徵稅額爲超額利潤部分的20%到30%。未來“支柱一”的營收門檻可能進一步下調至100億歐元。
當被問及哪些公司會受到影響時,斯塔克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目前還沒有一份完整的名單,但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等美國科技巨頭肯定囊括其中。
亞馬遜目前總體利潤率不足10%,但“支柱一”的適用範圍可以延伸到公司財報裏的業務分支上。也就是說,亞馬遜利潤豐厚的雲業務部門AWS也將被納入利潤分配的框架中。
美國政府此前估計,按照以上標準,全球約有100家公司將受到影響,其中,美國公司佔了多半。華盛頓的稅收政策智庫Tax Foundation則指出,符合標準的美國企業佔54個。
歐堪波教授對《每日經濟新聞》表示,儘管受影響的美國公司佔了多數,但美國也將由此獲得更多的額外稅收,這也是美國支持“雙支柱方案”的原因。
對於國際稅制改革的進展,谷歌、亞馬遜及Facebook都表達了支持態度。對此,斯塔克對記者分析稱,法國、西班牙等國家已經對科技巨頭徵收單邊數字服務稅,加拿大等也在制定類似的數字稅。“支柱一”的作用和數字服務稅相似,全球統一框架通過後,各國有望取消單邊數字服務稅,企業合規成本將大幅下降。
“避稅天堂”不復存在?
每經記者查閱經合組織“包容性框架”的成員名單發現,百慕大羣島、開曼羣島、維爾京羣島已經同意“雙支柱”方案,但愛爾蘭、匈牙利、愛沙尼亞這三個著名的低稅率國家仍持保留意見。
毋庸置疑,全球有效最低企業稅率一旦實施,將對零稅率或低稅率國家造成重大沖擊,尤其是對於那些沒有其他手段吸引外資的經濟體而言。
以企業稅率設定爲12.5%的愛爾蘭爲例,得益於低稅率,愛爾蘭成功吸引到蘋果、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軟、Facebook等科技巨頭在當地設立海外業務總部,創造了豐厚的財政收入。如果採用新規則,以全球企業最低稅率設定爲15%爲例,即使愛爾蘭拒絕提高企業稅,美國也可以單方面向這些公司額外收取2.5%的稅,補足15%的稅率。
斯塔克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稱,愛爾蘭、匈牙利、愛沙尼亞希望保持靈活性,利用歐盟修改政策時需滿足“一致同意”原則的機制,爲自己尋求儘可能優惠的條件。
對於缺乏經濟資源,長期以零稅率吸引外國公司註冊以賺取服務費的“避稅羣島”,斯塔克認爲,全球最低稅率如果實施,這些島嶼屆時可能會自行徵收企業稅,以彌補吸引力下降帶來的收入損失。此外,“避稅羣島”還可以通過提供精細化的會計、法律、保險等服務,提高競爭力。
在歐堪波教授看來,15%的稅率定得過低,與愛爾蘭、瑞士等國的現有企業稅相去不遠。未來,改革新規則實施後,各國和地區可能會比拼誰更接近15%的最低稅率線,無法明顯削弱跨國企業將利潤轉移至低稅率地區的動機。ICRICT一直呼籲將最低稅率提高至25%。
儘管“雙支柱”國際稅改框架目前已得到廣泛支持,但其正式實施還面臨着諸多變數。
斯塔克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美國國內是否立法支持“雙支柱”方案將是接下來的焦點,也是國際稅收改革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之一,因爲目前拜登所在的民主黨僅在國會佔據微弱優勢。
此外,斯塔克認爲稅收體系的改革還面臨着技術性的挑戰。協調全球的跨國稅收是一項極度複雜的體系,如果最後出爐的規則給跨國企業和各國稅務機關帶來了難以消化的合規成本,實施的效果也必將大打折扣。
對中企影響幾何?
對於改革方案可能對中國企業帶來的影響,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曹鴻宇認爲,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制度對中國整體負面影響較爲有限。中國企業海外收入相對較低,受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影響的企業海外利潤並不大,而政府支持企業“走出去”,對企業海外利潤徵稅也持寬鬆態度。
中國內地已於2008年對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進行“兩稅合併”,統一了該兩類企業的所得稅。目前,中國內地法定企業所得稅率爲25%,非居民企業稅率爲20%,而一些特定產業和特定地區等優惠稅率爲15%。
普華永道中國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夥人王鵬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鑑於內地企業所得稅率是25%,如果進入門檻範圍的內地企業大部分運營在境內,境外運營規模較小,那麼該規則對其影響將非常有限。如果內地企業在境外有一定規模的運營,未來則需要重點關注位於低稅率稅收管轄地的實體運營情況以及當地所獲得的稅收優惠情況。
劉明揚告訴記者,爲適應新的全球稅制,大型跨國企業應檢視其現有或未來的海外業務情況,評估最低稅率可能對其帶來的影響,如有需要,可進行適當的業務重組。
多名稅務專家同時認爲,國際稅收體系改革不會讓中國的營商環境發生大的改變。
在劉明揚看來,相對於稅收,其他非稅務或商業因素,如人才、生活成本、金融基礎設施、法律制度等,對跨國公司未來的商業和投資規劃將變得更加重要。
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也認爲,“比起稅制,外資考慮是否來內地的更重要因素應該是市場性因素。”
中國香港作爲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在此次全球稅率改革中所受到的影響也備受關注。
莊太量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稱,目前中國香港相比內地稅率偏低,法定企業利得稅率是16.5%,從2018年開始,前200萬港元利潤的利得稅率降到了8.25%。但“中國香港納稅的主力是本地的電力公司、地產商等,以及部分國際銀行,而全球稅制改革對這些公司影響不大,而且它們搬遷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麼對於來港的大型跨國企業會有影響嗎?
“新制度對所有低稅率地區都有影響,因此,跨國企業會更全面地綜合考慮其他營商因素。”劉明揚對記者說。據他分析,中國香港的低稅率和稅務優惠措施的吸引力表面上來看將受影響或會削減。大型跨國企業在中國香港享受着低稅率、地域來源徵稅原則、免徵資本收益原則及稅務優惠措施,但如果有效稅率低於全球最低稅率,那麼這些企業就需要繳納補足稅。
德勤中國稅務合夥人Jonathan Culver也在採訪中對記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表示,中國香港可能會考慮在全球最低稅率的基礎上建立自己內部的最低稅額體系,這樣一來,中國香港就可以自己徵收部分需要補足的稅款。另外,許多企業在中國香港設立公司也出於其他目的,便於進入內地市場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但劉明揚最後強調,中國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蓬勃的資本市場、沒有外匯管制、有世界一流的專業服務,這些固有的營商環境優勢仍有利於吸引跨國公司來港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