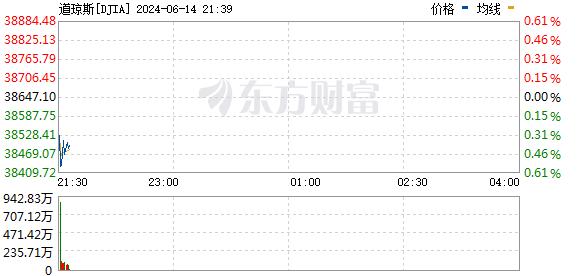911事件後“恣意揮霍”20年 美國還剩下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01年9月11日,三架客機分別撞擊了美國的雙子塔和五角大樓,還有一架客機墜毀在撞擊第三個目標的路上。這次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給美國造成了慘重的損失,911事件之後,當時的小布什政府先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兩場戰爭。

9·11事件是二戰之後美國本土遭受的最嚴重襲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如今,20年時間轉瞬飛逝,有人說在阿富汗我們好像看到了一個“圈”:20年前阿富汗是塔利班在執政,後來美國人來了,塔利班被趕走了;然後美國人和盟友們在阿富汗折騰了20年;20年後美國人走了,走得既不光彩也不體面,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混亂。這些混亂一開始看上去像是喜劇,本質核心都是悲劇,當然更多地越來越像一場鬧劇。尤其是美國撤離喀布爾的景象,被稱爲“西貢時刻再現”。
如果我們以阿富汗爲個案分析,911以來這20年的時間並不是美國的一個“循環”,這20年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爲美國霸權的一個“戰略揮霍期”,這種“戰略揮霍”可以理解爲一個霸權國家在沒有清晰戰略指引的情況下,使用自己軟件和硬件方面的資源,採取某些行動,以一種微觀戰術層面可能是比較有序的、精巧的、甚至精心設計的方式,但在戰略層面漫無目的開展行動的狀態。
2019年12月9日,《華盛頓郵報》上出了一組系列報道,中間有一篇依據美國信息公開法案從美國國會設立的專門機構“阿富汗事務檢察長辦公室”獲取的報告,從中可以佐證這個揮霍期的存在。這篇報告的題目叫《因爲沒有戰略而擱淺》,這篇35頁的報告看下來,你會感覺我是不是生活在一個電影Matrix(黑客帝國)所描繪的世界當中——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在20年的阿富汗行動中,尤其是在小布什和奧巴馬任期,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清晰的國家層面的戰略。文中有這樣一個描述:他們所獲得的文件顯示,通過對大概幾百個外交官、軍方的將軍、前線指揮官、情報人員的訪談,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對以下三個問題:1。誰是我們的敵人,2。誰是我們的盟友,3。 啥時候我們能知道我們在阿富汗贏了——他們認爲美國是沒有答案的。
這篇報告裏面講了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有一次對布什說:“有兩個將軍要向您彙報工作,一個是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可能要談一些跟伊拉克相關的事兒,另外還有一箇中將叫麥克尼爾”。小布什對拉姆斯菲爾德的反應是:“麥克尼爾是誰啊?”拉姆斯菲爾德說:“他是你任命的美國駐阿富汗的軍隊的最高軍事指揮”,然後你覺得你要見他嗎?小布什說:“我不需要見他。”
當小布什衝進阿富汗,花了6個月時間把塔利班從喀布爾趕出去之後,美國白宮做了一次宣佈;後來小布什又去伊拉克做了次表演,自己坐了一架艦載機在航空母艦上着陸,着陸以後上面有一個標語:Mission Accomplished(任務完成),小布什站在甲板上宣佈在伊拉克的主要戰鬥行動結束,然後拉姆斯菲爾德飛到阿富汗去,差不多同一時間做了類似的表態。
在小布什來看,當他做完這件事情之後一切就結束了,但是美國的軍隊還在阿富汗,這批人怎麼辦?要不要撤?什麼時候撤?怎麼撤?撤之前需要做哪些準備?小布什這樣一個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經驗的人是不會考慮的。

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同時,報告中反覆強調一點,美國既不懂阿富汗,也不懂塔利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組織”“恐怖主義”若干個概念在小布什這個層面的美國核心決策者當中是被混淆使用的,有一些基本的事實是不清楚的。一方面,根據拜登政府公佈的美國《911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顯示,9·11恐怖襲擊也許和所謂的阿富汗以及塔利班沒有直接的關聯。劫機的那些人以沙特阿拉伯人居多;另一方面,基地組織跟塔利班不是一回事。塔利班當時的問題是容留基地組織,並且拒絕交出基地組織的領導人本·拉登。
美國花了6個月的時間把塔利班趕出喀布爾之後,基地組織頭目躲的躲、藏的藏,進入到山區地區,基地組織從一個組織被打成了一個運動,離開了阿富汗。小布什政府後期在阿富汗執行軍事反恐任務的時候,有無數當地人告訴美國軍方,當地已經沒有基地組織了,他們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美國人繼續把塔利班當恐怖分子打。
這份報告指出,大約2002年到2009年之間,美國面臨一個在阿富汗實施行動終結的黃金機會,就是塔利班希望跟美方接觸和談判,希望在新組建的政府中謀求一席之地,這個要求被美國無情地拒絕了。
事實上,後期當美國開始考慮如何體面地從阿富汗撤軍的時候,依然不得不選擇跟塔利班進行政治會談,不得不給塔利班以政治上的認可。於是到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和塔利班的代表在卡塔爾進行正面對話和談判,並且談成了美軍的撤軍方案。
整個過程,在沒有清晰戰略指引,又有看上去可以近似於無限量供應戰術支援的支撐下,一個超級大國非常魯莽地進入到了一個看上去不起眼的、別名“帝國墳場”的地方,在那消耗了20年。
說完小布什,我們再看奧巴馬。奧巴馬公佈了一個紙面上很漂亮的阿富汗戰略,採取了和小布什政府非常不同的指導方針——把美國在阿富汗的行動從反恐轉向了反叛亂作戰,並且搞了一套反派亂作戰的戰術方法理念。然而,外界評價奧巴馬這個方案的特點是:在極爲有限的時期內,也就是在他總統任期內的4年或者8年,要實現數量衆多的目標——太多目標,太短的期限,太過多樣化的考慮。
舉個例子,奧巴馬講了一堆反叛亂作戰的東西,又對阿富汗增了一大圈兵,提升了在阿富汗美軍軍事行動的強度。但他同時在任內宣佈了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最後日期——一個非常精準的日期。這不是說列出美國在阿富汗要做到幾件事情,每件事情做成的衡量標準是什麼,達到目的後就撤軍,比如說建立一個一個廉潔而有效的政府,能夠給阿富汗穩定地供應水電這些關鍵基礎設施,讓當地老百姓的生活處於穩定的狀態;比如說阿富汗政府的有效控制能力能夠覆蓋阿富汗的全境,而不僅僅是侷限於喀布爾等幾個有限城市的美軍保護區等等;而是再增完兵以後,明確宣佈所有派出去的美軍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從阿富汗全境撤離。
這意味着什麼?塔利班一聽到這消息,“明白了!”剩下就是啥都不做,等那天來了,你走了我再出來就可以了。由此可見,當奧巴馬拿出這樣一份東西的時候,他其實對戰略是沒有概念的。
奧巴馬之所以給出這個撤軍日期,原因很簡單,競選總統期間這是他的主要政治主張,爲了滿足美國國內民衆對於早日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無休止的軍事存在的需求。
奧巴馬政府任內對阿富汗有大體上三個核心的假設:第一,阿富汗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間接受美國移植的西方民主制度;第二,從美國開始遂行反叛亂作戰方案到美軍全部撤離,很短的幾年時間內,大多數阿富汗本地人可以大幅度提升對這個政府的支持程度;第三,阿富汗政府本身所具有的硬件能力能在很短的時間裏大幅度躍升,以至於當美國和北約的力量撤離後它能保障自己作爲一個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安全和發展這兩項最基本的功能。可惜,所有這些假設都不存在。
而在執行整個戰略的過程中,歷任美國政府唯一的核心指導戰略是歷任美國總統的國內支持度,是政客及其所在政黨在美國國內政治當中可能的收益和損失的精巧計算。但是這兩者之間是對沖的。奧巴馬儘管奉行了和小布什截然相反的指導方針,然而他的反叛亂作戰註定趨於失敗,因爲該戰略的核心支柱——阿富汗當地本身的這個政府,美國撐不起來。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有美國記者這樣評價美國在阿富汗的行動:“自9·11之後,美國人花了大約6個月時間就推翻塔利班政權、打擊乃至於摧毀基地組織的主要戰術目標。但自那之後,在10多年至20年的時間裏面,美國不停地在擴展和修改它的任務和目標,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他們致命地採用了一整套註定會趨於失敗的軍事戰略,而這個軍事戰略建立在對阿富汗這個他們沒有理解的國家一種誤導性的認知和理解的基礎之上的。這是美國最終在阿富汗遭到決定性挫敗的核心原因。”
20年的時間,美國用比任何理論教程、政策文件、分析報告都要鮮活的實際行動戳破了或者說挑戰了我們的一個常識性的認知——學過政治的人都知道,所謂“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很完備的,表現在通過制度設計,它可以把人的因素降到最低。美國的政治制度下,雖然好人不一定能夠做成事,但壞人肯定一定不可能壞事。”甚至戲謔地說這個制度成熟的標誌就是“你選個人跟選只狗當總統沒啥區別”。但是這20年,四任美國領導人的操作告訴我們,區別很大。
此外,從布什到奧巴馬這16年間,美國的戰略實踐告訴我們的第二件事情是美國的制度是沒有教育功能的。一個不懂戰略的人不是說他在總統位置上坐了8年之後,他就懂戰略了——8年前不懂,8年以後還是不懂。
20年前,當小布什決定入侵阿富汗把塔利班幹掉,大背景是蘇聯解體、世界進入後冷戰時代之後美國實力的達到峯值。在那個頂端上美國所處的地位、它所維繫的霸權秩序和美國所擁有的力量大體是匹配的。當美國被9·11一下子“吵醒”之後,真正面臨的挑戰是:美國究竟清不清楚自己有多少資源,這些資源能夠支撐起一個怎樣的行動?用什麼樣的方式能夠進一步提升和改善美國的國家利益,讓美國的霸權地位更加鞏固?
恰恰相反,正是處在國際體系力量頂端的美國在受到了重大刺激之後,領導人遵循的是自己的本能和直覺性,認爲美國近似有可以揮霍不完的資源,可以實現任何一種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推出第二重含義,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失敗的原因正是因爲沒有戰略。戰略本質上是一個國家如何去精準地去運用自己的各種各樣的資源、手段,以可接受的成本去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目標,本質上它是一種成本覈算。而當時美國進入的一個最大的誤區是高層決策者堅定地相信,美國有無窮無盡的資源,以至於美國不需要一個戰略,不需要去搞清楚我的敵人是誰,我的盟友是誰,我在那邊要幹嘛,我打就是了,誰出來鬧事情我一個一個地解決……
不要看阿富汗很小,比起美國來阿富汗弱到幾乎在硬實力上可以忽略不計。但事實上“治大國若烹小鮮”,即使像美國這種雖然未經聯合國授權,但國際社會因爲將其認爲“美國被空襲後的自衛行動”而予以理解的軍事幹涉,也需要通過精準的成本和收益覈算,制定一個停止點——做到什麼時候、達成哪幾個目標就收手,爲了實現這個撤離的目標要做到哪些事,從而在撤離之後當地可以維繫一個有效支撐下去的狀態。
這不是戰術問題,是戰略問題。但是20年,美國在阿富汗沒有一份這樣的戰略。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事件是一個啓動點,美國的實踐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大國真正的挑戰是如何有節制地、審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對於國家來說這種審慎在中長期會給予相當優厚的回報。
我們可以對比老布什政府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的表現。在戰術指導性原則上,老布什堅持美國對外軍事幹涉行動六項原則中的“追求一個明確可實現的目標”——海外戰爭什麼時候停?把伊拉克軍隊從科威特趕走。老布什沒有隨意更改這個目標,比如說沒有把它更改爲趕走之後要推翻薩達姆政權、讓伊拉克實現政權更迭,沒有輕率地把海灣戰爭從科威特擴大到伊拉克境內,只是追求“解放科威特”這樣一個有清晰衡量指標的目標。最後,這個行動取得了非常漂亮的成功。
從2001年 9月11日開始到2021年9月11日,美國在阿富汗地區對於自身戰略資源的揮霍性使用,向大家展示了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佔據壓倒性優勢地位之後錯誤地使用自身力量優勢的所有可能的形式。總結起來有這麼幾條:
第一,在沒有清晰戰略指導下奉行一種近似於沒有邊界、不計成本的原則,僅憑短期利益考量乃至於某種突發刺激作爲主要驅動就開始一場長時間的行動;
第二,在行動過程中沒有一以貫之的策略,對行動的目標難度、面臨的挑戰風險在最高決策層中缺乏有效的認識和控制能力,而且有明顯的拖延症;
第三,對於美國的戰略決策者來說,個人利益至上、貫徹精緻的利己主義,以一種無知和狂妄的態度去看待和理解美國與世界的關係,這是造成美國在阿富汗陷入戰略窘迫的關鍵。
第四,這20年提醒我們,要形成一個認識和理解美國霸權的正確框架。美國在阿富汗的行動不斷提醒我們,通過不同方式會認識到不同的美國,而真實的美國是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去運行呢,是一個需要不斷校準的概念。美國現在發生變化的速度遠比大家想象的要快。

8月29日,美國總統拜登和夫人在美軍多佛空軍基地迎接阿富汗撤軍中被炸死的美軍士兵遺體,結果拜登被拍到中途看手錶。
伴隨着美國從阿富汗的撤離,歷史表現出了以螺旋方式前行的一種相似性。很顯然,美國的霸權在經歷過阿富汗20年的實踐之後,以戲劇性地撤離來到了一個新的拐點。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美國就此不再有任何概率實現復興、再現昔日輝煌;但另一方面,這20年對美國不管是資源還是心理等各方面的挫敗、衝擊和挑戰,有相當大的可能讓其產生某些重大的變化,對此我們需要認真觀察和思考。
最後,恐怖主義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911恐怖襲擊事件不僅是美國的悲劇,也是人類社會的悲劇。國際社會當然必須攜起手來,以各種方式有效地應對恐怖主義帶來的威脅,並謀求實現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除恐怖主義的目標,這也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必須完成的一項使命。
美國在阿富汗的20年實踐告訴我們,單純依靠軍事反恐是沒有出路和前途的,因爲它不能真實滴解決問題。儘管拜登政府不願意承認,並且反覆強調說“美國在阿富汗所追求的目標從來都不是國家建設,而只是反恐”,但客觀事實告訴我們,除非實現有效的國家建設,避免一些國家由於內部發展遇到的問題,從而因爲治理瓶頸和困境成爲全球恐怖主義的窪地和集結地,否則人類就不能在真正意義上戰勝恐怖主義。而在此過程中,發展的力量永遠比征服、干預、強制所獲得的效果要顯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