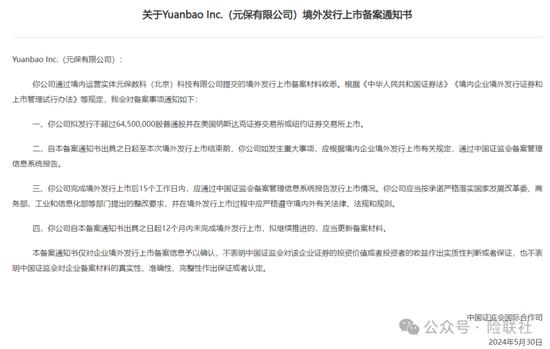金燦榮:911後20年美國內外傷挺重 拜登不是好醫生
美東時間2001年9月11日上午8時46分,美航11號班機撞向世貿中心北塔;9時03分,美聯航175號班機撞向世貿中心南塔……時任總統小布什之後發動浩浩蕩蕩的“反恐戰爭”。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飛機撞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濃煙從紐約世貿中心北塔滾滾而出,15分鐘後第二架聯合航空公司175號航班撞擊世貿中心南塔。圖源:視覺中國)
喀布爾時間2021年8月26日17時48分,自殺式襲擊者身穿綁着25磅炸藥的背心走向美軍士兵,4天后,運送最後一批美軍人員的C-17運輸機飛離喀布爾,撤出了其“反恐戰爭”主戰場,美國曆史上最長的戰爭就此結束。
(8月30日,運送最後一批美軍人員的C-17運輸機飛離喀布爾)
北京時間9月8日中午11時30分,環球網記者在北京採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他告訴我們,“9·11”之後的20年,美國“內傷”和“外傷”都挺重,但可惜,拜登不是好醫生。
塔利班的勝利與美國“9·11時代”
記者:2001年9月20日,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宣佈發動“反恐戰爭”,以擊敗全球恐怖主義網絡。20年過去了,您覺得小布什當年的目標實現了嗎?
金燦榮:從國際關係角度來講,“9·11”事件是21世紀第一件大事,它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進而改變了世界。這事件對美國人的心理震撼還是挺大的,是美國本土第一次遭到攻擊,攻擊目標也非常準確,就是對着美國的要害去的。我記得小布什總統當時站在世貿中心的廢墟上宣佈,這是一場“戰爭”,後來又在別的場合說“這是幾代人的反恐,是幾代人的戰爭”。“9·11”事件對美國刺激大,所以美國反應就大。
(小布什站在世貿中心大廈廢墟上發表講話)
在當時,美國知識界、戰略界有一種邏輯,即怎麼從根本上消除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就是讓那些國家“民主化”,因爲美國人有個理論“民主國家間不打仗”。他們認爲,如果把伊拉克、阿富汗都變成民主國家,就能從根上解決這個問題。事後來看,美國這個戰略應該是錯的。美國自己也承認“重塑阿富汗”失敗了。
美軍在喀布爾 圖源:外媒
另外美國戰略界還有不同的人表態,阿富汗戰爭的目標是通過控制阿富汗來威懾中國和俄羅斯。因爲阿富汗是“亞洲十字路口”,正好是中亞、南亞、西亞、東亞的交界,他們覺得把這個地方控制住了,往北威懾俄羅斯,往東威懾中國,往西能嚇住伊朗,往南能控制印度洋和南亞次大陸。
現在可以很肯定地講,美國當時宣佈的這些目標一個都沒實現。美國有人說“反恐”的目標實現了,因爲擊斃了本·拉登。但本·拉登2011年就死了,美國爲什麼又拖了10年?美國當時爲什麼不走?而且現在其實恐怖主義還存在。大家都注意到,8月26日,美國在喀布爾機場撤軍時還被“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分支攻擊了一次,恐怖分子還在。
所以我認爲,“9·11”確實對美國打擊很大,小布什當時的決策我覺得太情緒化了,被民意綁架,然後又被塞了很多私貨在裏面,結果就是把美國捲入了一個長達20年的戰爭。
記者:您剛提到,美國其中一個目標是“重塑”這些國家。當時堅定支持小布什的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近日承認,他那一代領導人“天真的”以爲一個國家真的可以重塑,與此同時還警告說,美國未來對地面戰反恐戰越來越沒有興趣,西方要考慮在沒有美國的參與下,與俄中以及伊斯蘭國家合作進行反恐,您怎麼看待布萊爾的話?
金燦榮:我們對布萊爾講話一部分加以肯定,比如他反思、承認了一些錯誤,但他總的基調其實還是在辯護,我們對此要有清楚的認識。布萊爾現在的反思是根據最新情況做出來的觀點調整。
另外,他對美國領導權的信任的反思也是對的。現在看來,無論哪個黨、哪個人在美國執政,“美國優先”都是一樣的。從這次阿富汗撤軍就看得出來,不光美國優先,而且是美國軍火商優先。現在西方內部看來也得清醒,都指望美國的領導很可能是錯誤的,不僅傷害自己國家利益,還傷害當地人民。
“9·11”之後的20年,美國變了多少?
記者:我們來談談美國的“改變”吧,您覺得2021年的美國相比2001年的美國,有哪些變化?
金燦榮:這20年裏,美國“內傷”和“外傷”挺重的。
“9·11”事件後,反恐成爲美國外交重點,原本用於民生的資源被用於反恐,社會治理出現嚴重問題,以致於美國“內傷”挺重。第一,在政治決策過程中,華爾街有着超出比例的影響,導致整個國家經濟結構偏向金融資本。
第二,基礎設施現狀糟糕。坦率來講,美國“鐵公機”(地鐵、公路、機場)佈局較爲合理,但基本都建成於上世界30年代,到現在快90歲了;多個城市供水、供電、通信系統非常老化。而中國的通信系統基本都是光伏、光纜,並且美國的光伏覆蓋率沒有中國高,其中一部分還是銅纜,美國的通信基站也只有40萬個,連中國的1/20都不到。我去美國之後所感受到的就是,他曾經輝煌過。但由於資本被華爾街壟斷,無法投入到基礎設施上去,也導致美國的製造業無法恢復。
(美國紐約地鐵站)
第三,貧富分化趨於嚴重。1980年時,美國五百強CEO的平均工資是白人白領工人平均工資的80倍;到2000年變成了450倍;202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700倍。
第四,種族矛盾激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後,美國的種族矛盾有所緩解,但近年又重新激化,特別是2016年特朗普執政後。另外,還有社會犯罪率上升、槍支毒品氾濫等問題。總之,美國社會這些問題本來就存在,但在美國耗費大量資源去反恐後,這些問題、矛盾更突出了。
從“外傷”層面而言,美國的“雙標”損害其國際公信力,“美國優先”政策削弱了其與盟友的關係。就近期喀布爾撤軍而言,美國奉行美國軍人、軍火商優先撤離,不管朋友,部分美國平民也不管,最新消息說還有100多名美國公民依然滯留阿富汗。
記者:美國這些“內傷”,是因“9·11”事件後反恐佔用太多資源導致的綜合徵嗎?
金燦榮:我認爲,今天美國出現的很多問題要溯源到1971年,當時的美國總統沒與盟友商量,直接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以美元爲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一定是有危機的,這在國際上留下了金融隱患,但對美國國內其實影響更大。因爲美元沒有黃金本位的約束,美國濫發美元,起初解決眼前問題,但導致了嚴重後果:產業空心化,因爲金融業開始一枝獨大,華爾街權力越來越大,開始操縱各種領域、思想、政治;社會貧富分化,實體經濟越來越困難,社會矛盾激化。總的結論是,美國在1971年犯了挺大一個錯誤,這個錯誤讓美國病了。
其次,1991年12月25日是一個轉折點。我始終認爲,冷戰結束的標誌時間應該是1991年12月25號蘇聯解體。但直到今天,美國戰略界對冷戰的認識都是錯誤的,他們把冷戰結束的原因給搞混了。冷戰結束的結果確實是美國贏了,因爲對手自我解體了,但冷戰結束的原因不是美國戰勝了蘇聯,而是蘇聯內部出了問題,送了美國一個勝利,所以美國人心態要正常,應該謙卑。美國那個時候應該做什麼?保持謙卑,三顧茅廬,請俄羅斯出山共治天下。那樣的話,美國今天的戰略處境會好很多。
但美國戰略界直到今天也沒有清楚認識,依舊傲慢,而傲慢則帶來內外問題。“對外欺負人”:首先欺負俄羅斯,把俄羅斯當戰敗國對待,欺負中國和盟友,欺負鄰居拉美國家。由於沒有蘇聯了,美國對內開始以市場化改革的名義剝奪中產階級各種福利,那麼就導致現在社會諸多矛盾。
所以回顧半世紀曆史,1971年和1991年都是重要轉折點,而“9·11事件”讓美國病情加重。如果沒有“9·11”,美國的病症會發展得慢一點。但美國精英層現在有個毛病,他把美國家裏內內外外的問題都歸咎於中國。美國自己把自己折騰病了,結果他要我們中國喫藥。於是中美關係必然下滑。
記者:針對美國這些病症,您覺得拜登政府有藥嗎?
金燦榮:拜登政府還是技術官僚爲主,他不是一個“好醫生”。“好醫生”應該是大戰略家,但現在美國沒有這樣的人。美國目前面臨的困境,坦率講需要“偉人”,需要極其有魄力的領導者才能解決。拜登挺自負的,他想做富蘭克林·羅斯福,但我個人直覺,他能力夠不上。
拜登 資料圖
其次,拜登所用的人中“書呆子”居多,特別是這一次阿富汗撤軍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外交官,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理論上一套一套的,但行動不行、執行力不行。按照中國人的說法,有點像趙括,紙上談兵很厲害。所以我的直覺是,面對美國現在的問題,拜登沒有答案,沒有藥方。後“9·11”時代,美國“全政府對華”
記者:拜登在阿富汗撤軍時辯解提到,撤軍的目的之一是爲更集中精力應對中俄挑戰。接下來會是大國競爭的時代嗎?
金燦榮:其實美國內部在2010年前後就已經有這種聲音了,在反恐有點進展後,美國國內就有人說要轉向大國競爭。但我覺得真正把大國競爭放到反恐之前,是2017年12月18號,美國國防部發表四年一度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把大國競爭放到首位,其中點名了中俄,中國還被放在了俄羅斯之前。所以應該說從2017年底開始,大國競爭就開始重新成爲美國戰略的頭號任務。
此次阿富汗撤軍,美國也扯上了中國。從美國戰略角度來講,這個思路是對的,但是其作用存疑。因爲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投入的資源其實很有限,20年花2.2萬億美元,一年就是1000多億美元,實際上美國省出這一點資源對大國競爭的意義不大。另外,由於阿富汗的重建失敗,撤軍狼狽,美國在盟友、在美國內部的信心是受打擊的。所以,我們可以聽他這麼一說,但實際效果上,我覺得這對中美未來博弈,對以後俄美博弈的影響是很小的,不宜誇大。
8月15日,阿富汗喀布爾,美軍直升機抵達美國駐阿富汗使館上空準備撤離使館人員
記者:美國一些戰略人士認爲,“9·11”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國,您怎麼看待這種觀點?
金燦榮:我們不能說它錯,它有點道理。“9·11”之後,美國主要精力放到反恐上去了,對中國的遏制少一點。如果一定要說“最大受益者”,可能是伊朗。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作爲“什葉派大本營”的伊朗在整個世界都很孤立,整個遜尼派世界排斥伊朗,美國也拉攏西方孤立伊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伊朗處境艱難,面臨戰爭,經濟困難。但美國在“9·11”事件後所犯的錯誤幫助了伊朗,美國先是幹掉了伊朗的宿敵薩達姆,又在伊拉克搞西方民主投票,60%人口都是什葉派的伊拉克成爲了伊朗的勢力範圍。之後,伊朗勢力範圍從波斯灣往西擴張,從伊拉克到敘利亞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形成了“什葉派新月地帶”。另外進入本世紀後,油價瘋漲。美國資本炒油,從經濟上幫助了伊朗。
所以一定要說誰獲益最大,伊朗排第一。我們不否認中國有所受益,但不是“最大受益者”。
記者:如果美國接下來搞“大國競爭”,您覺得它會往哪幾個方向去佈局?
金燦榮:美國現在把中國當對手了,所以中國將會面臨全方位的壓力。
以前我們過着很窮的日子,美國就放心。美國最喜歡中國幹什麼呢?中國人都做農民工、當打工人,天天給美國做襪子、做傢俱。但這個不行,我們人民要發展,14億人要發展,光做襪子有什麼利潤?我肯定要先做電視機,之後要做高鐵,做盾構機,然後再做大飛機、機器人,高端機牀。這是必然的,但美國不接受了。所以中美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國有發展的權利和願望,而且做得還不錯,但美國不接受,這是根本的問題。
面對中國崛起,美國不接受,中美矛盾就上升了。根據剛纔的分析,來自美國的壓力很大,中國一定是有一段時間很難受,因爲壓力是全方位的。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在搞一個“全政府對華政策”,不許政出多門。所以中國現在壓力挺大,但我們不用害怕,我覺得中國能扛得住。我們最關鍵的就是穩穩當當地發展,解決各種矛盾,美國的壓力我們能扛住。
從長期看,中美的競爭是世紀博弈,我覺得中國勝算還是挺大的。
記者:除了中國,您覺得美國還會把哪些國家當做它的目標?
金燦榮:美國現在基本上把中俄當主要對手。拜登在1月20日就任總統後說過,俄羅斯是美國最大威脅,中國是美國最大戰略競爭者。他對中俄是有所區分的。從美國角度來講,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對美國威脅比較直接,所以美國被迫應對,但長期看中國是主要對手,所以美國第一層面的對手主要是中俄。
美國第二層面的對手就是伊朗、朝鮮、敘利亞、委內瑞拉、古巴、波利維亞等一系列左翼政府。第三層面還要關注可能會搖擺的國家,比如巴西,如果盧拉再次當選,美國就得擔心。第四層面,美國對一些盟友不放心,其中有一些跟美國也是經常叫板。
所以美國要維持“老大”地位並不容易,雖然主觀上把中國當第一對手,想全力以赴對付中國,但其實客觀上他掣肘挺多,很難做到全力以赴對付中國。
記者:那中國應該怎麼應對美國的戰略調整?
金燦榮:中國首先還是好好發展自己。目標很簡單,超越自己。具體而言,在政治上優化黨的領導、加強法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經濟上進行產業調整,促進科技進步,搞好教育。此外,也要處理好其他一些問題,比如社會公正、環境保護等。
國際上,中國要承擔國際責任,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儘量跟西方,尤其是跟美國要做到鬥而不破,在第三世界廣交朋友。國內和國際都理性、穩健應對,中美博弈我個人是有信心的。來源:環球網/朱夢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