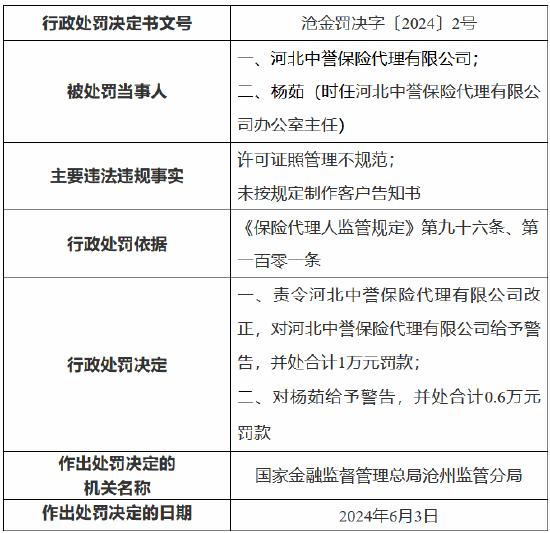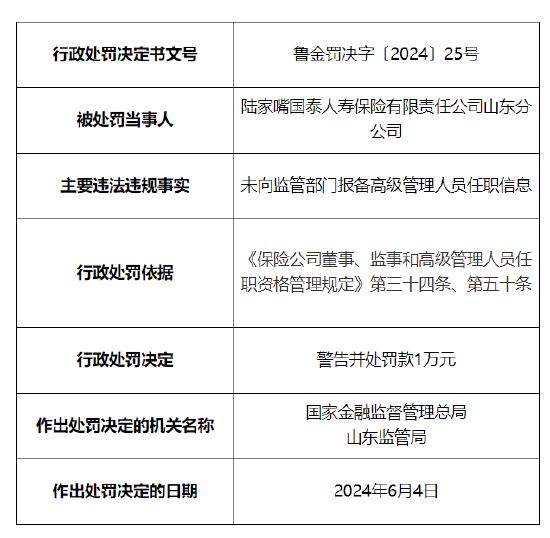大家保險羅勝:壽險新一輪大轉型關口,不悲不懼堅定向前
編者按
彷彿是在一夜之間,中國壽險業突然陷入轉型困境,新單、人力等核心指標幾乎是行業性的負增長,幾大上市險企股價跌跌不休,困惑、迷惘瀰漫行業,甚至還有一些靈魂拷問:中國壽險業是否還有未來?!
在這樣的迷思中,有些人寄希望於一些頭部公司的速效改革,有些人則期待監管進行又一次逆週期調節,帶領行業走出這一輪負增長。林林總總的轉型方案和改革宏論中,或許有靈魂拷問,但並沒有靈魂反思,中國壽險業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左右爲難的?時代紅利消失後的“攀巖模式”中,深刻又複雜的外部環境挑戰下,新一輪壽險大轉型關口又該如何“向前多走一步”?
今天的推送是一篇限時講話稿,或許最終也沒有明確結論,或許有些觀點也只是一家之言,但作者羅勝秉持深度思考誠意發聲,從他一貫主張的保險商業模式底層邏輯的分析方法出發,加上一些國際視野的映證比較,進行了縝密的邏輯推演,爲我們更深刻認清當前壽險業的形勢和任務,提供了一種分析問題的思維框架。在他推論的基礎上,作者所在機構根據自身資源稟賦,進行了一些轉型探索實踐,也可做爲一個觀察樣本。
正如有人說:生活中的10%由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組成,而另外的90%則是由你對所發生的事情如何反應所決定。壽險轉型確實遭遇瓶頸,但壽險基本面並未完全崩壞,哪些傳統優勢還存在,哪些增量空間待破局,需要深刻認識冷靜應對,不悲不懼堅定向前。

大家保險集團總經理臨時負責人羅勝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
大家下午好!很高興也很榮幸能參加這樣一個一年一度的行業盛會。認真聆聽了前面政府領導的重要講話、專家學者的深刻見解和行業翹楚的精彩發言,深受啓發,收穫很大。大家保險是一個正在艱難求生、求變、求發展的新機構,更希望得到同業先進的引領和指導。大會的主題是轉型,探求新格局下壽險業的高質量發展之道,本人忝列其中,敬陪末座,謹爲建言。
一段時間以來,我有這樣一個感受,今年以來壽險市場的大幅下滑,可以說是突如其來。大家似乎都有點迷惘,不知道這個變化是趨勢性的,還是週期性的,行業該怎麼應對,什麼時候結束。更進一步追問,還會有以前的高增長嗎,保險還算是朝陽行業嗎,未來的出路在哪裏。作爲局中之人,藉此機會,談一談我對壽險轉型內外部因素及轉型方向的粗淺理解,不一定正確,誠惶誠恐,求教方家。
三重驅動內因
壽險業直面大資管時代跨界競爭,監管、互聯網經濟倒逼行業轉型
本輪壽險業大轉型的帷幕,如果大家能達成共識,應該是從幾年前所謂資產驅動型業務模式被監管叫停拉開的。當時所謂資產驅動,就部分公司而言,其實質是壽險業務的全面“理財化”。監管因之提出迴歸保障的要求,轉型成爲監管壓力之下的整改之路。其實放眼國內外,近十年來,壽險的經營基礎和商業邏輯不斷髮生深刻變化,轉型已是勢在必行。晚轉不如早轉,隨着時間推移,轉型的難度和複雜度都在增加。
第一,壽險被迫也必然要參與大理財的競爭
隨着金融的可及性提升和金融產品的進一步融合創新,民衆的投資理財意識被激發,資產配置這樣的專業概念飛入尋常百姓家。壽險作爲一種財務風險管理和財富增值手段,被迫參與到大理財領域金融各業的同臺競爭。不用說理財型保險產品,就連所有帶現金價值的傳統壽險產品,也都從風險的敘事邏輯中拉拽出來,納入範圍更廣的金融產品收益比價隊列,按照理財的敘事邏輯重新進行價值評估。
衆所周知,金融產品是價格敏感型產品,收益或利率就是敏感點,也是最主要的競爭點。雖然我們在保費繳納和給付返還方面採取了許多消除價格敏感性的動作,但客戶的覺醒走得比我們想象的更遠,有的客戶已經開始運用IRR等專業分析模型,評估每一款保險產品的實際價值,然後與其它金融競品做比較,再決定購買行爲。
在賺錢是硬道理的驅動下,長期穩健的故事和風險考量的勸說缺乏猛烈而直接的衝擊力。這也正是前幾年P2P氾濫,近年來基金熱銷的直接原因。
這兩年你翻開抖音,隨時都能刷到基金銷售的廣告帶貨,有人甚至將2020年冠名爲“基金元年”。僅僅一年時間,公募基金規模增長5萬多億,增幅近35%。基金的概念植入也非常成功,從剛畢業的大學生,到退休在家的大爺大媽,都知道只有開展權益投資,纔是實現人生財富目標的不二法門。
在金融產品邊界日益模糊的大資管(從公司角度)、大理財(從客戶角度)市場裏,不管你穿什麼牌照馬甲、貼什麼金融標籤,都需要考慮如何適應或迎合金融消費最直接的心理需求。徐敬惠先生在一次演講中曾談到,商業的本質不是銷售商品,是提供生活解決方案,是爲客戶提供價值,對此我深以爲然。站在客戶的角度,一款壽險產品它的價值和吸引力究竟在哪裏,真的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
第二,全球監管對利率風險的高度重視,利率承諾型產品資本損耗增加,逼迫壽險公司改變產品策略和經營戰略
在所有宏觀經濟要素中,利率可能是對壽險經營影響最大的指標。各國曆史上幾乎都出現過因長期利率定價偏差導致重大風險的案例。在償付能力監管的制度演進中,大部分國家都對有承諾利率的壽險產品採取高資本損耗的限制措施。近十年來,發達經濟體基準利率持續下行,根本性地改變了壽險的經營基礎。
在產品方面,壽險機構紛紛改變產品策略,向“資本效率型”(capital efficient products)產品方向聚集。一是產險化,即重點銷售純風險損失率定價產品,如終身壽險、定期壽險、健康險等。二是基金化,不承諾利率,投資收益風險由客戶自擔,如無收益擔保的萬能險、投連險等。
我們比較着看這些年來部分發達市場的行業數據,或者跨國保險集團公開披露的報表,能明顯看到這種變化。
圖1:意大利壽險保費結構變化(2010-2018)
圖2:西班牙壽險保費結構變化(2010-2020)
圖3:英國壽險保費結構變化(2010-2018)
在經營戰略調整方面,春江水暖鴨先知,發達保險市場動作開始得比較早。如韓國近年來一直處在低利率環境中,醞釀多年即將發佈的償付能力監管新規也實行了更嚴格的利率風險資本要求。過去幾年裏,歐資保險公司幾乎全部主動退出了韓國市場,退出過程可以說是壯士斷腕,義無反顧。
如安聯人壽,十幾年前收購韓國第一人壽,累計投入資本十多億美元,4年前以倒貼6千萬美元的方式,賣給了一家中資公司。脫手之後,安聯集團股價應聲大漲。
在英國等市場,由於傳統的長期期繳壽險保單幾無新增,封閉式業務模式(closed book business)興起。這些公司不再開展新業務,關閉銷售,縮減運營,以極低成本運行,專注以存量資產投資獲取收益。
這些都是首先感觸趨勢變化的市場和機構的應對之舉。此外,長期期繳壽險保單增長乏力,也對壽險公司內含價值的高估值模式有所衝擊,導致壽險公司估值下行。從全球範圍看,低利率市場中壽險公司估值很少有PB超過1的。
表1:安聯保險新單保費現值(單位:%,億歐元)
表2:安聯保險營業利潤(單位:億歐元,%)
當然,利率下行有一個長期的過程,甚至會出現反覆。不同國家也有其根深蒂固的金融消費傳統。一些跨國保險集團,針對不同國家的消費習慣和利率環境,採取不同的產品策略,也照樣“站着把錢掙了”。換句話說,傳統的壽險經營模式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和時間窗口。但從長遠來看,客戶消費習慣的轉變和利率趨勢的變化正在一點一點發生,我們應早做準備,未雨綢繆。
第三,互聯網邏輯倒逼壽險產品簡化,同一產品中保障和理財功能分離,產品複雜度降低,可能更受客戶認可
經過互聯網經濟的浸潤和薰陶,客戶越來越喜歡簡單直白的產品。商業模式清晰簡單的公司也更容易得到高估值,這也是近年來酒店等行業重資產和輕資產不斷分離分化、輕資產模式受追捧的原因之一。
壽險產品的功能複合化和內容複雜化,有生命健康風險本身複雜的客觀原因,但更多是銷售策略等推動的。在其它金融產品越來越簡約並直抵核心需求的情況下,產品複雜化導致需求面收窄,銷售成本在跨界競爭中不佔優勢。需求流失和成本劣勢同時對原本賴以建立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個人代理人隊伍形成衝擊,傳統的銷售模式和觸客模式都面臨新的挑戰。
產品的簡單化並不代表公司經營的單一化,從發達市場的情況看,保險產品和保險公司可以遵循各自不同的發展邏輯。保險產品,作爲風險保障工具,做它該乾的事。保險公司,作爲金融機構,做它能幹的事。
保障和理財的邏輯分離,可以擴大保障的槓桿效應,提高消費者的風險保障覆蓋程度,讓民衆真正享受到保險。這也就是百萬醫療、惠民保等在產品推出後,重疾險越來越賣不動的原因。先不論這些產品定價是否充分,單從保險發揮社會功能的角度看,羣衆購買的積極性有利於樹立保險業良好的風險管理形象,是好事情。
在產品功能簡約化的同時,保險公司則基於其不斷增厚的整體基礎能力,積極參與理財市場的競爭,形成多個業務線和利潤中心。近期陸續有保險公司獲批基金牌照,說明監管機構認可其投資理財能力可以在其它金融產品領域得到展現。從發達市場的監管策略和跨國保險集團的業務構成情況看,也基本都是這個發展進路。
深刻又複雜的外因
新概念、新方略、新格局不斷湧現,生育率下降,預期壽命延長牽引行業轉型
近年來,行業外部社會事態風起雲湧,既深刻又複雜。雙循環、雙碳、科技斷供、自主創新、數字化、智能化、平臺壟斷、共同富裕等,新概念、新方略、新格局不斷湧現,正在從根本層面上重新定義我們所處的社會,也蘊含了壽險業從負債端、運營端和投資端全方位轉型發展的外部牽引要素。這裏的每一個概念都是一個大話題。人口老齡化是大會本環節的主題,也是影響壽險業發展的最重大而直接的外部因素之一,我們就此專論。
隨着“七普”數據的發佈,人們對中國即將邁入深度老齡化有了更加真切的認識,如何養老成爲社會熱點話題。老齡化是個人口結構問題,主要由人口的出生率和預期壽命兩方面決定。但不管從什麼樣的數據維度,無論以哪家機構的統計口徑來看,中國都將加速邁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生育率下降是人類文明化一個壞的副產品,即便在一向被認爲是高生育率傳統的伊斯蘭國家,也能觀察到文明和富裕程度提升後生育率下降的現象。很多國家都出臺過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效果都不明顯。如德國,政策力度很大,在歐洲是最有效果的國家之一,但也只能將出生率從十年前的1.3提升到現在的1.5-1.6,達不到更替生育率水平。美國的人口增加,主要靠移民帶動。
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2020年城鎮化率爲68.39%,並可能在2035年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80%左右的水平。未來中國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已不可能,有人甚至預計將在2023-2024年達到峯值,隨後絕對人口數開始下降。如果大家去看攜程的創始人、人口學家梁建章的文章,對中國的人口問題可能會有更深的憂慮。
預期壽命延長是人類文明化一個好的副產品。這主要應歸功於科技的進步。此次新冠疫情,在各國疫苗研發的大競賽中,mRNA技術嶄露頭角,被列爲2021全球十大突破性技術之一。其發明人卡里科被認爲是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的最熱門人選。伊隆·馬斯克認爲mRNA代表醫學的未來,可以用它“治癒一切”。目前,全球30多家公司上馬了180多個管線的以這項技術爲基礎的藥物研發項目,其中包括多種癌症藥物。有科學家認爲,未來十年,生物醫學加上人工智能,將誕生最猛烈的一波科技革命。
總而言之,雖然像人類即將實現永生這類預言還不足信,但科技進步將使得人類預期壽命大幅度延長則已是不爭之共識。“喫飯快快長大,喫藥慢慢變老”將成爲人類生活的常態。
不管我們怎麼轉變觀念樂觀對待,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肯定算不上好消息,但也無需過度擔憂。對社會來說,持續的老齡化將會極大地改變社會的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對我們每一個終將老去的個體來說,做好財務安排,規避養老風險,避免出現“人還活着,錢花沒了”的窘境,則是事關個人尊嚴福祉的重要問題。隨着社會的進步,養老的品質要求不斷提高,既加速催生新的養老消費業態,提升養老消費總量,也擴大了養老的財務保障需求,拓展養老金融的市場空間。
從這個角度講,老齡化對以生命和健康風險保障爲己任的壽險業來說,可以算是很好的發展機遇,有着廣闊的市場前景。
問題隨之而來,在這個泛養老金融的年代,在這個金融各業都想要分一杯羹的第三支柱市場裏,保險業的競爭力在哪裏?如果不能比收益,我們比什麼?
近期銀保監會羅豔君副主任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上有個精彩發言,她認爲中國的第三支柱體系更應當借鑑德國模式,保險在第三支柱領域有深厚傳統和獨特優勢,大有可爲。
我非常贊同羅主任的觀點,同時也認爲,不管是德國模式、英美模式還是什麼別的模式,如果拼收益不是保險的長項的話,就需要能講出不一樣的故事來。
轉型的可行方向和路徑
需要更加開放甚至大膽的思維,靠近實體經濟,靠近原生需求
轉型是行業和企業發展永恆不變的主題。保險起源於產險,以物爲標的。在隨後的發展過程中,開始以生命表爲基礎,將人本身納入保險標的範疇,管理人的生存和死亡風險,並讓保單具備現金價值,由此產生了壽險業,這可以算是保險業的第一次重大轉型。之後的一次次轉型,使保險業呈現出更加豐富和複雜的樣態。在尋求增量市場和突破性發展的轉型嘗試中,有成功有失敗,有的甚至帶有悲壯色彩。
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新型壽險產品的創設,個人代理渠道的建立,銀行保險的發展等,使我國壽險業發生了一次又一次的躍遷,成長爲世界第二大保險市場。
失敗的例子也不少。比如,保險業在信用風險管理方面幾次嘗試,幾乎均以失敗告終。從美國AIG大量銷售CDS最後爲2008年金融危機買單,到幾年前我國部分產險公司的信用保證保險爲P2P客戶提供損失補償,雖然吸收了社會風險,發揮了保障社會經濟穩定的部分作用,但“我以我血薦軒轅”,部分公司終因失血過多而不得不尋求社會資本或政府資金的拯救。
轉型分很多層面,當前全行業所重點關注的,是代理人渠道的改革,據說整個資本市場都在盯着平安的代理人改革。多家公司嘗試獨代模式,也是在爲改革探路。
大家都知道,代理人模式發展至今,存在的問題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改革的驅動因素也不是增加底層代理人收入的道德感召,而是基於前面分析的內外部因素,是市場發生了深刻變化。
改革到什麼程度纔算成功,時間才能給出答案。這裏不展開分析,只舉一個小例子,說明改革也許永無止境,甚至是自我革命。在荷蘭,因爲難以根除的銷售誤導,改革的最終結果是代理人模式整個退出壽險市場。現在留存的是少量所謂財務顧問(Financial Consultant),但FC只能基於其專業諮詢服務向保單購買者收費,不能從保險公司獲取任何費用。
幾年前,安邦在荷蘭收購的保險公司邀請其合作的FC到北京考察,費用全由FC自己支付。其間安邦贈送了每位客人一件風衣,因價格略微超標,在經過數年調查後,以監管部門罰款幾十萬歐元了事。當然,荷蘭市場是比較極端的例子,這種做法在全世界也不多見,但從中也可以看出諸多端倪。
結合本節會議的主題,我認爲在老齡化時代,需要我們用更加開放甚至更加大膽的思維,思考壽險業如何轉型的話題。如前所問,老故事講不通的話,新故事在哪裏?
我們知道,金融和保險都是次生需求,必須附着在諸如衣食住行等原生需求的基礎上。在生態化年代,任何次生需求的開發,都需要與原生需求更加緊密地結合,才能佔得先機。在供給充分的情況下,去哪裏找到客戶並喚醒需求就成爲競爭的主戰場。
換句話說,在生態經濟和數字經濟驅動下,金融業發展的邏輯變了,“更靠近實體經濟,更靠近原生需求”可能成爲未來發展戰略中繞不過去的環節。這不單是培育“第二增長曲線”的問題,而是挖土築地,爲未來深耕厚植奠定基礎,即所謂“長坡、厚雪、寬道”的問題。
招商銀行近年來不斷在各類個人生活場景中爲客戶提供各種打折優惠或補貼,貼近客戶的原生需求並建立高頻互動,將其金融服務深深植根於客戶的日常消費中,最終在大理財時代再次建立起領先優勢。招行的戰略獲得了資本市場的青睞,目前其滬深股市值1.36萬億元,市淨率達到2.11倍,市值在中國的銀行中僅次於工商銀行。
表3:代表性上市銀行市值走勢(單位:億元)
也因此,回到前面的問題,保險與其它行業在養老金融市場的競爭中,可以從哪裏尋求突破?如果不能提高有競爭力的收益回報,我拿什麼奉獻給你,我的保險客戶?答案也許就在於,保險需要多走一步,更深入地佈局到原生需求領域。而和壽險最直接相關的原生需求,就是健康醫療和養老服務。
大家都知道凱撒醫療和聯合健康的故事。從近十來年對大都會人壽與聯合健康的市值對比來看,我們就知道市場對這種深度結合是認同的。十年前兩家公司市值相仿,十年來,聯合健康增長了7倍多,達到3800多億美元,PB爲5.8,而大都會人壽只增長了60%左右,520多億美元,PB僅爲0.8。養老與保險的結合全球鮮有先例,但泰康在中國市場率先開始探索,目前也取得了社會的充分認可和業務發展上的成功。
圖4:聯合健康與大都會市值對比
圖5:聯合健康與大都會P/B對比
當然,險養結合模式屬於從金融向實體的深度滲透,在觀念、政策、技術、風控等層面還存在諸多問題。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是,險養結合如果被看作是多元化經營,在政策層面該如何看待這種由客戶需求驅動和時代變化推動的創新和突破?
歷史上看,保險業的多元化,有如下幾種動因:
第一種是投資衝動。就是運用保險資金盲目開展控制性併購,這種模式缺乏內在的協同邏輯,單純尋求資金話語權,專業能力和管理經驗跟不上,基本上都是失敗的案例,應當嚴令禁止。
第二種是混業金融。這屬於金融供給的橫向擴展,在監管和風控到位的情況下,有成功的可能。但從多次金融危機的教訓看,混業經營往往導致風險跨業傳遞,需要謹慎對待,監管目前也是嚴格控制的態度。
第三種是生態經營。這是基於生態模式構建下的服務鏈縱向延伸,是產業發展到數字化和科技化階段的產物,有其市場必然性和合理性,可以在有監管的前提下,逐步積累經驗,有序開放和發展。
當然,對於這種產業鏈的縱向延伸,作爲金融工具的保險業,應該有哪些風險隔離措施,應當具備哪些基礎條件,財務上能否自圓其說,保險以什麼方式切入這個領域更好,險養怎麼結合,如何處理好主輔關係,醫護和宜居哪個是這一模式的重點,需要哪些政策支持和監管覆蓋等,目前全行業都還沒有特別明確的答案。
但無論如何,這種轉型是保險業新一輪的模式創新,也是環境逼迫下的又一次突圍之旅,也許決定着保險業的未來走向,需要監管和行業以既開放又審慎的態度,進行更紮實的探索和求證,共同尋找答案。
各位都知道大家保險的來龍去脈。三年多來,我們沿着“資產重組、管理重塑、業務重啓”同步推進的康復之路,努力推動公司轉型發展。時逢行業內外部形勢的劇烈變化,挑戰和難度可想而知。公司成立以來,何肖鋒董事長提出了“CPC(Customer-Product-Channel)+SHI(Senior Housing Industry)”的業務戰略。渠道方面目前我們正努力推進獨代模式的試點,養老產業方面我們以城心養老和旅居養老爲切入點,加速在全國佈局。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爲保險業的健養生態建設貢獻一個“大家樣本”。
多年以前,梁啓超在遊歷歐洲回國後,面對積弊重生的國政和愚昧落後的國民,用他一貫樂觀堅韌的人生態度寫到:可以憂患,不可以悲觀!更多年以前,陶淵明面對人生的不如意曾經寫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今天,我們面對低迷的市場,嚴苛的環境,更需要這種冷靜、達觀和堅毅。只有更堅定不移地推動行業擁抱變化,不斷向前,腳踏實地,大膽轉型,壽險業的未來發展才更值得期待。
路在腳下。其實並不複雜,只要記得你是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