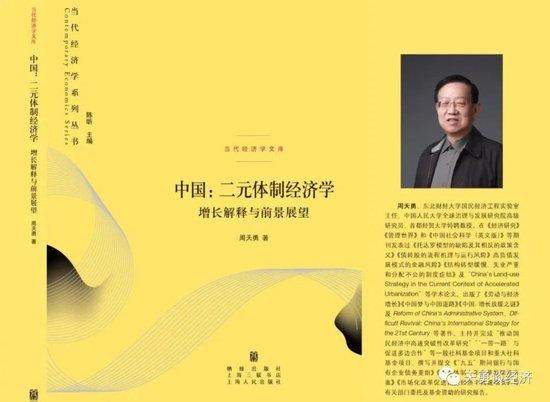西安裝修工住進業主家的21天,喫了60多桶方便麪
原標題:西安裝修工住進業主家的21天

梁炎平暫住的房間。受訪者供圖
作者|劉言
編輯|秦珍子
一接到鄰居的通知,梁炎平就開始往家趕。
這個62歲的湖北人在西安打工,租住在南三環附近的南里王村。2021年12月21日,他和工友出門幹了半天活兒,下午3點多,鄰居打來電話說,“要封村了”。
梁炎平是搞裝修的,業主家所在的中環國際小區,離南里王村只有4公里。他騎電動車,路上已經看到村子被綠色鐵皮圍擋住。抵達村口後,他被執勤的民警告知,“村子不讓進,也不讓出。你從哪兒來,就回哪兒去”。
這一天是冬至,截至24時,西安市共劃定了封控區229個,管控區76個,封控16萬人,管控68.5萬人。
梁炎平和工友沒處可去,不得不返回工作地點。那是一套新房,剛整完地面和牆面,沒有暖氣、熱水、竈具或任何傢俱。裝修公司徵得業主同意,給他們送來4條被子。
第二天,12月22日,西安發佈通知,23日0時起,“全市小區(村)、單位實行封閉式管理”。通知發佈的當天,大量市民湧入超市、便利店搶購食品。
和梁炎平一樣,很多人暫時無法回家了。喫飯這件小事,成了最大的事。在西安美術學院附近,一家小廚房開始給滯留的考研學生送飯。在西安紅會醫院,醫護人員組織起來,把飯送到無法出院的患者病房。蔬菜供應緊張的時候,不少小區組織了物資交換羣,“土豆掛在門把手上,等會兒再開門時,變成了兩個西紅柿”。
1
回憶起作決定的那個時刻,梁炎平說:“要是回來晚了,這邊再一封,我們不就睡在馬路上了。”
他在西安工作了26年,沒有其他落腳點。工作的場所,成了他和工友臨時的依靠。
梁炎平開始意識到,自己之前對疫情的估計太樂觀了。此前幾天,他曾聽說村裏有了確診病例,防疫人員穿着防護服,上了村子裏的一戶人家的門。他也曾目睹,那家人所在的巷子豎起了圍擋,不允許進出。但在當時,這些並沒有引起他的重視,“我們該掃碼掃碼,該幹活兒幹活兒”。
他沒更詳細瞭解的情況是,12月19日,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通報稱,南里王村一位24歲的女性確診新冠肺炎,21日,和她同樓居住的一位30歲男性也被通報確診,南里王村升級爲中風險地區。
梁炎平記得,他們住進中環國際小區時,小區裏便利店商品還比較齊全,“方便麪、麪包、火腿腸、鵪鶉蛋、雞腿、鴨腿都還有”。到了22日,他發現周圍已經很難找到營業的餐館。裝修公司經理跑了好幾個地方,給他們帶了飯菜,“晚上他說,我也出不來了,我們只能各管各的”。
中環國際小區很快也進入封閉狀態,“可以上下樓,不能出小區”,梁炎平開始了隔離生活。屋裏地面冰冷,他和工友把裝修用的木工板抬進朝南的主臥,鋪上公司送來的被子,搭了個簡易的地鋪。
這不是梁炎平第一次經歷隔離的生活。2020年春節,他回湖北天門老家過年,經歷了一個多月的居家隔離。和那次相比,這一次他少了很多焦慮。讓梁炎平苦惱的是,由於小區封閉倉促,他們沒有攜帶生活用品和換洗衣物,“身上都要臭了”。
主臥有15平方米,有大大的落地窗。梁炎平每天會從這裏往下看。剛開始,他還能看到路上有私家車和公交車,漸漸地,路上既沒有車也沒有人了,“乾淨得很”。外賣也都停了,“送不進來,下了單馬上就取消了”。
喫飯,成了他的頭等大事。
2022年元旦前,一條抖音短視頻在關心西安疫情的人羣中傳遞。畫面中有幾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羞澀地解釋,自己來考西安美術學院的研究生,暫時走不了,沒飯喫了。拍攝畫面者是位女性,在視頻中,她熱情地表示,來我們這裏喫吧,每天都可以來。
那位女性是西安德善廚房的一位工作人員。這家公益廚房地處陝西省腫瘤醫院和西安交大一附院附近,平日裏有需要的病患家屬可以來做飯,“炒一個菜2元,米飯1元管飽”。
本輪疫情管控升級後,德善廚房的發起人許凱想,很多外地患者和家屬租住在醫院附近的城中村裏,不少房屋沒有竈具、炊具,“他們更需要那頓飯”。
他當時還沒有想到,西安美院也在附近,城中村裏還生活着另一個羣體——考研學生。
許凱曾經學過畫畫,他看到自己的一位美術老師發出求助信息,有考美院的學生滯留西安,封在城中村裏,沒有飯喫。
2
惦記着“讓他們喫上飯”,許凱的德善廚房“火力全開”了。志願者每天準備1000多份熱飯,免費送給支援西安的救護車隊、負責社區核酸檢測的醫務人員、附近城中村裏滯留的外地就醫者和考研學生,大廚來自一家五星級酒店。大鍋裏,翻騰着面片、蔬菜、肉丸子和熱湯,許凱的合夥人開車送飯,他則每天兩次,拎着幾十份燴麪、麻食(一種西安麪食)等走路送到城中村裏。

德善廚房的工作人員正在切菜。受訪者供圖
送飯時他了解到,學生來自全國各地,有陝北的,也有內蒙古呼倫貝爾的、河南鄭州的、河北石家莊的。他還認識了一位乳腺癌患者,這位女士在喫到他送來的飯之前,已經喫了十幾天方便麪。
——紅燒牛肉、麻辣牛肉、西紅柿燉牛肉……這些硬菜的名稱後加一個“面”字,正是梁炎平和工友的口糧。屋裏只有一隻電水壺,沒有炊具和餐具,梁炎平和工友買了3箱桶裝方便麪,一開始還能換着口味喫。
後來,小區的便利店裏,方便麪也沒有了,物業賣給他們一箱。“我還想弄一點鹹菜、榨菜,都沒了,看見有一袋酸豆角就趕緊拿上。”梁炎平回憶。
截至發稿,梁炎平和工友已經喫了60多桶方便麪。他們想盡辦法喫出不一樣的滋味,比如這頓不放香料,下頓不放油包,再下一頓不放鹽包,“調料少一種口味就有差別”。因爲沒喫蔬菜,梁炎平20多天只有幾次大便。
他和工友找到小區物業尋求幫助,經理告訴他,“有什麼困難儘量找我們”。他的第一個請求就是想喫點別的。有時核酸採樣時間長,物業會給防疫人員訂飯。元旦那天,經理也幫他們多訂了一份。那是一份炒米飯,梁炎平“風捲殘雲”地喫完了。
“一份香腸丁炒飯,配菜是蒜苗和洋蔥。”梁炎平把那份炒飯記得清清楚楚,“我是湖北人,確實好久沒喫米飯了,實在受不了。”
那天和妻子視頻通話時,他“報喜”:“我今天終於喫上米飯了,特別香,你們別擔心。”一個多月前,妻子回了湖北老家,擔心他過得不好,每天要打視頻電話看他。20多天過去,他花白的鬍子已經長過了領口。
梁炎平看新聞發現,喫飯問題不光是他自己的問題,城市實行封閉管控後,很多居民家都出現物資短缺的情況。後來,各個社區開始配送糧油和蔬菜水果。他每天透過窗戶看,小區今天有沒有人送進來物資,送的什麼東西,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他們用得上的。他記得,2021年12月28日,有車拉着蔬菜進小區,“蘿蔔、白菜還有好幾個饃,99元一袋”。元旦那天,政府送來免費菜,小區居民每戶憑卡領一袋,“有蘿蔔、白菜,還有青菜,必須得弄熟,我們就沒要”。
梁炎平每天都和同住在南里王村的朋友聯絡。朋友告訴他:“外面有人拉菜進去賣,就是價格稍稍貴了一點,一棵白菜賣到了30元。”
根據最初的疫情防控措施,西安多家醫院停診,醫護人員則留在院內值守。康鑫是西安紅會醫院運動醫學科醫生,也是醫院志願者服務隊隊長。這家知名的骨科醫院有40多個病區,在院患者600多人,加上陪同和醫護,每天每餐需要1000多份餐食,全靠醫護志願者運送。但在作爲外科醫生的康鑫看來,還有一類事,比喫飯更加緊急。
3
1月2日下午6點,康鑫接到朋友的求助微信,稱鄰居張成(化名)急需醫生幫助。
張成所在的小區位於雁塔區東儀路,已經封閉管控。不到一個小時前,張成躺在牀上休息,被兒子當成“蹦蹦牀”踩了,膝蓋“當時就感覺跑偏了”。
張成試着撥打“120”,得知就診需要“社區安排”。按照當時西安發佈的就診流程,居住在封控區的張成需要聯繫社區工作人員預約定點醫院後,再由街道安排專用轉運車“點對點”就醫。情況緊急,他通過微信,聯繫上了康鑫。
收到傷者發來的微信圖片,康鑫看到,張成左腿的膝蓋已經偏到身體外側。“髕骨脫位。”這位醫生很快作出診斷。在紅會醫院,他平均每個月都要急會診很多這種髕骨脫位的患者。
他撥通張成的視頻電話,在充分告知各種預後情況的前提下,指導他的家人,“通過手法復位,能解決他目前最要緊的問題”。康鑫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張成的情況不是非常緊急,不一定非要到醫院處理,自己遠程指導,也許能把轉運救護車這些公共資源讓給最需要的人。
視頻接通了。康鑫讓張成的兒子拿着手機,把攝像頭對準膝蓋部位,然後指揮張成父親“哪個指頭下壓,哪個指頭要發力,按着腿往哪個角度使勁,往哪個方向抬”。康鑫回憶,老人不懂專業的醫學知識,但“能狠得下心聽指揮”。一分多鐘以後,張成膝蓋的“絞索”狀態解除了。
康鑫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並不是紅會醫院唯一一個遠程幫助封控區病人的。在自家小區的業主羣裏,運動診療中心主任鄭江也收到了求助:“鄭主任,我娃胳膊脫臼了,您能不能來幫忙看一下。”
一直堅守在醫院的鄭江拉來一位科室醫生當模特,找來另一位醫生拍下一段19秒的手法復位視頻,告訴患兒母親,聽到彈響聲就可以了。母親對照視頻操作,很快成功復位了孩子的胳膊,鄭江在羣裏收到一片“大拇哥”。

西安紅會醫院鄭江醫生爲患者錄製的手法復位示範視頻截圖。受訪者供圖
比起沒飯喫,梁炎平更害怕生病。剛刷完牆的房間格外潮溼,但他和工友甚至不敢開窗通風,“現在還好,萬一感個冒也沒地方治,喫藥也沒地方買,更難受了”。
寒冬臘月的西安,平均氣溫在0攝氏度左右,到了晚上還會降到零下。屋裏沒通暖氣,兩個男人睡在一起,“抱團取暖”。兩個人不僅是工友,租住在南里王村時也是鄰居,這讓這段“同居時光”少了幾分尷尬。閒着沒事,他們會聊一聊老家的情況,盤算着工地上還有哪些活兒沒做,哪幾個地方的工錢沒有收回來,還有多少工人的工資沒發下去。
晚上6點,天一黑,屋裏的溫度就直線下降,兩人冷得鑽進被窩,一直捱到10點,“犯困了,手機往邊上一撇就睡着了”。這些天來,早上不到5點,梁炎平就會被凍醒,在被子裏來回翻騰,直到8點起牀。
早上,他要下樓到小區裏排隊接受核酸檢測採樣,最初每兩天做一次,28日開始變成了每天一次。“做完上來刷一會手機,中午喫完飯,再繼續刷手機,刷到5點再喫飯,喫完飯就去躺着刷手機,直到睡覺。”年過花甲的他正在經歷人生中最艱難的一段日子,與往常不同,新聞成了他每天的必需品。“前一天疫情是個什麼情況,會不會得到扭轉。”他期盼着能在手機屏幕裏看到,“什麼時候能回去,儘快結束這種生活。”
所有人都抱着相似的期待,爲了那一天早點到來,許多人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
德善廚房成了“力量的中轉站”。一位臺灣同胞捐贈了1萬元;一家武漢的心理診所捐贈了幾千元,一所武漢的幼兒園義賣了孩子們的畫,捐了1000多元;一位武漢微光救援隊隊員4天兩趟開車往返西安,送來物資;一名執行任務還能出入廚具市場的西安警官,聯合同事捐贈了一個猛火大竈;一位路邊的保安買來饅頭;而一個坐救護車到醫院給孩子取藥的父親則專程趕來,把一沓百元人民幣塞到許凱手上,讓他“能買多少(菜)買多少”。
“哥,那你是誰,你是誰嘛?!”許凱推不掉這份心意,追着那位父親跑,用陝西方言大聲問。
“額是……額是……”男人語塞,一邊跑一邊急忙道,“額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