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聯盟信息部長:北約轟炸南聯盟——西方妖魔化塞爾維亞的最後一擊
導讀:1999年3月24日,北約對前南斯拉夫聯盟悍然發動襲擊,向其990個目標發射了2300枚導彈,投擲了14000枚包括貧鈾彈和集束炸彈在內的炸彈。導致超過2000名平民喪生,數千人受傷,20多萬人流離失所。 但是,在西方的媒體霸權下,這樣一場人道主義災難卻被描繪成北約爲“挽救被南聯盟迫害的科索沃阿族人”而發起的正義行動。 對此,前南聯盟信息部長格蘭·馬蒂奇詳細剖析了北約轟炸圖謀的醞釀背景和過程。他表示,西方對塞爾維亞展開了系統性的妖魔化,古羅馬時代的“迦太基必須被毀滅”,正發生在他們身上。
【文/前南聯盟信息部長 格蘭·馬蒂奇 翻譯/菲利蒲·菲利波維奇(塞爾維亞在華留學生) 編輯/李煥宇】
南斯拉夫——一個⼆戰之後⼤家集體達成⼀致形成的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德國統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後,當初維繫各方的一致共識已不復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它已被宣告死亡,而科索沃危機,是給這個正在解體的國家敲下的最後⼀擊。

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巴爾幹新格局出現
南斯拉夫(聯邦)的解體原本能有多種模式,在90年代初的時候,塞爾維亞就曾主張過通過憲法和民主的⽅式和平解體,這意味着民衆可以選擇⾃⼰想在哪⼀個共同體⾥繼續⽣活。然而,後面發生的事情跟這種精神背道而馳,它是以一種⾮憲法、⾮民主的⽅式開始的。
首先是斯洛文尼亞在西⽅尤其是德國的⽀持下獨⽴,之後是克羅地亞。不過在那個國家,居住着⼀⼤批不想獨⽴的塞族,加上⼆戰時期遺留下的後遺症(注:⼆戰期間,克羅地亞在德國的幫助下殺死了七⼗萬塞族,亞賽諾瓦茨等諸多集中營記錄了克羅地亞納粹分子的罪惡行徑),使得他們更不願意與克羅地亞⼈⼀起⽣活。由於塞族不願意接受作爲德國(和西⽅)代理⼈的克羅地亞這樣獨⽴,該國爆發了內戰。
克羅地亞內戰期間,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波黑)又被美國基本承認獨立了。但是,波黑當時完全不具備作爲⼀個國家⽣存的條件,什麼問題都沒解決,於是波黑也爆發了戰爭,那是一場大戰,各方打得很慘烈。

波黑地圖,紅色爲波黑塞族共和國;藍色爲克族和波黑穆斯林的波黑聯邦,右上角是《代頓協議》爲了將塞族共和國拆開設立的布爾奇科特區
再之後的事情我們也看到了,在布什和⼽爾巴喬夫談的時候,德國也參加了,當時說讓華約解體,北約不東擴。但是這個沒有發⽣,華約解體之後北約展現出了進攻性姿態,吸納了前華約陣營的國家,然後開始包圍俄羅斯。塞爾維亞則被視爲⼩俄羅斯,因爲兩族都信仰東正教,還有着良好的關係,那些規劃肢解南斯拉夫(聯邦)的人也借⽤這⼀機會向俄羅斯施壓。
於是,內戰的責任全都被推到了塞族⾝上,塞族沒做的事最後塞族被承擔了責任:塞族被指責挑起克羅地亞戰爭,即使這是南斯拉夫(聯邦)內部的事;塞族被指責在波⿊犯下了滔天⼤罪,⽽這些事根本就不是塞族做的……
最後,1995年的代頓協議結束了波黑戰爭,次年的伊爾杜協議化解了克羅地亞和該國塞族之間的不和。1997年,巴爾幹已經出現了全新的⼒量格局。
科索沃問題與北約第一次轟炸圖謀敗露
正是從這⼀年開始,美國開始向南斯拉夫(聯盟)施壓,逼着南斯拉夫(聯盟)以不同的姿態對待科索沃,這時候的南聯盟是由塞爾維亞和⿊⼭構成的⼀個國家。這些施壓從97年開始,我以官⽅⾝份親⾃去過⼏次美國(談判),⽽且多次和美國駐南⼤使討論過這件事。他們當時希望在國際監管的基礎上以某種⽅式讓我們把科索沃轉交給他們。
這個國際監管⾔外之意就是美國監管。我們當時認爲這是南聯盟內政,而任何⼀個國家內部的少數民族問題不能通過這種簡單的獨⽴來解決。在那段時間,國際社會對南友好的國家也在幫助南聯盟採取政治協商措施,政府也組織了⼀系列與科索沃阿族領導⼈的對話,然⽽阿族領導⼈經常不願意出席對話。
只有在1998年,他們提出要⾃⼰搞⼀套獨⽴的教育體系,這個被批准了,然後這方面搞出了⼀個和解。
但也正是在這一年,科索沃問題不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我們⾯對的是接受過武裝訓練的阿族,他們主要是在接受培訓,然後從阿爾巴尼亞向科索沃滲透。
那一年的科索沃和梅託西亞省(科索沃全稱),有超過2000個不同民族的⼈被殺害,包括塞族、阿爾巴尼亞族、黑山人、土耳其人,克羅地亞⼈也有,他們都不接受科索沃獨⽴,甚⾄有⼀些在政府機構上班。
這個恐怖組織被稱爲科索沃解放組織,他們殺害包括物流⼈員到政府⼈員在內的各種⼈、不管他們是什麼民族,他們想通過這種⽅式表明他們不想在塞爾維亞政府所在的地⽅居住。
在意識到得到武裝的阿族在西方支持下策劃了當地的恐怖⾏動後,1998年6月,政府採取了⾏動,把這個恐怖勢⼒給摧毀了。當時我們帶着各國使節,包括中國⼤使去了普⾥什蒂納,並且告知世界科索沃還在我們的體制當中,恐怖主義已經被消滅,⼈民的⽣活是正常的,在⼀些塞族村莊可以看到恐怖⾏動和反恐戰爭的⼀些後果。
那年10月,我們接到消息說,聯合國的代表緒方貞子要去科索沃,當時我們在塞爾維亞政府內有專門負責難民的官員布拉蒂斯拉瓦·莫里娜(Bratislava Morina),她本來要去接聯合國的代表。但是在這次訪問之前⼀天,我們從⼀個國外友好情報機構得到消息說,她去科索沃是要準備搞⼀個⼤的虛假宣傳,他們會僱傭當地民衆僞裝成阿族難民在當地搞遊⾏,然後通過製造所謂難民危機來授權北約轟炸南聯盟。因爲北約已經在這之前出臺了文件,說在科索沃阿族⼈權被侵害的時候可以授權空襲。

緒方貞子 圖片來源:日經中文網
這一套宣傳的目的是讓北約在98年10⽉的時候就開始空襲。我們之後也發現,他們的轟炸規劃是爲冬天準備的,他們的轟炸⽬標⾥⾯包括民⽤的熱電站,還有⼀些軍⽤設備和建築。他們當時認爲如果10⽉開始轟炸,在12⽉期間塞爾維亞已經會⾯臨能源上的崩潰局⾯。
最終,聯合國的代表緒方貞子去了科索沃,但是我們在她去之前提前得到了他們的攝像規劃和抹黑南聯盟的視頻材料,視頻裏面有西方人員跟演難民的⼈的交易視頻,錄像裏面還有西⽅指導他們怎麼僞裝成阿族難民。
我記得緒方貞子是週末到的,⽽我們周⼀就已經準備了與所有⼤使的會議。時任外長也跟我⼀起去了,我給了他⼤概60個錄像帶,發給了所有⼤使,並且明確告訴各國使節:“這是西⽅想搞的⼀出戏,本來所有西⽅媒體都要放這個的,他們想通過這種⽅式指責塞族是法西斯納粹,搞什麼種族清洗,這都是假的,證據給你們。“
拉查克事件,北約轟炸開始
這個之後事情稍微有所緩和,後來歐安組織提出要求要加入,歐安組織表示要派獨立的非軍事觀察團,我們也接受了。然⽽這個觀察團的領隊是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威廉·沃克爾,他在拉查克演出了那個所謂的事件——科索沃解放組織的成員⾝穿軍裝與我⽅警察發⽣交戰並且被清除,第⼆天他們的軍裝被脫掉了,然後⼀次反恐⾏動被外界描繪成了對平民的屠殺。後來這也證實是假的了,然⽽北約就是在這個事件的基礎上轟炸了南聯盟(注:拉查克事件被認爲是北約轟炸南聯盟的導火索)。
期間還有過幾輪在朗布依埃和巴黎舉行的和平談判,但是談判期間又有⼀些新的事情:
⾸先拉查克還是被定性爲了塞族的罪行——這是假的,所有歐安組織的⼈也知道這是假的,因爲他們觀察了全過程。歐安組織原本作爲歐洲維和的⼀部分,被北約惡意利⽤成了宣傳⼯具。
然後就是那些談判根本算不上是和平談判。參加會議的西⽅⾼層,⽐如美國時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她在桌上擺了兩個跟阿塞談判沒有任何關係的附件:第⼀份附件的⽬的是授權北約進⼊南聯盟全境,並且讓他們的⼠兵享受治外法權。英國⾸相布萊爾被問起這樣做的⽬的是什麼,英⽅表⽰這是爲了⽅便外國⼒量到貝爾格萊德逮捕⽶洛舍維奇;第⼆個附件是三年內讓科索沃搞獨⽴公投,當然這個公投肯定受他們影響,塞爾維亞將被迫接受科索沃獨⽴。
這兩個⽂件西⽅政客沒有向西⽅民衆公佈,他們只是說南聯盟不接受任何和平協議和政治解決。
現實是,南聯盟接受了政治解決,也接受了科索沃⾼度⾃治,但是沒有接受被侵略。然後空襲就開始了,我們被迫接受新的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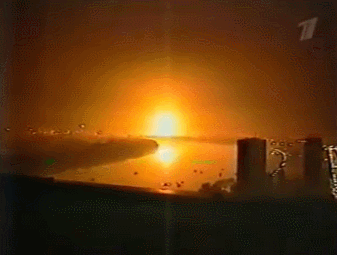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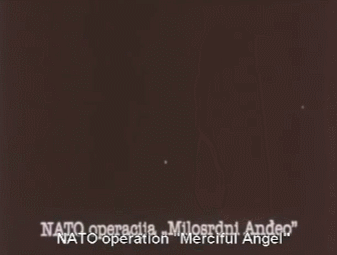

轟炸期間,北約共向南聯盟990個目標發射了2300枚導彈,投擲了14000枚包括貧鈾彈和集束炸彈在內的炸彈。導致超過2000名平民喪生,包括88名兒童,數千人受傷。約20萬塞爾維亞人被迫撤離科索沃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南聯盟的輿論反擊戰
空襲的第⼀天我們就知道北約和西方會利用那些假的精英和專家提供的(看起來慘不忍睹的)照片、文件、報告什麼的,於是我們決定做以下事情。
西⽅記者除了根據指令做事之外,還有⼀些個人動機,比如在報道期間得到勁爆的消息,傳送現場照⽚,然後以此晉升、賺錢等。於是我們就嘗試利⽤這些有權勢的媒體,BBC、CNN、SKY、CBS等,把這些記者打包進⼀輛公交車,使他們在平民被北約空襲的時候能在場,然後讓他們去拍。我們還告訴他們可以拿⾛⼀些炸彈碎⽚,讓你們給民衆看看這是你們炸的,炸彈上有寫編碼和名字。
轟炸造成了近兩千平民傷亡,之後他們就把這些發給了⾃⼰的公衆,這些西⽅媒體也沒辦法拒絕把材料放出來,⽐如SKY電臺的記者,蒂姆·馬歇爾(Tim Marshal),他跟⾃⼰的編輯吵起來了,SKY主編那邊問你確定這些東西不是塞族空襲造成的嗎,然後就反覆拖沓,想盡辦法找理由是不是塞族做的,最後他們就找了⼀個詞:所謂附帶損傷。然後⼀直在報道他們的空襲多麼多麼成功。

蒂姆·馬歇爾在貝爾格萊德
我們⽤照⽚反對報道的概念還是有所成效的,且重點在於這些照⽚是他們的記者發給他們的,⽽不是我們的。假如我們把這些照⽚給⽐如RTS(南斯拉夫廣播電視臺)這樣的塞媒發給西⽅的話,西⽅肯定會說這是假新聞。也根本不會接受這個現實。我們利⽤他們的媒體,把材料發給西⽅民衆,給他們看了他們的領導⼈⽤空襲造成的罪⾏,並且讓他們的記者去拍,這是我們唯⼀能做的。
他們⾃⼰也說我們這⼀點做的很成功。他們也的確因這些報道碰到過麻煩,⽐如BBC記者約翰·辛普森(Jhon Sipmson)就因這些報告與布萊爾吵過架。辛普森對塞爾維亞的傾向並不是很強,還是跟英國站在同⼀戰線的,但是當寫到北約要炸居民區並要殺平民的時候,他就是這麼寫好發過去的,這個他沒有辦法撒謊,他也不想被當成騙⼦被⼈記住。⾄於他推崇英國的政策、推進英國的政策,主張轟炸塞爾維亞,這是另外⼀回事。總之我們通過⾃⼰的努⼒稍微把情況掰過來了⼀點。
之後⼀個奇怪的情況出現了,空襲的時候他們打不到軍事⽬標,另⼀⽅⾯他們又要⾯對⾃⼰的公衆,我們每天會通過他們的媒體向他們的公衆發佈當地發⽣的所有轟炸。他們如今也沒辦法否認這些罪⾏,塞⽅提供的材料以後希望留給後代去審判那些應該被審判的⼈,⾄少當作歷史材料進⾏作證,⽤以證明他們的謊⾔。
假如沒有我們提供的這些材料,他們所有那些編造出來的照⽚,編造出來的報告會永遠被當作現實。當時主要主張轟炸的那⼀批西⽅⾼層也逐漸⼀去不復返了,克林頓的⼈基本沒了、布萊爾也下去了,施羅德現在在搞北溪項⽬,希拉剋去世了,索拉納退休了,還得了新型冠狀病毒,慢慢那⼀整代⼈正在消失。他們的後代肯定不可能⼀夜之間改變他們的⽴場,但是現實他們總歸是逃不過去的。因爲現實是他們的記者拍下來發給他們的。
現在只剩下⼀個道德問題,也就是戰爭到底道不道德,需要如何懲罰。這是留給未來的。
科索沃危機,西方系統性反塞的冰山一角
需要強調⼀點,科索沃只是90年開始這⼀系列事件當中的最後⼀個瞬間。從90年代開始,呼籲肢解南斯拉夫的聲音從未斷過,尤其是德國方面,想方設法要侮辱我們。
這是因爲兩次世界⼤戰德國的戰敗。兩次世界⼤戰中,即使塞爾維亞很渺⼩,但是發揮的作⽤很⼤。第⼀次世界⼤戰,塞爾維亞堅守住了塞薩洛尼基防線,⼆戰中塞族牽制了原本可以幫助德軍攻下斯⼤林格勒的重要⼒量。因此我們從官⽅渠道和祕密渠道都瞭解到,德國⾼層存在⼀股⾮常反塞的勢⼒,他們認爲需要迫使塞族徹底跪下。
在這樣的⼀個政策下,⼀整套相互協調的舉措便開始了,背後有索羅斯的全球化⼒量贊助的⾏動,他與克林頓的美國政府相互合作在全球形成了⼀股攻勢,在巴爾⼲地區這⼀點尤其明顯。他贊助的衆多⾮政府組織,⽐如開放社會基⾦、南斯拉夫⼈權律師協會等,以及他們發展的,我們所謂的“有影響⼒的祕密⼒量”,即⽀持親西⽅⽴場的精英和知識分⼦在當地⾮常活躍。
早在93年波⿊內戰之際,就有數⼗個當地知識分⼦聯名要求轟炸南斯拉夫了,這個後來也被西⽅媒體報道了。這些知識分⼦⼤多是塞爾維亞⼈,⽐如瑟爾賈·波波維奇(Srdja Popovic,顏色革命“教父”吉恩·夏普的學生,塞爾維亞非政府組織“抵抗”的創始人,其運作手法成爲顏色革命的模板被推廣到全世界,包括香港);⾄於那⼀些受到穆斯林和克羅地亞影響的知識分⼦我就不提了。他們就是想把⼀切栽贓給塞族,或者用宣傳術語講叫對塞族的動態妖魔化。
這種動態妖魔化從90年代初就開始了,主要參與的是德國,理由我已在上面提到過,還有他們的地緣政治⽬的,這⾥⾯梵蒂岡起到的作⽤很⼤,因爲他們想擴⼤天主教的勢⼒範圍。我們現在碰到的這個教宗,在大概六次演講中提到對克羅地亞⼈來說巴爾幹是家園和任務。這意味着他們覺得在巴爾幹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任務是在巴爾幹非天主教的地區繼續擴⼤勢⼒範圍。說⽩了就是針對伊斯蘭和東正教。這個實際上延續了16、17世紀耶穌會的那⼀套理念。

巴爾幹一帶的宗教分佈:紅色系爲天主教、紫色系爲東正教、綠色系爲伊斯蘭教
所以說呢,塞爾維亞人在這樣的⼀個環境下敵⼈實在是太多了,我剛剛提到了指揮西歐⾏爲的德國,還有告訴天主教世界如何應對塞爾維亞的梵蒂岡;波⿊內戰期間的⼤半個伊斯蘭世界⽀持波⿊穆斯林;我就不深⼊講波⿊⼈是什麼了,簡單說就是信仰別的宗教的塞族。然後還有克林頓政府,美國當地的學者說克林頓政府免職了所有反對巴爾⼲和中東伊斯蘭化的情報官員,在克林頓兩個任期⾥⾯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其實已經開始猖獗了。
塞爾維亞這時候還要⾯對葉利欽的俄羅斯,⼀個在地緣政治上很孤⽴,處境很不好的國家,其他⼤部分國家則是反塞的。塞爾維亞能挺過90年代⽣存下來簡直算是個奇蹟。當時所有的政府機構都花了很⼤的⼒⽓,包括⾼層、情報界、民事和軍事的國家安全界,以及我們的反宣傳舉措,不論我們有多麼渺⼩,我們當時⾯對的就是如今所說的西⽅媒體的壟斷。當時我們就已經要⾯對所謂全球化的、利⼰的西⽅媒體,當時CNN、BBC、SKY、ARD、RAI或者法國的電臺,這些關鍵的媒體不會出現表態不⼀的情況,你們也很難看到他們不分享同⼀個⽴場。
所以,塞爾維亞⼀直在⾯對這種統⼀的妖魔化,這種妖魔化的局⾯如同⽼加圖在羅馬元⽼院⾥天天喊“迦太基必須被毀滅”。這⼀幕在塞爾維亞⾝上也發⽣了。
也有⼀些國家是⽀持我們的,⽐如俄羅斯,但是並不是通過葉利欽這邊,⽽是通過其他渠道,⽩俄羅斯的⽀持很⼤,塞浦路斯也有提供幫助,當然還有中國的幫助,但是那時候中國在巴爾⼲並不活躍,⽽且經濟和政治層⾯我們當時很難期待中國起到決定性的戰略作⽤。畢竟1999年的中國和2020年的中國有着天壤之別。
國際政治當中如今太多事情改變了。這⾥⾯有意思的是,西⽅的媒體已經超霸權了,他們是⼀個協調的整體,並且在推進各⾃政府的戰略和利益。從屬結構上,他們是世界上最強⼤的跨國公司的附屬品,跨國公司通過各種協議得到政府授權來控制媒體。
有⼀本很著名的書叫The new media monopoly,班·巴格迪基(Ben Bagdikian)寫的,他在⽔門事件的時候就有點名⽓了,他在書中寫道,當美國所有這些重要媒體的⽼板,⽐如FOX、CNN等,當這些⽼板全都放在⼀起,⼀個15平⽶的房間都能裝得下。可以說是屈指可數。

我們如今⼀直說獨⽴媒體、媒體去中⼼化,還有什麼客觀報道,這些東西當時都不存在,我的個⼈經歷是完全相反的,1997、98年左右的時候我先是擔任了信息部的祕書長,後來擔任信息部部長,我們當時做了做⼀個實時跟進西⽅電⼦媒體的團隊,當時在塞爾維亞今⽇報社我們還只有跟進短波電臺的團隊和紙質報紙的團隊,⽐如紐約時報、泰晤⼠報等。
但是這種跟進的模式太慢了,SKY或者FOX這種媒體在電⼦衛星版的媒體上每個⼩時都在發佈新東西,每⼀個⼩時都不⼀樣,然後當時我們搞了⼀整套追蹤電⼦版新聞的現代化辦公室,裝了⼤概20多臺屏幕實時跟進,結合我們已經有的技術進⾏全覆蓋。然後這些信息我們又會和各個駐外使領館以及情報部門提供的信息進⾏對照。
到後⾯我們就形成了⼀套預測程序,根據他們的新聞判斷他們要做什麼,⽐如CNN不太會報道記者在說什麼,CNN有明確的指揮體系,會接受明確的指令,具體到什麼時間段放什麼信息、什麼照⽚、要引起怎麼樣的效果,⽐如要引起恐慌,或是其他的⼀些情感,要煽動還是要怎麼怎麼樣,我們實際上發現西⽅媒體如同⼀個很⼤的交響樂團,他們所放的⾳樂是根據指揮他們的西⽅政府放出去的。

某一天,美國幾十家電視臺發出來幾乎一模一樣的臺詞痛斥社交媒體上氾濫的假新聞
⼀般來說指揮最多的是美國,有時候也會有⼀些在巴爾⼲有利益的國家會⾃⼰加⼀點東西進去,克羅地亞這種。但是這種媒體⾏爲都指向⼀個⽅向,就是對塞爾維亞進⾏施壓,塞爾維亞是被侮辱最慘的⼀⽅,對塞政府和民衆的那種侮辱是令⼈感到驚悚的,⽽且參與這種侮辱的都是很有權勢的⼈,⽐如時任法國總統稱直接成塞族是⼀個野蠻的畜⽣⼀樣的需要被消滅的民族。
這都是⼀些西⽅政客和精英的⾔論,當然很多精英是收錢這麼做的,媒體還會專門找這種⼈進⾏採訪,其中還有⽐如德國外長菲舍爾,還有施羅德,不過後者⾃我洗⽩然後跟俄羅斯⼈合作去了。這些⼈的所作所爲對塞爾維亞的國家和民族⽽⾔都是極⼤的侮辱。西⽅媒體所做的事是希望激起⼀種仇恨情緒,就是讓收聽這些新聞的外國民衆厭惡塞族。這個情況⼀直持續到了99年。我們98年的時候算是撐住了,揭露了他們的⼀些謊⾔和10⽉試圖轟炸南聯盟的企圖。
西方媒體霸權下,中國需要塞爾維亞視角
⾄於中國和拉美的問題,我們當時沒有集中向拉美和中國地區的公衆釋放信息,爲什麼?因爲中國對南聯盟的危機報道⽐較⼴泛,⽽且⽐較客觀真實,對塞爾維亞的⽴場也⽐較積極。我們當時沒有必要向中國提供過多信息,中國在貝爾格萊德也有⾃⼰的記者,他們當時被允許隨意⾛動,我們和他們關係也很好,所以我們認爲不需要單獨把中國列作⼀個我們信息達不到的地⽅。
中國當時的記者很棒,信息也很好,我們當時經常引⽤中國的報道,⽤中國的報道告訴塞爾維亞民衆客觀的視角是如何看待南斯拉夫危機的。不幸的是,中國大使館遭到了轟炸,出現人員傷亡。

1999年5月7日,北約用導彈野蠻襲擊了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造成正在使館中工作的新華社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朱穎不幸犧牲,同時炸傷數十人,使館館舍嚴重損毀
可能在這個之後會出問題,因爲西⽅的報告和西⽅的媒體還是太霸權了,主要還是因爲英語太⼴泛了,我估計在中國因爲這種西⽅媒體的霸權,肯定有⼈會吹捧克林頓和奧爾布賴特的說辭,然後這個可能對中國公衆構成影響。
我覺得中⽅需要對此引起重視。塞爾維亞如今在和中國快速推進關係,中塞之間的關係⾮常緊密,⾼層關係很緊,經濟關係的層級也很⾼,我認爲塞爾維亞需要努⼒把這些東西翻譯出來,翻譯成中⽂,英⽂也好,⽤作教材。需要建⽴⼀個所謂塞爾維亞視⾓的概念。
塞爾維亞視⾓不是說我們所謂的特殊的事實,⽽是利⽤西⽅存在的客觀報道,我們逼着他們報道現實的那些材料,從⽽覆蓋我們所說的事情,我們的歷史材料你在BBC、CNN、FOX也能找到,雖然這些信息的量還是少了點。我們當時沒有辦法影響他們的退休軍官和精英⾼層,他們⼀直在說塞爾維亞是⼀個搞種族屠殺的民族,說塞族應該被炸,說塞族活該,說⽶洛舍維奇是巴爾⼲屠夫法西斯。他們會像出售其他東西⼀樣出售這些概念,還會附帶很好的⼴告宣傳。
他們花了⼤價錢宣傳這些東西,美國國務院、政府、議會都⽀持了他們的這種宣傳。他們現在也需要推進這種宣傳,因爲他們的地緣政治⽬標還沒有實現。美國⼈在科索沃現在還有軍事基地,歐洲最⼤的基地之⼀。中國⾼層對這⼀切是很清楚的。並且有⾃⼰的⼀套國際關係理念。
中俄的發展讓北約重演轟炸已不再可能
重點在於西⽅那種全球化的回聲還會持續多久,還有亨廷頓說的那種美國孤⽴的霸權還會持續多久,事實是美國的信⽤也耗盡了,就連他們的戰略規劃師布熱津斯基也表⽰美國耗盡了⾃⼰的打贏冷戰所獲得的所有優勢,並且需要在國際關係⾥⾯尋找新的位置。
他們耗盡了那種所謂的民主信⽤,他作爲⼀個⾃由、開放的國家,最後把這⼀切演變爲了霸權和⼲涉。後續怎麼發展這是下⼀代的事了,但是有⼀點很重要,事實必須被⼈們知道。只要⼤家知道事實,那歷史和未來就能被好好規劃。如果歷史按照德國、美國之前的那⼀套發展,那其他國家也會被污衊。(如果不採取⾏動)這個(撒謊)模式會波及到別的國家。

3月17日,在歐羅巴聯賽16強的比賽中,貝爾格萊德紅星隊球迷用橫幅列出了美國和北約組織直接或間接參與入侵的國家
但是如今的情況已經⼤有不同了。如今我們有⼀個意識到發⽣了什麼的俄羅斯,他們之前就知道,但是那時候沒有能⼒介入。2020年的俄羅斯是⼀個革新的軍事經濟體,⽽且媒體方面⼤有長進,從RT到⼀系列媒體,在全球範圍內都有影響力。
⾄於中國,中國太棒了。我在⼏年前去過希臘,中國在希臘做的宣傳⽐西⽅好太多,因爲中國在宣傳自己的成功經驗。中國如今在宣傳體制內的⾏爲模式跟十幾年前⼤有不同。如今的世界也不是90年代末的那個世界,當時信息革命帶動了美國,但是都是以我們爲犧牲品的。如今情況變了,比如2020年如果美國還想帶動全世界⽀持他們轟炸塞爾維亞,這個如今已經不可能了。有上千個理由,⽐如中俄不⽌會⽤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票來制止美國,肯定還會採取其他措施。
90年代發⽣的事情是國際關係的淪陷,甚⾄是干涉主義史上最⼤的⼀個污點。這個污點有媒體霸權在跟進。那種媒體霸權使其他媒體都被拋擲腦後,如今這種情況已經不存在了。南聯盟轟炸成了許多⼈的前車之鑑。美國已經沒有辦法這樣做了。德國和歐洲也得維護⾃⼰的利益,所以這種擴張沒有了,尤其是英國脫歐之後。
⽣活必需⽤現實的眼光去看待,還有更重要的是,中國必須繼續發展⾃⼰的媒體,中國的媒體客觀、有原則,並且會⽤中國的視⾓塑造國際關係。中國在國際關係層⾯不是⼀個⼲涉主義的進攻性國家。不是那種貶低主權或者想摧毀⼀個主權國家的國家。中國民族性格上就不是這樣的國家,因此這樣的⼀種⽴場需要在國際宣傳界當中立足。中國⽬前做的很好,但是可以進步的空間還是非常⼤的。







